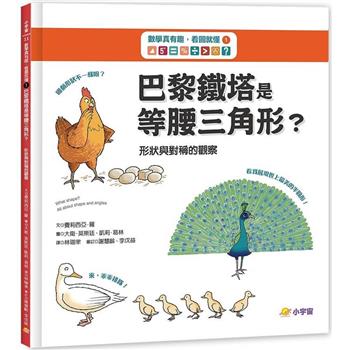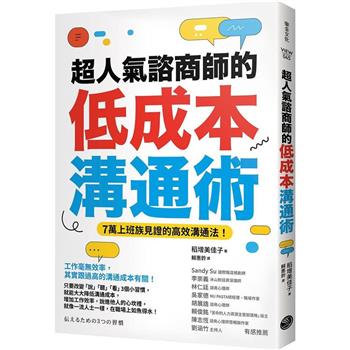第一章
醫學倫理學何以令人激動?
「我沒那麼多時間去思考,」他用一種略帶防衛的語氣說,「我只是把我成千上萬的冰淇淋賣給大家。哲學就留給醉漢們吧。」
(冰淇淋攤販,摘自MalcomPryce,AberystwythMonAmour)
醫學倫理學會引起各種人的興趣:既有思想家,也有實幹家;既有哲學家,也有男男女女的活動家。它涉及一些重大的道德問題:例如安樂死和殺人的道德壓力。它還將我們領入了政治哲學的領域。受到必然限制的衛生保健資源應當如何分配?決策程序應當是怎樣的?醫學倫理學還與法律問題相關。醫生實施安樂死總是一種犯罪行為嗎?甚麼時候才能違背一個精神病人的意願對其進行治療?此外,醫學倫理學還探討了一個值得關注的世界性議題,即富國與貧國之間的正確關係。
現代醫學創造了新的道德選擇,並給我們已有的傳統觀點帶來了挑戰。克隆給許多電影帶來了靈感,也給人們帶來了很多擔憂。創造半人半獸生物的可能性已經離我們不遠了。生殖技術引出了一個很抽象的問題:我們應當如何考慮那些尚未出生——也可能從不會存在的生命的利益?這個問題讓我們從醫學以外的角度來考慮我們應對人類的未來承擔的責任。
從形而上學到日常實踐都屬於醫學倫理學的範疇。醫學倫理學不僅涉及這些大問題,而且也涉及日常的醫學實踐。醫生與人們的性命密切相關,日常生活中充滿了道德壓力。一位有些癡呆的老年婦女患上了一種急性的、危及生命的疾病。是應該讓她在醫院裏接受所有現有的藥物和技術治療,還是應該讓她舒服地待在家裏養病呢?一家人無法達成一致。這件事可能根本無法上頭版頭條;但是,正如奧登筆下的古典畫家所認為的那樣,大多數時間裏,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平常的事就是重要的事。我們在從事醫學倫理學研究時,必須準備好與理論進行抗爭,花時間思考並發揮想像力。但是我們還必須做好務實的準備:能夠採用一種嚴肅、切實的方法。
我自己對於醫學倫理學的興趣是從理論開始的,當時我在讀一個有哲學課程的學位。但當我進入醫學以後,我的愛好更多地偏向了實用。決定總是要做的,病人也總是要救助的。我被訓練成了一位精神病醫生,倫理學在我作為醫生和臨床學家的工作中僅成為了我的一絲興趣。隨着臨床經驗的積累,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倫理價值是醫學的核心。我的訓練中強調得比較多的是臨床決策中應用科學依據的重要性。很少有人會想去論證,更不會有人注意到這些決策背後的倫理假設的正確性。因此我更多地向醫學倫理學靠攏,期待醫學實踐以及患者能從倫理學推理中受益。我喜歡高度理論化的東西,也喜歡從事回到普遍性與抽象性的純粹推理,但同時我也密切關注着實踐的發展。我還探討了非同一性問題(第四章)這一哲學「雷區」,因為我相信這一問題與醫生和社會需要做出的決定是相關的。
哲學家與文化歷史學家以賽亞.柏林(IsaiahBerlin)對托爾斯泰的一篇評論開頭如下:
希臘詩人阿基洛科斯的詩段中有一句詩寫道:
「狐狸知道許多事情,而刺猬知道一件大事。」
柏林隨後提出,打比方來說,狐狸與刺猬之間的差別可以標示出「作家與思想家之間最深刻的區別之一,而且這個區別也許可以適用於整個人類」。刺猬代表了將所有事情歸攏到一個核心見解的人,這一見解是:
根據他們的理解、想法和感覺建立的一個大體一致或能夠清楚表達的系統——一條有組織的普遍原則,根據這一原則,他們本身和他們的言語都有重要意義。
狐狸代表了:
那些追求許多目標的人,這些目標常常互無關聯甚至相互矛盾,只有在某種實際的情形下才有可能有聯繫,⋯⋯[他們]生活,活動,抱有一些獨立的而非統一的觀點⋯⋯抓住各種體驗的精髓⋯⋯卻沒有⋯⋯試圖將它們納入⋯⋯任何一種不變的、包含一切的⋯⋯單一的內在視角。
柏林在眾人中舉出了刺猬型的人:但丁、柏拉圖、陀斯妥耶夫斯基、黑格爾、普魯斯特等。他還舉出了狐狸型的人:莎士比亞、希羅多德、亞里士多德、蒙田和喬伊斯。柏林還認為托爾斯泰是天生的狐狸,但卻被誤以為是刺猬。
我是一隻狐狸,或者至少我的意願是做一隻狐狸。我欽佩那些努力創造一個單一視角的人在智慧上的嚴謹,但我更喜歡柏林所說的狐狸豐富、矛盾和無序的視角。本書中,我無意用一種單一的道德理論來討論不同的問題。每一章我都用一個特定的立場來討論一個議題,無論何種討論方法對我來說似乎都是最相關的方法。我在不同的章節裏討論了不同的領域:遺傳學、現代生殖技術、資源分配、心理健康、醫學研究等;並且在每個領域都着眼於一個問題。本書的最後我向讀者提出了一些其他的問題和更多的讀物。
貫穿全書的一個觀點是推理與合理性的極端重要性。我認為醫學倫理學本質上是一個理性的學科:它就是要你為所持的觀點給出理由,並隨時準備好根據理由改變你的觀點。因此本書的中部有一章是對多種理性論證工具的討論。儘管我相信理由和證據的極端重要性,但是我心中的狐狸卻發出了一聲警告。清晰的思維以及高度的理性是不夠的,我們需要開發我們的心靈,同樣也需要開發我們的智力。如果沒有正確的敏感性、思想上的一致性與道德上的熱情,就可能會導致糟糕的行為和錯誤的決定。小說家扎迪.史密斯(ZadieSmith)曾寫道:
在英國喜劇小說中,沒有比自認為正確更大的罪惡了。喜劇小說給我們的經驗是,我們道德上的狂熱讓我們變得頑固、膚淺、單調。
我們需要把這個經驗應用到實踐倫理學的任一領域,包括醫學倫理學。
難道還有甚麼能比安樂死這個棘手的問題更適合開始我們的醫學倫理學旅程嗎?
| FindBook |
有 2 項符合
醫學倫理的圖書 |
 |
【牛津通識】醫學倫理 譯者:吳俊華,李方,裘劼人 出版社: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16-09-0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176頁 / 13 x 19.6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醫學倫理
醫學倫理愈來愈令人關注,它涉及一些重大的道德問題,例如安樂死和殺人的道德壓力,它還將我們領入了政治哲學的領域,還有它與法律問題相關,與貧富也有不同的關係等等。比如說安樂死是原則上錯誤的嗎?在精神疾病患者不同意的情況下可否對其進行強制治療?絕經後的婦女能接受輔助生殖?基因檢測資料對誰才能公開?醫療保健資源如何合理分配?
在這本醫學倫理通識小書中,作者收集和整理了許多生動的案例,很有意義也很發人深省,對於生命和醫療的關係提出了新的道德啟示。
作者簡介:
托尼•霍普Tony Hope
牛津大學醫學倫理學教授,精神科名譽顧問醫師,牛津大學醫療倫理和溝通中心的創立者。與人合著有Oxford Handbook of Clinical Medicine和Manage Your Mind。
譯者簡介:
吳俊華 專業譯者
李 方 專業譯者
裘劼人 專業譯者
TOP
章節試閱
第一章
醫學倫理學何以令人激動?
「我沒那麼多時間去思考,」他用一種略帶防衛的語氣說,「我只是把我成千上萬的冰淇淋賣給大家。哲學就留給醉漢們吧。」
(冰淇淋攤販,摘自MalcomPryce,AberystwythMonAmour)
醫學倫理學會引起各種人的興趣:既有思想家,也有實幹家;既有哲學家,也有男男女女的活動家。它涉及一些重大的道德問題:例如安樂死和殺人的道德壓力。它還將我們領入了政治哲學的領域。受到必然限制的衛生保健資源應當如何分配?決策程序應當是怎樣的?醫學倫理學還與法律問題相關。醫生實施安樂死總是一種犯罪行為嗎?甚麼...
醫學倫理學何以令人激動?
「我沒那麼多時間去思考,」他用一種略帶防衛的語氣說,「我只是把我成千上萬的冰淇淋賣給大家。哲學就留給醉漢們吧。」
(冰淇淋攤販,摘自MalcomPryce,AberystwythMonAmour)
醫學倫理學會引起各種人的興趣:既有思想家,也有實幹家;既有哲學家,也有男男女女的活動家。它涉及一些重大的道德問題:例如安樂死和殺人的道德壓力。它還將我們領入了政治哲學的領域。受到必然限制的衛生保健資源應當如何分配?決策程序應當是怎樣的?醫學倫理學還與法律問題相關。醫生實施安樂死總是一種犯罪行為嗎?甚麼...
»看全部
TOP
目錄
1 第一章 醫學倫理學何以令人激動?
9 第二章 安樂死:有益的醫學實踐還是謀殺?
31 第三章 為何低估「統計學上的」人會付出生
命的代價?
51 第四章 至少目前為止還不存在的人
71 第五章 推理工具箱
91 第六章 對待精神錯亂者的不一致性
105 第七章 現代遺傳學如何考驗傳統保密?
119 第八章 醫學研究是新帝國主義?
133 第九章 家庭醫學遭遇上議院
151 參考書目
155 推薦閱讀書目
9 第二章 安樂死:有益的醫學實踐還是謀殺?
31 第三章 為何低估「統計學上的」人會付出生
命的代價?
51 第四章 至少目前為止還不存在的人
71 第五章 推理工具箱
91 第六章 對待精神錯亂者的不一致性
105 第七章 現代遺傳學如何考驗傳統保密?
119 第八章 醫學研究是新帝國主義?
133 第九章 家庭醫學遭遇上議院
151 參考書目
155 推薦閱讀書目
TOP
商品資料
- 作者: Tony Hope 譯者: 吳俊華、李方、裘劼人
- 出版社: 牛津大學 出版日期:2016-09-01 ISBN/ISSN:9780199433735
- 語言:繁體中文 裝訂方式:平裝 頁數:176頁 開數:32開(13X19.6 CM)
- 類別: 中文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