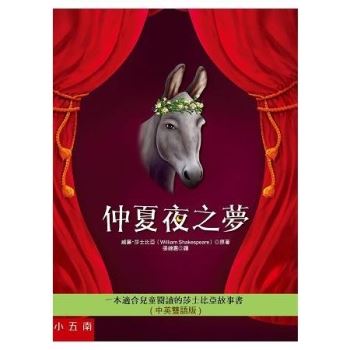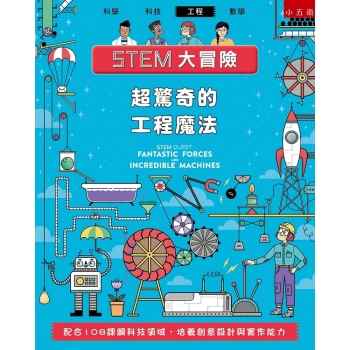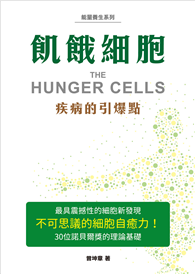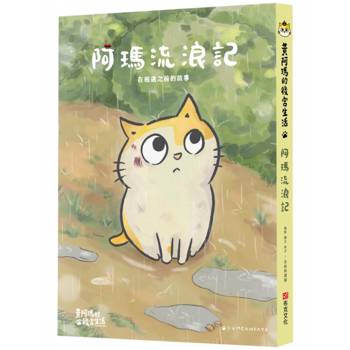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套上下兩冊的巨著,是全球80多位學者對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最新發現、研究成果。
毛澤東和他發動的文革是一場顛覆了中國社會、人類文明的政治運動,其基因仍在、遺毒猶烈,決定和影響著中國當今和未來。正因為如此,中共將文革研究視為禁區,試圖掩蓋遠未被揭示徹底的罪惡,他們擔心其掌權的法理基礎被摧毀。
所以,文革發生在中國,真正獨立、專業的研究會議卻只能在美國召開。由美國著名文革研究專家宋永毅、著名中國事務教授林培瑞等召集的文革50周年國際研討會,2016年在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舉行,與中國對文革的禁聲,形成了諷刺性對比。
這一會議聚集了來自美、加、德、日、中國香港、澳門等地的學者,更有十多位來自中國大陸的重量級文革專家。這樣的會議規模和陣容,已屬「史無前例」,而且新人輩出,新說迭起,如一些媒體所言,實為一次迄今為止「規模最大、水平最高」的有關文革的國際學術會議。
會議向世人昭示了海內外史學家們探究歷史真相的勇氣和堅韌,對於重構中華民族對文革的集體記憶,極具戰略意義。
記錄會議成果的這套巨著,注定成為中國當代歷史的珍藏。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上下)的圖書 |
 |
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共二冊) 出版社:明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2-02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380頁 / 14 x 21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900 |
史地 |
$ 930 |
中文書 |
$ 930 |
中國歷史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上下)
內容簡介
序
前言
韌性博弈後的成果 宋永毅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一百萬字、上下兩冊的题名为《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的巨著是我在美國編纂的第二本有關文革的論文集。十年以前,在文革40周年之際,我也曾受委託組織過大型的國際研討會,並在事後找到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了題名為《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的兩卷本的論文集。
這本新的論文集是今年6月24-26日,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召開的、題名為「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的紀念文革5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的產物。會議的主辦單位有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社會和意識研究中心、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輯委員會。協辦單位有紐約天問聯合學會。但在出版計畫上大有不同的是:早在一年多以前,紐約明鏡出版集團的老總何頻先生得知我們即將組織這一會議時,便慨然拍板決定了這一論文集的出版,充分顯示了一個出版家的良知和眼光。
一
在我編纂這本新的論文集時,內心的感受可謂悲喜交加、五味雜陳。
悲的是:十年前我們相聚紐約開文革40周年研討會時,內心都或多或少地抱著一絲神思遐想:下一個十年能不能在文革的發生地——中國大陸開這樣的研討會?然而,幻想總是溫暖的,現實卻是冰冷的。和十年前相比,中國大陸的新領導人不僅更嚴厲地在國內禁止任何有關文革的學術活動,還想把已經前行了50年的歷史車輪拉回到黑暗的毛澤東時代去。
喜的是:在政客們千方百計掩蓋歷史的同時,還有史學家們堅韌不拔的對真相的揭露。雖然歷史有時會發生短暫的倒退,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客和學者的悠久的博弈中,前者一定是「勝利者」。雖然學者只掌握形而上的「批判的武器」(思想和言論),但在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的構築中,並不一定輸給政客們的形而下的「武器的批判」(警察和監獄)。在這些投身與文革研究的歷史學者身上,我們還看到了自春秋末年齊國史官太史伯三兄弟為纂信史而不畏死的節操和承傳。由於他們正氣的震懾,篡位的君王最後認識到他只能主導當政時期,而史官卻傳承千年中華歷史。中國千年以來的史官們秉承著「史學、史識、史才、史德」,秉持了「險惡矯誣之人,不足以言史」的信念,成為華夏民族歷史真理的捍衛者。
在這次會議中,我們也確實欣慰地看到了韌性博弈後的成果。例如,這一會議聚集了來自美、加、德、日、中、港、澳(門)等地的70多位學者,其中有十位來自中國大陸。他們中有徐友漁、秦暉、王海光、米鶴都、金光耀、李遜、崔衛平等重量級的文革研究專家。此外,會議還收到了朱學勤、唐少傑、董國強、申曉雲、徐海亮等七位大陸著名學者的書面發言和論文。這樣的規模,如一些媒體所言,實屬「史無前例」了。十年前,在紐約召開文革4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時,由於大陸有關方面的阻攔,在上述的知名文革研究專家中,僅有徐海亮教授一人能與會。更令人欣慰的是: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文革也已經成為了一個國際性的學術課題。既然在中國國內無法進行任何公開的學術研討活動,與會的學者、尤其是華裔學者都認為:他們在海外學術自由的環境中組織和召開這樣的大會就責無旁貸。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真相一定要被揭示,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一定要被保存。
二
因為中共當局對文革研究的禁錮和阻攔,文革研究是否後繼有人的問題一直是纏繞著海內外學界的一個憂慮。其實,有關當局的陰暗企圖是一回事,他們能不能使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集體失憶又是另外一碼事。尤其是中華民族的史學有著「以史為鑑」的優良傳統,要利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強迫海內外學界放棄「文革研究」是不可能的。近十年來,不要說海外學界的新生輩層出不窮,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批相當數量的以文革為研究課題的博士研究生。會議的組織者敏銳地發見了這一剛剛浮現的新群體,邀請了六位80後的文革研究新人與會。並以「新一代學人(80後)的文革研究」為題,開啟了大會第一天的首場討論。這六位來自世界各地(美國、德國、中國、澳門)的五位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學者是:陳闖創(美國青年學者)、宋國慶(德國佛萊堡大學漢學研究博士生)、劉成晨(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王芳(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楊雋(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等。
這幾位青年學人儘管都生在文革後,但他們的發言和論文卻有著堅實的史料基礎和新學科知識的底蘊。首先,他們的研究雖然比較微觀,集中在某一個省、市或縣,但都以大量的檔案史料和現場訪談為基礎。例如宋國慶的〈遲到的正義:廣西處理文革亂打死人問題的啟動〉是他近兩年內在廣西查找檔案和田野調查收集口述資料的結果。再如王芳的〈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以滬、漢兩地為例(1966-1967)〉一文,同樣也是她奔波於滬漢兩地調查訪談的結果。為此,他們所梳理的歷史真相都比較可信和全面。其次,雖然他們的研究都帶有個案研究色彩,卻也同時顯現了現代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知識的學養,在理論上也有一定的開拓意義。例如,劉成晨和他導師郝志東合著的英文論文《理解中國的暴力:以一個縣域的土改與文革為例》,是第一次把土改和文革暴力做比較研究的論文,還得出了「1940年代的土改和1960年代-1970年代的文革之間有相當的關聯性,其暴力的機理是一脈相承的」的新結論。對一門學科建設而言,及時推出和鼓勵學術新人具有相當的戰略意義。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洛杉磯研討會不僅給人以文革研究後繼有人的信心,更將沉實地推動該學科今後幾十年內的發展。
韌性博弈後的成果 宋永毅
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一百萬字、上下兩冊的题名为《文革五十年: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的巨著是我在美國編纂的第二本有關文革的論文集。十年以前,在文革40周年之際,我也曾受委託組織過大型的國際研討會,並在事後找到香港田園書屋出版了題名為《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的兩卷本的論文集。
這本新的論文集是今年6月24-26日,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召開的、題名為「毛澤東遺產和當代中國」的紀念文革5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的產物。會議的主辦單位有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社會和意識研究中心、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和《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編輯委員會。協辦單位有紐約天問聯合學會。但在出版計畫上大有不同的是:早在一年多以前,紐約明鏡出版集團的老總何頻先生得知我們即將組織這一會議時,便慨然拍板決定了這一論文集的出版,充分顯示了一個出版家的良知和眼光。
一
在我編纂這本新的論文集時,內心的感受可謂悲喜交加、五味雜陳。
悲的是:十年前我們相聚紐約開文革40周年研討會時,內心都或多或少地抱著一絲神思遐想:下一個十年能不能在文革的發生地——中國大陸開這樣的研討會?然而,幻想總是溫暖的,現實卻是冰冷的。和十年前相比,中國大陸的新領導人不僅更嚴厲地在國內禁止任何有關文革的學術活動,還想把已經前行了50年的歷史車輪拉回到黑暗的毛澤東時代去。
喜的是:在政客們千方百計掩蓋歷史的同時,還有史學家們堅韌不拔的對真相的揭露。雖然歷史有時會發生短暫的倒退,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客和學者的悠久的博弈中,前者一定是「勝利者」。雖然學者只掌握形而上的「批判的武器」(思想和言論),但在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的構築中,並不一定輸給政客們的形而下的「武器的批判」(警察和監獄)。在這些投身與文革研究的歷史學者身上,我們還看到了自春秋末年齊國史官太史伯三兄弟為纂信史而不畏死的節操和承傳。由於他們正氣的震懾,篡位的君王最後認識到他只能主導當政時期,而史官卻傳承千年中華歷史。中國千年以來的史官們秉承著「史學、史識、史才、史德」,秉持了「險惡矯誣之人,不足以言史」的信念,成為華夏民族歷史真理的捍衛者。
在這次會議中,我們也確實欣慰地看到了韌性博弈後的成果。例如,這一會議聚集了來自美、加、德、日、中、港、澳(門)等地的70多位學者,其中有十位來自中國大陸。他們中有徐友漁、秦暉、王海光、米鶴都、金光耀、李遜、崔衛平等重量級的文革研究專家。此外,會議還收到了朱學勤、唐少傑、董國強、申曉雲、徐海亮等七位大陸著名學者的書面發言和論文。這樣的規模,如一些媒體所言,實屬「史無前例」了。十年前,在紐約召開文革4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時,由於大陸有關方面的阻攔,在上述的知名文革研究專家中,僅有徐海亮教授一人能與會。更令人欣慰的是: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文革也已經成為了一個國際性的學術課題。既然在中國國內無法進行任何公開的學術研討活動,與會的學者、尤其是華裔學者都認為:他們在海外學術自由的環境中組織和召開這樣的大會就責無旁貸。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真相一定要被揭示,中華民族的集體記憶一定要被保存。
二
因為中共當局對文革研究的禁錮和阻攔,文革研究是否後繼有人的問題一直是纏繞著海內外學界的一個憂慮。其實,有關當局的陰暗企圖是一回事,他們能不能使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集體失憶又是另外一碼事。尤其是中華民族的史學有著「以史為鑑」的優良傳統,要利用國家機器的力量強迫海內外學界放棄「文革研究」是不可能的。近十年來,不要說海外學界的新生輩層出不窮,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批相當數量的以文革為研究課題的博士研究生。會議的組織者敏銳地發見了這一剛剛浮現的新群體,邀請了六位80後的文革研究新人與會。並以「新一代學人(80後)的文革研究」為題,開啟了大會第一天的首場討論。這六位來自世界各地(美國、德國、中國、澳門)的五位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學者是:陳闖創(美國青年學者)、宋國慶(德國佛萊堡大學漢學研究博士生)、劉成晨(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王芳(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楊雋(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生)等。
這幾位青年學人儘管都生在文革後,但他們的發言和論文卻有著堅實的史料基礎和新學科知識的底蘊。首先,他們的研究雖然比較微觀,集中在某一個省、市或縣,但都以大量的檔案史料和現場訪談為基礎。例如宋國慶的〈遲到的正義:廣西處理文革亂打死人問題的啟動〉是他近兩年內在廣西查找檔案和田野調查收集口述資料的結果。再如王芳的〈文革中的工人派系政治——以滬、漢兩地為例(1966-1967)〉一文,同樣也是她奔波於滬漢兩地調查訪談的結果。為此,他們所梳理的歷史真相都比較可信和全面。其次,雖然他們的研究都帶有個案研究色彩,卻也同時顯現了現代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理論知識的學養,在理論上也有一定的開拓意義。例如,劉成晨和他導師郝志東合著的英文論文《理解中國的暴力:以一個縣域的土改與文革為例》,是第一次把土改和文革暴力做比較研究的論文,還得出了「1940年代的土改和1960年代-1970年代的文革之間有相當的關聯性,其暴力的機理是一脈相承的」的新結論。對一門學科建設而言,及時推出和鼓勵學術新人具有相當的戰略意義。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洛杉磯研討會不僅給人以文革研究後繼有人的信心,更將沉實地推動該學科今後幾十年內的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