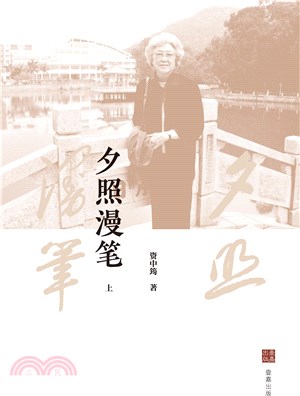本書是繼2011年《資中筠自選集》、2013年《老生常談》之後,著名學者資中筠的又一個自選集,收入其2013-2022年間尚未入集的文章,以及講座整理稿、訪談記錄。全書共兩卷、八輯,涉及學術思考、公共話題、私人生活等各個方面。上卷四輯為:文化教育、公益與社會改良、閒情與雜感、訪談錄,下卷四輯為:歷史與救國、世界觀察、思故人、音樂家園。
「難求於世有濟,但行此心所安。」資先生修改曾國藩名句自況,不阿世,不迎俗,宣導中國人擺脫「帝師」情結,洋洋五十萬言,所思所慮,還是「生於斯、長於斯、終老於斯的本鄉本土。」
--------
本文集中有一篇《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诠释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广为流传中,"天下"常被代以"国家"。其实顾的原意是把"天下"与"国家"分开,明确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另外一篇最新写的《国际研究的反思》,最后一段主张学者采取更为超脱、更高瞻远瞩的立场,与政客拉开距离。这是我的一贯治学和发声的态度,但很少为人所理解。--摘自资中筠《自序》
我们经历过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一个人受到万民的膜拜,这是制度问题。在集权的制度下,没有人敢发表不同的意见。但假如没有人拜,这个神就不存在了。事实是,仍有很多人习惯于崇拜皇权,认为掌权者即是皇帝,总会做出英明的决断,坏事都是底下人干的,天皇永远圣明,这就是一种文化,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制度会鼓励一种文化。--摘自资中筠《从文化制度看当代中国的启蒙》
本書特色
|獨立思想之華章,自由精神之光芒|
九十二歲之高齡,筆耕不輟,中國仍然敢於發聲的知識分子,最受尊敬的聲音──資中筠最新自選集(2013-2022)
| FindBook |
有 3 項符合
夕照漫筆.上卷(簡體版)(POD)的圖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夕照漫筆.上卷(簡體版)(POD)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資中筠
國際問題及美國研究資深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1947年考入燕京大學,後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多年從事對外關係工作。1980年代參與創辦《美國研究》雜誌與中華美國學會,創辦中美關係史研究會並任第一、二屆會長,主持並參加各種國內外學術活動。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後,著述尤豐,除專業國際研究外,旁涉中西歷史文化,近年來關注中國現代化問題,撰有大量隨筆、雜文。此外,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
資中筠
國際問題及美國研究資深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1947年考入燕京大學,後轉入清華大學外文系,畢業後多年從事對外關係工作。1980年代參與創辦《美國研究》雜誌與中華美國學會,創辦中美關係史研究會並任第一、二屆會長,主持並參加各種國內外學術活動。1996年從社科院美國所退休後,著述尤豐,除專業國際研究外,旁涉中西歷史文化,近年來關注中國現代化問題,撰有大量隨筆、雜文。此外,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
目錄
一、文化与教育
1. 中文修养是一种文化底蕴
2. 再谈学中文
3. 周有光集代序
4. 公益与教育
5. 历届留学生与报效祖国
6. 生祭《炎黄春秋》
7. 知识分子感言—写在杨绛先生仙逝之际
8. 从文化制度看当代启蒙
9. 坎坷而幸运的创业
10. 改开初期学术交流轶事
11. 祝宗璞《野葫芦引》终卷出版及九十大寿
12. 斯文何以扫地
13. 时代与青年
14. 哀清华
15. 文摘三则
二、公益与社会改良
1. 无心插柳柳成荫
2. 美国财富向善历程
3. 一家山区幼儿园
4. 21世纪的新公益
5. 新公益的最新发展
6. 新公益与社会改良
7. 传一基金会
8. 捐赠何为
三、闲情与杂感
1. 我们都是看客
2. 皇帝的新衣现代版
3. 讲真话为什么那么难?
4. 奢侈的会诊
5.《费加罗的婚礼》与美国独立
6. 闲话过敏症
7. 杀君马者道旁儿
8. 照顾文化差异?
9. 壬寅述怀
10. 铁链女与战争
四、访谈录
1. 我们这一代人:中国新闻周刊
2. 一位老知识分子的老生常谈:上海《生活月刊》
3. 关于《二十世纪的美国》:南方人物周刊
4. 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冷漠:新京报
5. 关于《九十自述》:跨文化思想家杂志
1. 中文修养是一种文化底蕴
2. 再谈学中文
3. 周有光集代序
4. 公益与教育
5. 历届留学生与报效祖国
6. 生祭《炎黄春秋》
7. 知识分子感言—写在杨绛先生仙逝之际
8. 从文化制度看当代启蒙
9. 坎坷而幸运的创业
10. 改开初期学术交流轶事
11. 祝宗璞《野葫芦引》终卷出版及九十大寿
12. 斯文何以扫地
13. 时代与青年
14. 哀清华
15. 文摘三则
二、公益与社会改良
1. 无心插柳柳成荫
2. 美国财富向善历程
3. 一家山区幼儿园
4. 21世纪的新公益
5. 新公益的最新发展
6. 新公益与社会改良
7. 传一基金会
8. 捐赠何为
三、闲情与杂感
1. 我们都是看客
2. 皇帝的新衣现代版
3. 讲真话为什么那么难?
4. 奢侈的会诊
5.《费加罗的婚礼》与美国独立
6. 闲话过敏症
7. 杀君马者道旁儿
8. 照顾文化差异?
9. 壬寅述怀
10. 铁链女与战争
四、访谈录
1. 我们这一代人:中国新闻周刊
2. 一位老知识分子的老生常谈:上海《生活月刊》
3. 关于《二十世纪的美国》:南方人物周刊
4. 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冷漠:新京报
5. 关于《九十自述》:跨文化思想家杂志
序
序言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在专业著述之外开始写一些随笔杂文,或长或短,隔几年出一本集子。2011年应广西师大出版社之邀,从三十年来的文字中选了一些自以为有长远价值的,按题材性质分五卷,出了《资中筠自选集》,又称《五卷集》。这套文集获得了一些关注,还得了各种图书奖。随后于2013年又将以后两年来的文字集结出版,题为《老生常谈》。自那以后,时格势禁,没有再出文集。如今应刘雁女士之邀,把2013年以后尚未入集的文字在这里集结出版。这是本人第一次中文著作在外国出版,这本书竟首先在海外与读者见面,是我未料想到的。
本书文章截止于2022年。其中少部分曾发表在国内一些报刊。2015年在朋友建议和帮助下开了微信公号,创作更加随性,读者点击率也日益增加。本书大部分文章是曾在公号上发表的。这个公号共存活三年,正在方兴未艾之时,2017年秋被“永久屏蔽”。但是互联网时代文网再密也有空隙,实际上我并未三缄其口,除撰写的文章外,应邀做讲座或访谈,本书有些是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所以内容驳杂,体例也无一定之规,即兴发言不像写文章,措辞可能不太严谨。不过不论何种形式,都是个人有所思、有所感,经过思考,出自肺腑之言。
专业是研究美国,所以有关国际评论的文章也大多与美国有关。关于把一个国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研究,我在1987年《美国研究》创刊号上已为文阐述一己之见。总之是把美国竖切面、横切面,作为一种文明全面考察,帮助国人增进了解,而不是为政府出谋划策,或为外交建言。当然此宗旨不为主流社科界所接受。只是自己的研究本着这一原则,主要代表性的专著有《二十世纪的美国》和《美国十讲》,以及几本论文集。另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关注领域,就是百年来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发展,为此写了专著,第一版题为《散财之道》,以后随着发展不断增订,最后一版题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因是之故,就这个专题接受了很多采访,应邀做了许多讲座。本文集设“公益”一栏,选入我最近几年的几篇文稿。美国是成熟的公民社会,NGO非常发达,进入后工业时代在这个领域又有所创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受到学界的关注远远不够。希望这一栏目的文章对读者有所帮助。
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分化变本加厉,特别是最近两届大选,不但在有选举权的华裔美国人中争议激烈,而且在中国的知识界也出现热烈的“川粉”现象。本人也曾被要求“表态”。我坚持作为中国人只能隔岸关火,绝不选边站。而且根据自己的研究角度,从来关注点不跟着大选跑,因为我不认为在美国制度下,总统能决定国运。
实际上我真正关注的当然是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本乡本土。借用杨奎松教授一本书的题目:忍不住的关怀。我关心的是民族精神,与研究外国一样,写作是以普通中国人为读者,绝对不作向上建言、献策之举。中国知识分子常有一种“帝师”情节,所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我竭力提倡的是摆脱这种情节而忧其民。本文集中有一篇《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诠释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广为流传中“天下”常被代以“国家”。其实顾的原意是把“天下”与“国家”分开,明确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另外一篇最新写的《国际研究的反思》,最后一段主张学者采取更为超脱、更高瞻远瞩的立场,与政客拉开距离。这是我的一贯治学和发声的态度,但很少为人所理解。
最后摘录《自选集》序言的片段:
-----
(2000年)的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
以上写于11年前,大体上仍能代表当前写作动力和心情。最后一段提到日本核泄漏的天灾人祸。科学发展对人类的祸福一直是我关切的话题,见本书《科学与人类》一文。但是再“杞人忧天”,也没有想到今日在国内竟身处这样类似荒诞剧的防病毒“封控”局面;外部世界竟然发生了超级武器库卷入的真正的“热战”。掌控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库的政客们凭理性克制了近80年之后,竟有失控的危险。与此同时,那些创新奇才似乎能将太空玩弄于股掌之上。人类、地球向何处去,已非我这风烛残年的凡夫俗子所能计。
2022年5月,九十二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在专业著述之外开始写一些随笔杂文,或长或短,隔几年出一本集子。2011年应广西师大出版社之邀,从三十年来的文字中选了一些自以为有长远价值的,按题材性质分五卷,出了《资中筠自选集》,又称《五卷集》。这套文集获得了一些关注,还得了各种图书奖。随后于2013年又将以后两年来的文字集结出版,题为《老生常谈》。自那以后,时格势禁,没有再出文集。如今应刘雁女士之邀,把2013年以后尚未入集的文字在这里集结出版。这是本人第一次中文著作在外国出版,这本书竟首先在海外与读者见面,是我未料想到的。
本书文章截止于2022年。其中少部分曾发表在国内一些报刊。2015年在朋友建议和帮助下开了微信公号,创作更加随性,读者点击率也日益增加。本书大部分文章是曾在公号上发表的。这个公号共存活三年,正在方兴未艾之时,2017年秋被“永久屏蔽”。但是互联网时代文网再密也有空隙,实际上我并未三缄其口,除撰写的文章外,应邀做讲座或访谈,本书有些是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所以内容驳杂,体例也无一定之规,即兴发言不像写文章,措辞可能不太严谨。不过不论何种形式,都是个人有所思、有所感,经过思考,出自肺腑之言。
专业是研究美国,所以有关国际评论的文章也大多与美国有关。关于把一个国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研究,我在1987年《美国研究》创刊号上已为文阐述一己之见。总之是把美国竖切面、横切面,作为一种文明全面考察,帮助国人增进了解,而不是为政府出谋划策,或为外交建言。当然此宗旨不为主流社科界所接受。只是自己的研究本着这一原则,主要代表性的专著有《二十世纪的美国》和《美国十讲》,以及几本论文集。另外还有一个独特的关注领域,就是百年来美国公益基金会的发展,为此写了专著,第一版题为《散财之道》,以后随着发展不断增订,最后一版题为《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因是之故,就这个专题接受了很多采访,应邀做了许多讲座。本文集设“公益”一栏,选入我最近几年的几篇文稿。美国是成熟的公民社会,NGO非常发达,进入后工业时代在这个领域又有所创新,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受到学界的关注远远不够。希望这一栏目的文章对读者有所帮助。
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分化变本加厉,特别是最近两届大选,不但在有选举权的华裔美国人中争议激烈,而且在中国的知识界也出现热烈的“川粉”现象。本人也曾被要求“表态”。我坚持作为中国人只能隔岸关火,绝不选边站。而且根据自己的研究角度,从来关注点不跟着大选跑,因为我不认为在美国制度下,总统能决定国运。
实际上我真正关注的当然是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本乡本土。借用杨奎松教授一本书的题目:忍不住的关怀。我关心的是民族精神,与研究外国一样,写作是以普通中国人为读者,绝对不作向上建言、献策之举。中国知识分子常有一种“帝师”情节,所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我竭力提倡的是摆脱这种情节而忧其民。本文集中有一篇《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诠释顾炎武的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广为流传中“天下”常被代以“国家”。其实顾的原意是把“天下”与“国家”分开,明确说“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另外一篇最新写的《国际研究的反思》,最后一段主张学者采取更为超脱、更高瞻远瞩的立场,与政客拉开距离。这是我的一贯治学和发声的态度,但很少为人所理解。
最后摘录《自选集》序言的片段:
-----
(2000年)的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知识分子与道统》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
以上写于11年前,大体上仍能代表当前写作动力和心情。最后一段提到日本核泄漏的天灾人祸。科学发展对人类的祸福一直是我关切的话题,见本书《科学与人类》一文。但是再“杞人忧天”,也没有想到今日在国内竟身处这样类似荒诞剧的防病毒“封控”局面;外部世界竟然发生了超级武器库卷入的真正的“热战”。掌控足以毁灭人类的武库的政客们凭理性克制了近80年之后,竟有失控的危险。与此同时,那些创新奇才似乎能将太空玩弄于股掌之上。人类、地球向何处去,已非我这风烛残年的凡夫俗子所能计。
2022年5月,九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