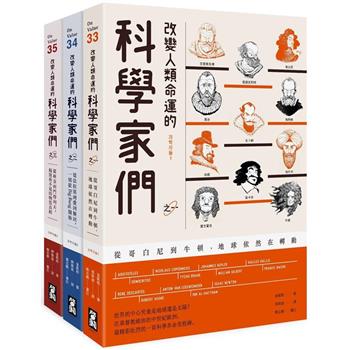後記
穿越城市的列車,穿越自我的光芒
『這世上沒有人,沒有任何人有權為她(過世的母親)哭泣。我也像她一樣,覺得已經準備好重新再活一次。彷彿那場暴怒淨化了我的苦痛,掏空了我的希望;在布滿預兆與星星的夜空下,我第一次敞開心胸,欣然接受這世界溫柔的冷漠。體會到我與這份冷漠有多麼貼近,簡直親如手足。我感覺自己曾經很快樂,而今也依舊如是。為了替一切畫上完美的句點,也為了教我不覺得那麼孤單,我只企盼行刑那天能聚集許多觀眾,以充滿憎恨和厭惡的叫囂來送我最後一程。』(註一)
這是卡繆的小說《異鄉人》的結局。在養老院的母親過世以後,男主角莫梭孑然一身,無依無靠、恍恍惚惚,竟在無意間失手殺了陌生人。在法庭上他被判刑死罪,原因竟然不是出自對死者的憐憫,而是因為沒有在母親的喪禮流淚的莫梭,早已被眾人判為無情的殺手。莫梭的內心並不能夠明白,他認為自己過去僅是誠實地面對生活,在經常使人暈眩的現實中孤獨行走,卻因為一次意外的決策遭到世俗的審判。如今,他將因道德的不完善而被排除於社會之外。臨死之前他終於體悟,自身的孤獨就是存在的一切,虛無就是存在本身。他終於釋懷了。相對於肉體的死亡,他的精神諷刺地獲得新生。
讀完《異鄉人》的結局,我開始寫《台北變形記》。
*****
先談談我成長的台北。
我出生於一九八八年的台北,前一年台灣解嚴,後一年柏林圍牆倒塌,世界處於自由解放的氛圍,慶祝著繁榮開闊的新世界即將到來。當時擠身亞洲四小龍的台灣,在經濟發展、人文思潮上一片繁景,首善之都台北更是充滿這樣的氣息,許多人來到都會區爭取更好的工作,對未來滿懷憧憬與期盼。然而時日過去,經濟的泡沫被吹得就要破開,都市逐漸顯露它的無情──孤獨和挫折埋伏在生活中,使得日日夜夜賺取財富的都會人們,同時感受到空虛的內在。有時半夜驚醒,他們會感到自己如推石的薛西弗斯,終日做著看不到終點的繁瑣工作。這種精神的匱乏感與繁榮的經濟表象形成強烈對比,時常縈繞在我們的生活。(註二)
我出生的那一年,台鐵淡水線被拆除了,城市將迎來新的台北捷運。
一九九六年,第一條台北捷運木柵線開通行駛;隔年,原台鐵淡水線上的捷運淡水線也接續啟用。當時還是孩童的我,站在彩色電漿電視前面,看著新聞播映著捷運開通行駛的熱鬧模樣,並不知曉那將是我未來生活的重要的一部分。往後幾年,捷運新店線、中和線、南港線、板橋線也陸續啟用。考上市區高中的我開始搭乘捷運通勤,每天必須從淡水線搭至台北車站轉乘,再擠上最擁擠的板南線。猶記得每日早晨,我擠在難以動彈的捷運車廂中,腦中想著升學、感情、友誼的煩惱。(雖然也有快樂的時刻,但是留下的印象並不多)於是,總是擁擠的捷運車廂和青春的憂鬱、壓抑、悲傷和憎怒逐漸重疊在一起,變成一種陰暗黏膩的城市印象。彼時我並沒有發覺,城市已將空洞的種子種植在我的身上,終日奔跑在地面之下。
二〇一三年,我離開家鄉前往英國念書。初到異國居住的我驚覺自己對世界的一無所知,在短短兩年間,我不斷與各國友人進行交流,努力適應不熟悉的文化。我學習到許多嶄新的事物,卻也頻頻回望自己的故鄉──當時的我體悟到,若不能好好瞭解自己的過往,便無法向他人妥善介紹自己。也就是在那段期間,台灣發生了太陽花學運、北捷隨機殺人事件和高雄氣爆事故;有賴於網際網路,生活在倫敦的我也能經由社群媒體即時知道故鄉正在發生的事情。在故鄉發生許許多多的紛擾時刻,我也在世界的另外一端懸著擔憂的心,過著魂不守舍、茶飯不思的生活。那個時候,就像與故鄉的人們站在一起般,我也覺得自己參與了台灣社會的重要變動。
然而兩年過去,當我從英國回到故鄉台灣,卻發現自己仍然是個缺席的人。我並沒有真正參與社會改變的時刻,只不過是經由網路參與了其中一部分。我像是再度成為異鄉人一般,感受到自己早已不是過往的自己,台北也不是我在異鄉重複建構的那個台北。巨大的隔閡阻擋在我和故鄉之間,每當我獨自搭上捷運時,總感覺像是從一個夢境穿梭至另外一個夢境。就是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創作小說《台北變形記》。
*****
《台北變形記》於二〇一五年開始撰寫。年初,我剛從英國歸來,正處於求職階段,時常逗留在圖書館中閱讀研習。讀完小說《異鄉人》的我,正巧看見「台北文學獎」的徵件,便決定來試試看許久沒有寫的短篇小說。實在沒有想到,這一寫就是三年的時光,直到二〇一八年才階段性完稿。
《台北變形記》從一個短篇小說的發想,逐漸增加故事的份量,最後演變成一個中篇小說。事出有因。首先,我動筆以後才發現,原來奇幻小說需要足夠的篇幅才能使讀者認識虛構的背景,而原本預期的篇幅是無法盡述的;其次,自從開始寫作以後,我竟感到自己已經無法停止──我像是嘔吐一樣將心中積淤多年的事物盡數吐露出來,最終成為一部富有幻想的自傳型小說。
喜愛文學的讀者應能迅速聯想,《台北變形記》的原形正是卡夫卡的經典作品《變形記》。小說《變形記》描述葛雷戈一覺醒來變成一隻黑蟲,過去日日夜夜盡忠職守、勤奮工作的他,如今為無法外出工作感到萬分焦急。葛雷戈的內心深處懼怕,自己就要變成外人眼中的無用害蟲。一夕之間的轉變,竟無情顯露出日常的脆弱,就連朝夕相處的家人也莫可奈何。讀完卡夫卡的《變形記》,我除了深有所感之外,也不禁思索:小說中葛雷戈所惶懼的處境,在現代社會是否依舊如此呢?一百年過去,我們的社會是否對於個體的差異化更加寬容呢?而對照卡夫卡的《變形記》與卡繆的《異鄉人》,裡頭竟存在著一種內在議題的強烈相似──主角都是因為主體的差異而感覺到被環境排擠,進一步感受到存在的危機。我不禁想像,倘若小說的主角們處於現代社會,是否已經能夠坦然自處?
結合奇幻元素和哲學詰問,《台北變形記》可以說是一本「哲幻小說」。我從哲學的問題出發,架構出一個虛構的世界,讓主人翁在其中遊走探索──透過「桃花源」探問起源、透過「奧林帕斯」探問信念、透過「烏托邦」探問理想、透過「亞特蘭提斯」探問命運。除了弗朗茨懷抱著存在的堪慮,在夢境中找尋生活的意義之外,巨蛾摩托、少女愛麗絲、少年賈寶玉,也分別來到夢境中尋求種族、性別、愛情的解惑。此外,《台北變形記》以夢境為主要架構,在弗朗茨經歷夢的探索之際,同時出現三個關於台北的夢中夢。我試圖透過夢的虛幻、夢中夢的雙重虛幻,去探討虛構的邊界、夢境的邊界、記憶的邊界,以及自我的邊界。而透過故事的發展,我逐漸體悟到,也許這正是身處數位時代的人們所必須面對的議題之一。
*****
寫作是貼合的技藝,將生命的所思所想,透過文字的揉合產生文學。
在《台北變形記》中,我嘗試不同的創作方法,讓閱讀者體驗內在的轉變。讀完應不難發現,除了傳統的文字閱讀之外,這本書需要動用更多感官進行思索。這也是為什麼時隔數年,我仍希望《台北變形記》以紙本的方式與讀者見面──唯有透過紙本的閱讀,才能全然體驗《台北變形記》的故事。在此,我要感謝一路幫助自己的人,包含陪伴我創作的親人、愛人和朋友,以及協助將這本書出版成冊的設計奕凱、編輯桓瑋。
誠實地說,創作的時候總是最孤獨的,獨自走在未知的途徑探索,卻也找到最幸福的事物。「我所要做的事情,只有誠實地面對文學而已。」每天睜開眼睛我都必須如此對自己說。
曾幾何時,我開始產生一種錯覺,認為自己的生命只會到三十二歲便結束。因此在寫作時,儘管遭遇許多孤獨與困境,我也告訴自己要把握時間完成,不留遺憾。只有時時刻刻將死亡捧在眼前,才能讓生活顯現出它的價值來。我常幻想自己像是敲打雕像的米開朗基羅,不斷做著文學的苦工,自迷霧一般的人生取出真正的價值;也是在如此辛勞之中,我逐漸感到《台北變形記》帶我觸摸到某種文學的核心。幸而在三十歲的時候,《台北變形記》的寫作終於告一個段落。而使人感到驚異的是,我竟感覺自己可以活下去了。是的,在死亡的陰影被印刻在小說的同時,我竟也逐漸感到自己有新生的可能。事到如今,我已脫離死亡的陰影,成為一個能夠勇敢直視生活的人。
謝謝文學。只盼這本小說能夠超越生命,成為一種支持的力量,陪伴更多人走下去。敬每一個認真活著的我們,請永遠記得愛。
二〇二三年‧台中
註一:此段摘錄自卡繆《異鄉人》,二〇〇九年,麥田出版,張一喬翻譯。
註二:若要感受八、九〇年代的台北,推薦讀者可看楊德昌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