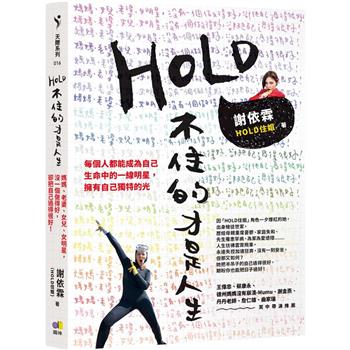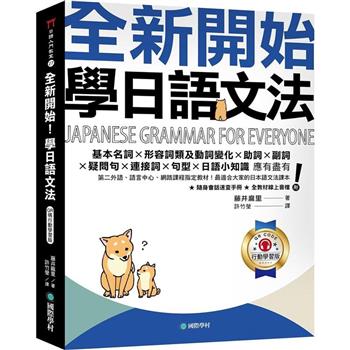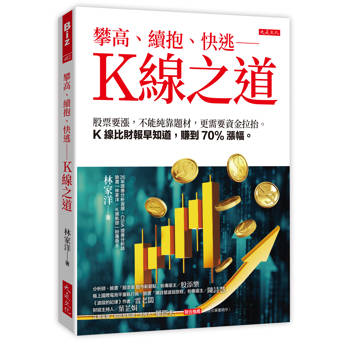17
昨晚,我夢到了從前。
一定是因為昨天無意間翻到的那封信。
那時候如果能夠交給他就好了。
當時的心情,促使現在的我提筆寫下這篇文章。
我將著把少女時的自己,化為文字留下。
但是,我其實沒有完成的自信,若是真的能用文字表達,那時候放棄的自己,沒有把信交給他的自己,又算什麼……
一想到現在寫下的東西,會不會使得那天的那個體驗成為流水帳的一頁,不由得遲疑了起來。
不過,我還是應該把那封信交給他的。在這麼久之後,都過了十三年之後,重新讀了那封沒有交出去的信,面對過去的自己卻掩不住心底的微笑,心情柔軟而溫暖。
「沒關係,把信交給他就好。」好想要這樣跟那天的自己說。
如果當時能夠再成熟一點,能夠勇敢地接受那個不完全的自己,或許結局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現在所寫的,就像是一封信,一封延宕了好久的信。
16
在經過一番掙扎,我決定從轉學的故事開始說起。
我常常對很多無謂的事情感到自卑。要如何說明自己從哪裡來就是其中之一。
在東京,這樣一個人口大量移入的都市,說明自己的出生地,做為話題的交集來說相當重要,但我總是為此感到困擾。
根據父母的話,我是在宇都宮出生的。
可是,我沒有任何關於宇都宮的記憶,更不覺得那裡是自己的根源,只知道那是母親的家鄉,偶爾聽家人說過,僅此而已。
在上小學前,我們搬到秋田,然後遷往靜岡,再去了石川。由於父親在栃木的地方電機製造公司工作,調去各地的分公司或是部門支援是基本義務。
所以直到現在,我沒有對任何地方存有歸屬感,
幼小的年紀在經歷不停地搬家與轉學後,造成這方面的意識薄弱。
無論在哪裡,都不願太過深入。
所在地永遠都只是暫時停留的地方而已。
這就是我從幼年到青春期對外界所抱持的基本態度。
那是在石川縣,國小三年級的冬天──
從母親口中得知,明年又要轉學的消息,這不知道是第幾次。
可以逃離這裡了。在我感受到一絲欣慰的同時,襲來的卻是必須又在異地重新開始的恐懼。
「這次我們要去東京喔!」母親用了像是中了大獎般的口氣說到。
現在想想,以父親的工作來說確實是如此。但我卻覺得“東京”這名詞的音律帶著一股不吉利的聲響。
在那之前,我從來沒有對於學校、街道或是人際關係感到一絲興趣,也打算就這樣繼續消極的冷眼旁觀。
對於沒有餘力的我來說,如果太留心於周邊的事物,一不小心就會跟別人對上眼。
只要跟人有了眼神的交集,言語就會接著攻擊,而那些話對我來說也不是什麼好事。
所以我總是低著頭,保持最大限度地警覺,不願跟外界有任何直接接觸。
轉學這件事,無論如何都是令人害怕的。
面對新的場所,新的面孔,說什麼都開心不起來。
不管轉去哪一間學校,我就是沒有辦法融入。那些不熟悉的口音,地方風情影響下的個性差異,陌生的建築物以及人群,還有還有……同學早已互相認識,卻只有我像局外人這樣不公平的狀態,一切的一切都讓我感到很不安。
每次被迫放身於新的環境之下,我就會嚴重感受到自己的身體正在緊縮,而班上孩子們的一點小動作,無意識的言語,對我來說都是壓力的來源。
曾經想過強硬地吞下恐懼,試著去面對,去抵抗,但這如此困難的事情,我是不可能做到的。
害怕是弱小的記號。
而弱小在孩子不成熟的社交中卻常與可以恣意的傷害別人畫上等號,反正最終都會得到原諒。
我每天都覺得很不舒服,生理上開始起了反應,如同肩膀都在抽搐般地作嘔,甚至希望噁心的感覺能再強烈一點,好像這樣就可以不用去學校一般,然而這個念頭往往使得反胃的狀況更加嚴重。
環境壓力或是氣氛感染引起的反應,我還能夠忍耐,盡量不要深呼吸,保持呼吸的平順,繃起身體,時間自然會過去的。
但真正令我難以忍受的是言語發動的攻擊。
聽覺是無法完全關閉的,就算用手掩住耳朵,只會換來更大音量且強硬不禮貌的言詞。
直到現在我還有一些怎樣都無法接受的字眼,那些孩童用來欺負人時帶有嘲笑意味的話語,而我總是身處在這樣的環境中,有時就連老師也會脫口而出。
我是在這時候就知道,原來大人在小孩的環境久了,也會變成跟小孩子一樣。
這樣只是等待時間過去的日子還會一直持續吧,直到自己死亡的那一天才能了結,但我怎麼樣都想不到脫逃的辦法,應該說從來都不覺得自己能夠真的逃走,沒有反抗的能力的我,只能默默地承受這一切。
那時候,閱讀是我唯一的慰藉。
雖然一個人卻能夠投入在豐富精彩的世界,這是何其美妙的事情。而我也始終這樣覺得,能夠在別的地方找到自己的歸屬,對我來說是一種救贖。
只要翻開書,我就可以變成另外一個人,有著另一種際遇,還能夠擁有超越自己想像的體驗。用心感受的風景往往比現實中所看到的還要繽紛。
我將自己置身於另一邊的世界與現實的日子隔絕,透過書本所學習到的東西才是所謂的知識吧。
那個時期,更具體來說是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最擄獲我心的一本書,是C.S路易士的『獅子.女巫.魔衣櫥』。
衣櫥的深處迎接我的另一個世界,裡頭住著光明的太陽之獸,用巫術控制冰雪的白女巫正計畫着邪惡的叛變……奇幻的畫面逐漸在腦海中展開,深深著迷的我無時無刻都在奇幻世界中神遊。
不止一次,我站在衣櫥前面,雖然知道現實生活中,門後並不存在異世界的入口,但打開的瞬間,還是忍不住小小的期待。
書本就是那魔衣櫥的門,一打開,我的心就掉進了納尼亞王國。
(我想作者路易斯先生應該是有意識的將開門與開書的意象結合吧!)
在想象力的那扇門後,我找到了自己的小世界。
所以在被告知明年春天要搬去東京的時候,我將懷中的書抱得更緊了,那硬硬的書皮都快被鑲進胸口裡一般,我拼命地想把迸出的恐怖給消滅。
即將要面對的事情,自己也清楚的很。
站在講台上,面對著台下的同學們。起初會抱著看熱鬧的心情,然後他們漸漸失去興趣,最後圍繞我的只剩下失望與不耐煩的神情。
我不並認為我可以改變這種狀況,也找不到容許我發聲的那扇窗,因此,我更必須守護那個特別的地方,最後完好的領域。外界帶來的傷害跟痛苦,讓沒有選擇的我只能咬緊牙忍耐。
拼命的壓抑是9歲的自己唯一的課題。
害怕會因為周圍的環境俱增,強烈的恐懼則使我受到更加負面的對待。
無論去到哪裡結果都是一樣的,這叫我如何融入其中,如何找得到自己的容身之處。
在父親的車開到了參宮橋的新公寓時,我的眼神一如往常地冷酷,車外移動的景色,嶄新的街道面貌,沒有在瞳孔中停留過,那又如何呢,停留與否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差別。
反正一切都要重新開始,如同在舊的牆上直接刷上一層新的油漆一般,身心反覆煎熬著,看來新的陣痛又要持續一段時間了。
我側着頭緊靠在車窗上。
要是我的四周也有像玻璃這樣透明且堅硬的帷幕包圍著就好了。
車門打開的瞬間,我的玻璃帷幕也應聲碎裂,那是一種令人不安的聲音。腳底踩著的柏油路,滲透進皮膚的冰冷空氣,那些感覺都讓我極度厭惡,強烈的情緒變化使得淚腺蠢動。
再過不到一個星期,新的學期就要開始了,我必須要一個人去面對。光是用想的就覺得胃在翻攪,肌肉緊繃,名為恐懼的毒隨著血液竄流全身。那時的我,對於死亡感到漠然,總覺得這樣的反應如果一直持續下去,恐怕也活不了多久。這跟自殺意圖不同,當然,我也沒有結束生命的勇氣。只是這樣,一點一點地衰弱,力氣也一點一點地消失,連影子都變得越來越薄,或許自己就會像融化的雪花一般消逝。
其實我並不排斥這樣的結果,當呼吸心跳停止,意識也隨之散去的同時,是否也代表了真正的解脫。尚未成熟的身心,小小的頭腦裡卻充滿如此哀傷的念頭。
然後,我就是在這裡遇見他的,遠野貴樹。
15
講台的高度,讓我感到暈眩。
雖然只比地板高出10公分,但站上去後的視角,面對台下一雙雙的眼睛,我開始發抖,無止境的墜落感湧出,最後那些包圍我的臉孔甚至都扭曲了起來。他們眼睛的深處,笑臉的背後,一定藏著什麼秘密,是我完全不得而知的。唏唏囌囌的笑聲傳來,我的肩膀很自然的縮起,手也收到胸前環抱著。粉筆在黑板上刮出有如尖叫聲般刺耳的噪音,我嚇得回過頭看。嬉鬧聲越來越大,我也越來越無法承受,老師在黑板上寫好了我的名子「篠原明里」,然後把手放在我的肩上,順便將我轉向同學們。
我感覺肩上的手好重好重,肩膀更是僵硬。
「這位就是從今天開始轉學進來的篠原明里同學,大家要好好相處喔!」
女老師笑著說,然後使了眼色要我和同學們問好。
我說:「請多多指教。」
同時彎下腰敬禮,但我的說話的聲音因為緊張而不穩定,呈現偏高的聲響,台下就七嘴八舌地評論了起來。
好像有一個聲音說道:「名字好怪喔!」接下來教室裡就佈滿足以掀起屋頂的笑聲。
每轉學一次就會發生一次,到最後我也覺得自己的名子真的很奇怪。
老師指責了那位說話的同學,但完全不是嚴肅的態度,看來有時候連大人都必須看場合氣氛說話。年幼無知的我還知道,學校老師是不會跟自己站在同一陣線的。
分配好新的座位後,走下講台時才發現自己的膝蓋僵硬的快要碎裂了,踉踉蹌蹌的走在桌子跟桌子之間的小走道。為什麼自己的身體總是不好好聽話呢?想到這裡,不由得悲傷了起來。坐在兩側的同學,雖然低著頭,但眼神不停往我這裡瞟,兩支手,還有晃動的裙擺,都感受得到他們的注視,汗毛也因為警戒而站立。
逐漸狹窄的視野,視線找不到焦點,晃動個不停,我卻怎麼也走不到座位。
就在這個時候──
耳邊傳來小小的一句話,
「沒事的!」
我不由得挺起胸,這才知道原來自己總是駝着背,忽然,我的視線也不再搖晃了。
很想停下腳步找尋聲音來源,但我很快就放棄了,在最後一排的座位坐下。
有很多人朝我看過來,照理來說我會直盯著桌面的木紋發呆才是,但這次我視線卻朝著那些人的方向游走。
是誰?
是誰跟我說話的?
那聲音其實相當微弱,說實話,連自己都無法確定是不是真的聽到了,除了我之外,好像沒有任何人注意到。
但是,那應該是個男生的聲音。
老師敲敲講桌,要大家把注意力拉回來,而我望著前方一排的後腦勺,心裡為了那個人的存在感到疑惑而澎湃。
一個小時的課程結束後,班上的同學開始聚集在我的四周,你一言我一語的問起些簡單的問題。像是你從哪裡來啦,為什麼會轉學啦,生日是什麼時候啊之類的。
我則是專心的看著那些人的臉,試圖想要從中分辨出「那個人」的聲音,完全沒有好好回答那些問題。
「沒事的!」
那個聲音一直在心裡迴盪,無法不去在意。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想的太過入神,字詞跟聲音的關聯竟然越來越模糊,都快要搞不清楚了。
就像是一句施了魔法的咒語。
真的──
從來沒有一個人這樣對我說過。
現在回想起來,每當遇到新的環境,我所追求且期望的,就是這句話吧!
一直以來自己雖渾然不知,但對於九歲的我來說,這句話是完美的。
我的不安與恐懼,終於有人瞭解並且願意跟我一起分擔了。
他是我的同伴。
他對我施了魔法。
輕輕的一句話,我挺直了背,抬起了頭,甚至讓我覺得,這次的轉學不再可怕了。
我睜大眼睛持續地在人群中搜尋著他。
有一個看起來很可靠,應該是班上領導人物的女孩,發覺我支支吾吾的,很溫暖的以為我是太緊張,還開口要大家不要一直圍著我,不要嚇到我才好。
無法好好回答別人的問題是我一直以來的缺點,但這次卻有人站出來幫我說話,對於這樣的改變我感到相當驚訝。
當我正感到不解,一個答案浮上了腦海。
原來,只是抬起頭,這一切就會完全不一樣啊。
開學日能夠這樣的順利,這還是第一次。
那聲音的主人,當天我就找到了。
花了很多堂的下課時間,眼睛轉啊轉的留意每一個人,忽的我發現他就在那裡。
對!不會錯的。
趁著熱心的女孩帶我參觀校園的時候,我忍不住一直偷看著他,他跟幾男孩若無其事地站著聊天,而其他男孩則是跟一般小孩一樣熱衷於討論轉學生的話題,並一邊向我看來。
通常班上同學對於轉學生的態度,不是積極表示好感,就是展現毫無興趣的態度。
但是他跟他們都不一樣。
不會特別在意,卻也不是完全不理會你,是一種中立的態度,讓人覺得很安心。
那時候的他──
在我看來,就像是其他種類的生物一樣,是個特別的存在。
看似自然地融入現場的氣氛,與人之間又確實地拉著一條界線。
那中間隔著的不是厚重的玻璃帷幕,而是一層不為人發現的膜,
薄如糖衣的膜,膜中包覆著另一個次元的世界。
我很在意那個人的一舉一動,應該說,我只對他一個人有興趣。
如果可以,我要站在他的面前,仔細觀察他的臉。
好想知道他的名子。
不過,身為轉學生的我是無法輕易做到這件事的。
就連私底下偷偷地詢問別人也不可以。因為我不能只對一個人特別有興趣,我必須要盡可能地跟全班的同學打好關係,這就是大家對轉學生的期望。
那天放學,我和同路的女同學們一起回家了。
從來沒想過能如此平穩且和睦的結束第一天的學校生活,我洋溢的笑意中帶有一絲羞怯。
很慶幸有一群不太討厭我的女生願意接納我,但我腦中卻一直想著那個男孩的事,要怎樣才能知道他的名子呢?
沿著學校的圍牆走去,內緣種著櫻花樹,從混著一抹青綠的枝枒上,
粉紅的櫻花花瓣隨風飄下。
雖然幾乎都是在春天轉學,但是我不曾像現在這樣留意過校園旁的花花草草。
秒速五公分,我在心中低語。
父親其實還像是個少年一樣,若是在書店找到小時候看的青少年科學雜誌,就會滿心歡喜得帶回家。
在雜誌的某一角落,雜學專欄的那部分令我印象深刻,上面是這樣寫的,「櫻花落下的速率是每秒五公分,也就是說時鐘裡最為忙碌的那根指針動一下,花瓣就會更接近地面五公分。」
我又會以怎樣的速度接近他呢?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秒速5公分one more side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90 |
二手中文書 |
$ 237 |
日本文學 |
$ 237 |
Books |
$ 237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264 |
中文書 |
$ 264 |
日本文學 |
$ 270 |
日本現代文學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秒速5公分one more side
「究竟要以什麼樣的速度活下去,才能再度見到你?」
重新詮釋新海誠經典名作《秒速5公分》,
以女主角視點撰寫的小說登場!
徹底補完動畫中未曾提及的細節,粉絲瘋狂爭相推薦!
【故事簡介】
遠野貴樹與篠原明里在小學畢業後即分隔兩地,雖然兩人對彼此都抱有著特別的思念,但時間仍無情地一天天流逝。在某個下著大雪的日子,貴樹終於決定要去見明里……
本作品一共分成描述貴樹與明里的幼小愛苗與他們重逢之日的「櫻花抄」、以對進入高中就讀的貴樹懷有好感的澄田花苗觀點來詮釋的「太空人」,以及描述兩人內心之徬徨,與本作片名同名的「秒速5公分」等三話。
以「現在、這裡」的日本為舞台,搭配抒情式畫面詮釋的連作短篇動畫作品再次小說化!
作者簡介:
新海誠
日本動畫作家和電影導演。居住在東京都。日本長野縣野澤北高等學校、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國文學專攻畢業。2002年他公開自己一手包辦獨立製作的動畫短片《星之聲》,一舉獲得第1回新世紀東京國際動畫博覽會21公募部門優秀獎,獲得廣大的注目。2004年新海誠首次的電影長篇作品《雲之彼端,約定的地方》於日本公開上映,這部作品在第59回每日電影競賽動畫電影獎以壓過宮崎駿導演的《霍爾的移動城堡》等得獎。2007年的連續短篇動畫《秒速5公分》、2011年《追逐繁星的孩子》、2016年《你的名字》票房皆創下新高,為日本最受矚目的動畫導演。
加納新太
愛知縣人,日本輕小說作家,愛知縣縣立大學文學系畢業,曾任自由編輯,二○○二年正式出道成為作家,代表作有《小鎮回憶》、《光明之心》系列。陸續將新海誠監督作品《雲之彼端,約定的地方》、《你的名字》改編小說化。本書《秒速5公分one more side》首次以不同視角詮釋,將原作故事描述得更為細膩動人,獲得讀者一致好評。
章節試閱
17
昨晚,我夢到了從前。
一定是因為昨天無意間翻到的那封信。
那時候如果能夠交給他就好了。
當時的心情,促使現在的我提筆寫下這篇文章。
我將著把少女時的自己,化為文字留下。
但是,我其實沒有完成的自信,若是真的能用文字表達,那時候放棄的自己,沒有把信交給他的自己,又算什麼……
一想到現在寫下的東西,會不會使得那天的那個體驗成為流水帳的一頁,不由得遲疑了起來。
不過,我還是應該把那封信交給他的。在這麼久之後,都過了十三年之後,重新讀了那封沒有交出去的信,面對過去的自己卻掩不住心底的微笑,心情柔軟而溫暖。...
昨晚,我夢到了從前。
一定是因為昨天無意間翻到的那封信。
那時候如果能夠交給他就好了。
當時的心情,促使現在的我提筆寫下這篇文章。
我將著把少女時的自己,化為文字留下。
但是,我其實沒有完成的自信,若是真的能用文字表達,那時候放棄的自己,沒有把信交給他的自己,又算什麼……
一想到現在寫下的東西,會不會使得那天的那個體驗成為流水帳的一頁,不由得遲疑了起來。
不過,我還是應該把那封信交給他的。在這麼久之後,都過了十三年之後,重新讀了那封沒有交出去的信,面對過去的自己卻掩不住心底的微笑,心情柔軟而溫暖。...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