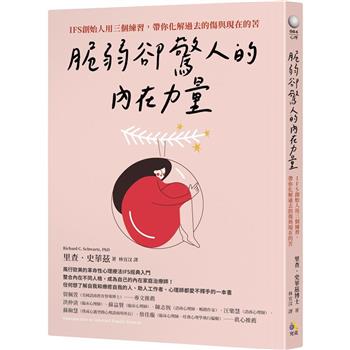圖書名稱:觀看的方式
約翰.伯格最長銷藝術評論經典作品!
探究我們如何觀看藝術和世界的方式,
最精練又最具衝擊性的經典視覺藝術之作。
觀看先於言語。孩童先會觀看和辨識,接著才會說話。
▌藉由觀看,我們確定自己置身於周遭世界當中;我們用言語解釋這個世界,但言語永遠無法還原這個事實:世界包圍著我們。我們看到的世界與我們知道的世界,兩者間的關係從未確定。
▌我們的知識和信仰會影響我們觀看事物的方式。當我們能夠觀看之後,我們很快就察覺到我們也可以被觀看。
▌當影像以藝術作品的方式呈現時,我們觀看它的方式,就會受到我們所學習的一整套藝術看法的影響。
約翰.伯格《觀看的方式》強調「形式」和「論點」兩者同樣重要,試圖引發讀者質疑與探究我們是如何觀看繪畫……這無疑將改變讀者觀看圖像的方式。
全書雖以章次為名,但讀者可以隨自己喜好以任何順序閱讀。其中四章由文字和圖像構成,另外三章則只有圖像。由圖像構成的章節,主題分別為觀看女體的方式,以及油畫傳統中的各種矛盾面向,雖然沒有文字,但它們企圖提出的問題並不下於有文字的篇章。在這些圖像篇章裡,作者有時不提供任何相關資料,因為擔心這類資訊可能會分散讀者的注意力,干擾圖像正在傳述的意旨。
本書初版於一九七二年,以BBC的同名電視影片為基礎加以延伸,是所有談論藝術的書籍中,最發人深省也最具影響力的經典作品,直到今日,其啟發讀者如何觀看藝術作品的入門地位依然不變。
作者簡介
約翰.伯格John Berger
世界知名文化藝術評論家、作家、詩人、劇作家,一九二六年出生於倫敦,二○一七年辭世。
伯格生前長期居住於鄰近法國邊境阿爾卑斯山的小村鎮裡,深受當地傳統習俗及艱困生活形態所吸引,以山中居民為主題撰寫多部相關作品。《約翰‧伯格四季肖像》紀錄片,捕捉巨匠晚年風華。
伯格作品大多批判色彩濃厚,表現形式不斷推陳出新,對社會、政治議題之看法亦獨具一格,公認為歐陸最具影響力藝評家。著作浩繁多元,重要作品有:《第七人》、《觀看的方式》、《觀看的視界》、《影像的閱讀》、《藝術與革命》、《另類的出口》、《另一種影像敘事》、《攝影的異義》、《我們在此相遇》、《留住一切親愛的》、《班托的素描簿》等。
譯者簡介
吳莉君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譯有《攝影的異義》、《我們在此相遇》、《留住一切親愛的》、《霍布斯邦看21世紀:全球化,民主與恐怖主義》等。任職出版社多年,現為自由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