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大國政治的悲劇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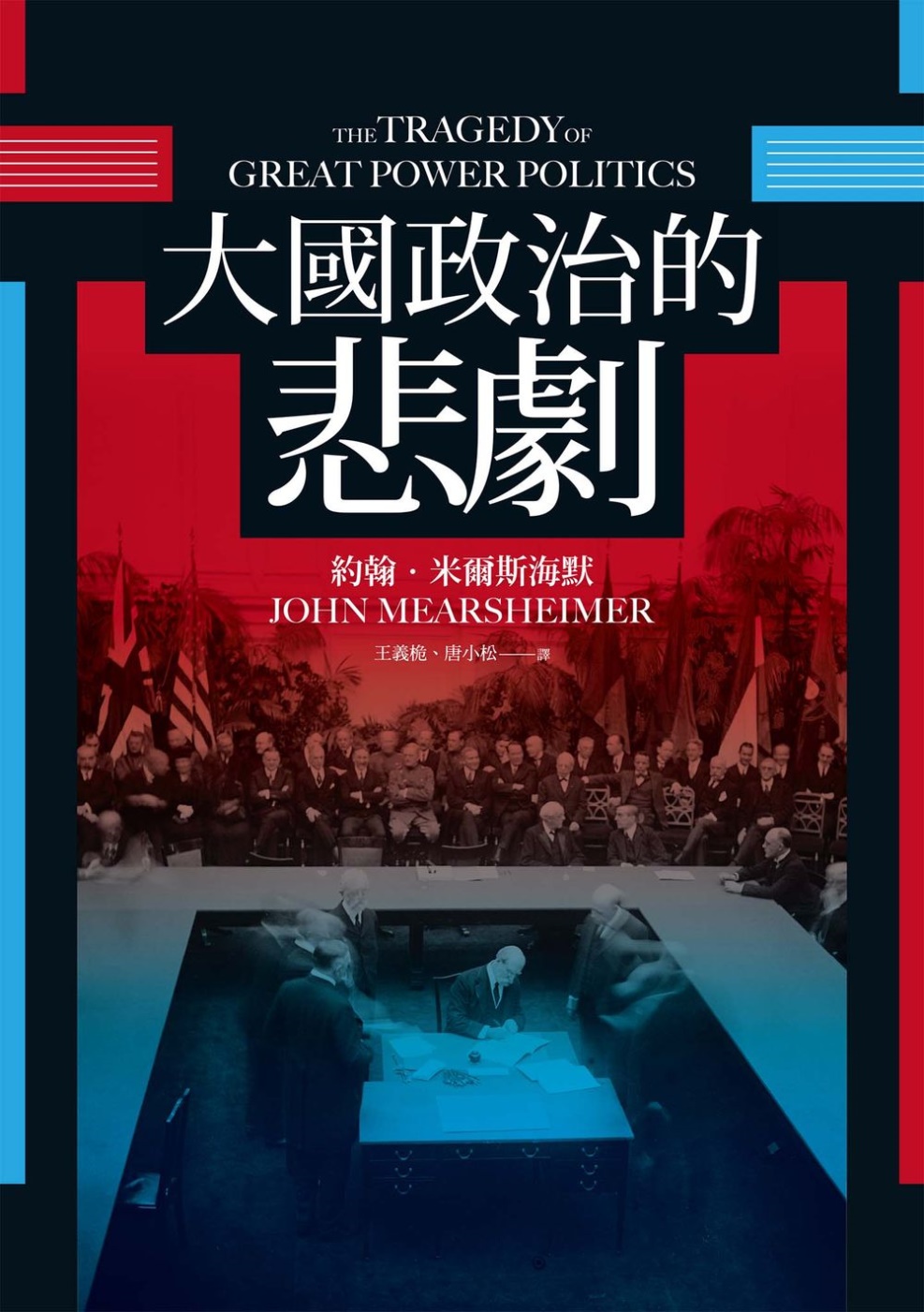 |
大國政治的悲劇 作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 譯者:王義桅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21-09-30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普通級/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46 |
國際關係概論/國際組織 |
電子書 |
$ 385 |
政治 |
二手書 |
$ 395 |
二手中文書 |
$ 435 |
政治概論 |
$ 435 |
政治 |
$ 435 |
Books |
$ 435 |
Books |
$ 435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484 |
中文書 |
$ 495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當代影響各國外交政策與戰略思想家最重要的一本書
理解國際關係,解讀中國能否和平崛起必讀新經典
「權力」是國家唯一的目標,「和平」只因翻臉時機未到
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兩年後蘇聯解體,冷戰戛然而止。隨後國際上瀰漫著一股樂觀氣氛,政治家與學者都相信,透過民主與貿易,戰爭終究會消失。
然而,隨著2001的九一一恐怖攻擊,美國入侵阿富汗、伊拉克而陷入泥淖,人們開始意識到永久的和平不會輕易降臨。俄羅斯染指烏克蘭,中國威逼東海、南海,歐亞大陸兩端一系列的衝突似乎更在昭告世人:權力、恐懼、衝突、戰爭,才是國家與國家間永恆的主題。
事實上,本書作者――芝加哥大學政治系米爾斯海默教授――早在美蘇冷戰剛結束不久,就已經甘冒大不諱地獨排眾議,力陳國際政治的悲劇性本質不變。他承襲早自古希臘以來一脈相傳的現實主義傳統,主張國家無論如何奢談理想,為了生存將不得不追求權力最大化,戰爭、欺詐、推卸責任、以鄰為壑、隔岸觀虎,無所不用其極。戰爭雖然殘酷,但其回報往往豐厚,因此有實力的大國莫不躍躍欲試。
在中國的陰影下,亞洲必將多事,台灣的前途也在未定之天。
《大國政治的悲劇》推出後,即因破除許多一相情願的樂觀幻想而備受重視,成為理解國際關係的新經典。二○一四年米爾斯海默為了回應中國崛起問題特別增補原版結論,集中探討「中國能和平崛起嗎?」米爾斯海默一向能言、敢言,稟著對理性的堅持與紮實的研究,勇於挑戰人們不願面對的真相。他對中美關係與台灣未來的預測,也與他對國際政治的理解一樣,是悲觀的。
作者簡介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
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專研國際關係,文章經常刊載於《紐約時報》、《新共和》、《大西洋月刊》等媒體上,並憑《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的「攻勢現實主義」思想受政治界與學術界極高的重視,奠定其國際關係學界的大師地位。
2007年,他與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渥特(Stephen Walt)合著的《以色列遊說團體與美國外交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也成為紐約時報最佳暢銷書,其中直言不諱的內容引發激烈爭論與猶太團體的抗議。2011年寫的《為什麼你的政府會說謊?揭開7種政治謊言背後的真相》(Why Leaders Lie: The Truth About Lying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曾在台灣出版。
2013年底米爾斯海默應「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之邀來台灣參訪,並發表「在中國崛起陰影下的台灣」專題演講,首次完整的闡述他對中美與兩岸的看法。
譯者簡介
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歐盟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教授、中國駐歐盟使團外交官。著有《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等,編著有《全球視野下的中歐關係》等。
唐小松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交學系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公共外交季刊》學術編輯,著有《遏制的困境——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的對華政策》。
張登及
本書附錄譯者。臺大政治學系教授。學術領域為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外交、共黨理論與歷史、兩岸關係等。
潘崇易
本書附錄譯者。臺大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