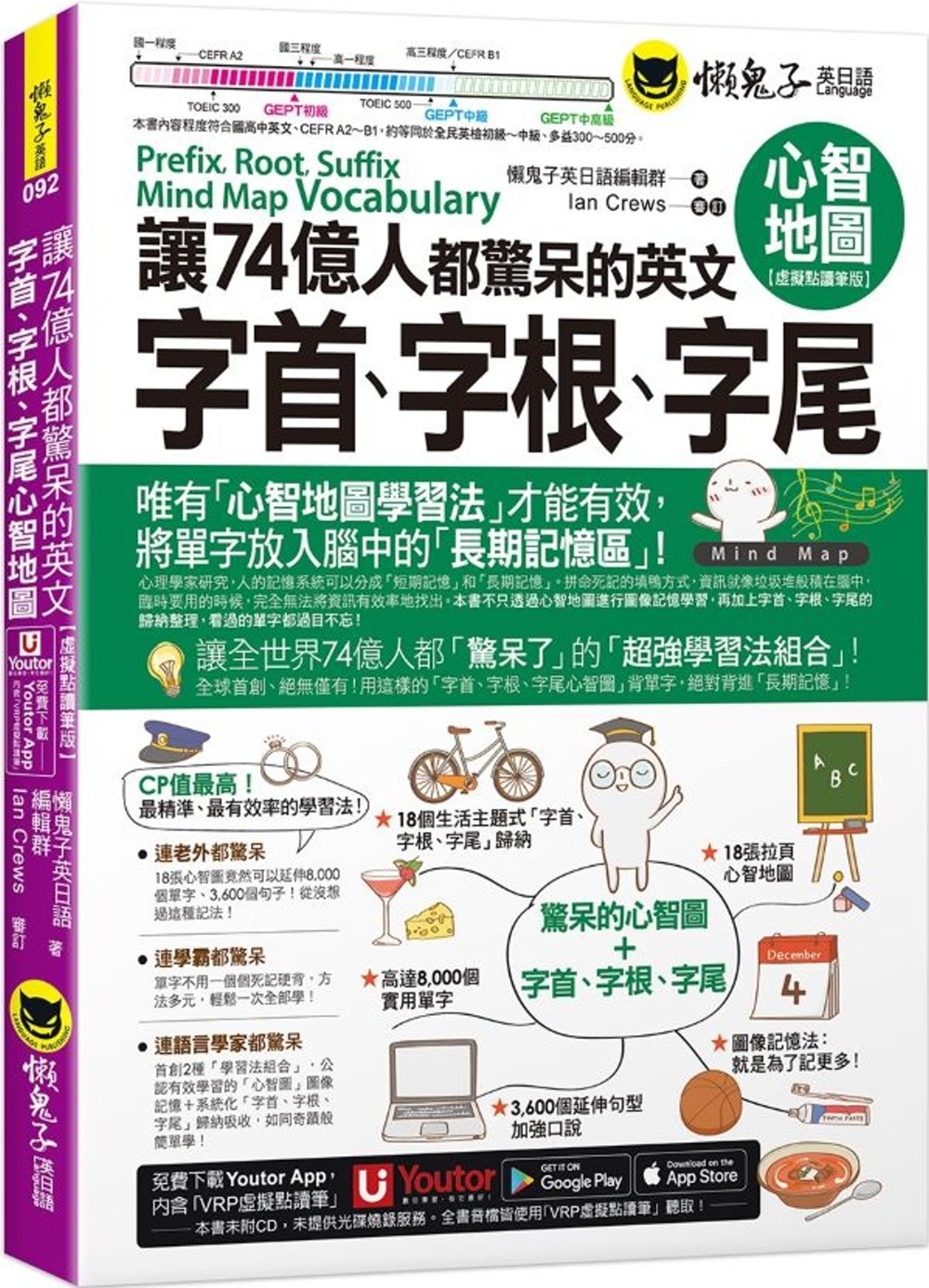夜晚的潛水艇
一九六六年一個寒夜,博爾赫斯(波赫士)站在輪船甲板上,往海中丟了一枚硬幣。硬幣帶著他手指的一點餘溫,跌進黑色的濤聲裡。博爾赫斯後來為它寫了首詩,詩中說,他丟硬幣這一舉動,在這星球的歷史中添加了兩條平行的、連續的系列:他的命運及硬幣的命運。此後他在陸地上每一瞬間的喜怒哀懼,都將對應著硬幣在海底每一瞬間的無知無覺。
一九八五年,博爾赫斯去世前一年,一位澳洲富商在航海旅途中無聊,借了同伴的書來看。對文學從無興趣的他,被一首題為〈致一枚硬幣〉的詩猝然擊中。一九九七年,在十餘年成功的商業生涯後,這位商人成了財產不可估量的巨富和博爾赫斯的頭號崇拜者。他收藏了各種珍貴版本的博爾赫斯作品、博爾赫斯用過的菸斗、墨鏡、吸墨紙,甚至連博爾赫斯的中文譯者王永年在翻譯時用的鋼筆他都收集了兩支(此時王還在世)。但這些仍無法平息他的狂熱。同年春天,一個念頭在黎明時分掉進他夢中,促使他資助了一場史上最荒誕的壯舉。他要找到博爾赫斯扔進海裡的那枚硬幣。他買下一艘當時最先進的潛艇並加以改進,聘請了一批來自世界各地的海洋學家、潛艇專家和海底作業員(該團隊由一名中國籍陳姓物理海洋學家擔任隊長)。富商深知他無法讓這群精英為自己的白日夢效力,因此向他們承諾,將為他們的海底考察提供長久的資助,要求僅是他們在科研工作之餘,順便找尋一下那枚硬幣的蹤跡。陳隊長問他:「如果一直都找不到呢?」「那我就一直資助下去。」
根據詩中資訊,博爾赫斯是從蒙特維多啟航,拐過塞羅時將硬幣丟進海中。團隊調取了那一年的洋流資料,並將塞羅周邊海域劃分成許多個邊長一公里的正方形,逐塊搜索。為了區分海底礦床及海中垃圾,他們特製了一台金屬探測器,僅對微小體積的金屬圓片產生反應。結果只找到幾枚大航海時期沉在海底的金幣。考慮到那枚硬幣已被鹽分啃噬了數十年,很可能僅剩餘一點殘片,或者完全消融了。第二年,富商讓他們離開塞羅,去全世界的海域開展科研考察,同時保持探測器開啟,萬一發現反應,再設法進行打撈。富商明白找到的希望微乎其微,但他認為找尋的過程本身就是在向博爾赫斯致敬,像一種朝聖。其間所耗費的財力之巨大和歲月之漫長,才配得上博爾赫斯的偉大。
阿萊夫號潛艇(名字自然取自博爾赫斯一篇小說的題目)的技術領先於同時代任何國家,為避免受到干預,這次考察行動從未向外界公布。潛艇定期在指定座標浮出海面,同富商的私家飛機交接。飛機運來物資,同時將潛艇外部安裝的攝像頭所錄下的影像資料帶回去。富商每夜看著海底的畫面入睡。考察進行了將近三年。一九九九年底,潛艇失去聯繫。推測是在探索海溝時失事。次年,富商病逝。他的孫女在多年後翻看他的遺物時發現了那些錄影帶。其中有一段不可思議的影像:
潛艇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駛入一座由珊瑚構建的迷宮。探照燈照出絢爛迷幻的圖景。隊員們誤估了兩座珊瑚礁之間的距離,導致潛艇被卡住,動彈不得。六小時後,鏡頭拍到遠方駛來一艘藍色潛艇,向阿萊夫號發射了兩枚魚雷。魚雷精準地擊碎了珊瑚礁,艇身得以鬆動,快因缺氧而昏迷的隊員連忙操縱潛艇,向海面升去。那艘潛艇則像幽靈般消失在深海,此後的航行中再未和它相遇過。
我國知名印象派畫家、象徵主義詩人陳透納去世後公開的手稿中,有一篇他追憶早年生活的散文(也有人將其歸類為小說),也許能為這一神祕事件提供另一種解釋:
國慶時回了趟老家。老房間的舊床實在是太好睡了。隨便一個睡姿裡,都重疊著以往時光裡無數個我的同一姿態。從小到大,一層套一層,像俄羅斯套娃一樣。我覺得格外充實,安適,床是柔軟的湖面,我靜悄悄沉下去,在這秋日的午後。醒來時我打量這房間。窗簾上繪著許多棕色落葉,各種飄墜的姿態,和秋天很相宜。淡黃色杉木地板,淡黃色書桌。藍色曲頸檯燈。圓圓的掛鐘,螢光綠的指針,很久以前就不轉了,毫無緣由地一直掛在那裡。牆刷過一次,仍隱約可辨我年幼時的塗鴉,像遠古的壁畫。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依然愛這個房間,儘管它不再是潛水艇的駕駛室。我該起床了。父母喊我吃晚飯的聲音,好像從遙遠的歲月裡傳來。穿衣服時,我依然無法相信自己已經三十歲了。
晚飯時母親說起,上禮拜沈醫生過世了,以前給你看過病的,你還記得吧。在妻子面前,父母絕口不提我生病那幾年的事,這次她娘家有事,沒跟我一起回來。我含著筷子嗯了一聲。中學那幾年,我像著了魔一樣沉浸在病態的妄想裡,自己倒不覺得什麼,對我父母來說,那是噩夢般的幾年。不過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也結婚生子,進了一家廣告公司,像個正常人一樣生活。大家都覺得很欣慰。
從初中起,我為過度生長的幻想所纏繞,沒法專心學習。沒法專心做任何事。更小一些,誰也沒覺察到症狀,還誇我想像力豐富。我指著房門上的木紋,說這是古代將軍的頭盔,那是熊貓的側面,爸媽都覺得像。有時我坐在地上,對著大理石的紋理發呆,想像這條細線是河流,那片斑紋是山脈,我在其中攀山涉水,花了一下午才走到另一塊大理石板上。有一天我爸回家,發現我一臉嚴肅地盯著正在抽水的馬桶,問我幹嘛,我說尼斯湖上出現了一個大漩渦,我們的獨木舟快被吸進去了。我爸問我們是誰,我說是我和丁丁,還有他的狗。他也只是摸摸我的頭說,要不要我來救你,不然來不及吃晚飯了。
這類幻想多半是一次性的,像一小團雲霧,隨處冒出,氤氳一陣又消散。只要有插圖的書,我都能拿來發呆。對著一根圓珠筆芯我能看上一節課。所以成績可想而知。四年級起,我迷上看山水畫。我看到美術課本上印著的《秋山晚翠圖》,一下就著了迷。我從畫底的雲煙裡攀上山腳的怪樹,一直沿著山澗,爬到畫上方的小木橋上,在畫中花了三天,在現實中則用了兩節課。我在草稿紙上畫出《溪山行旅圖》裡山峰的背面,設計出一條攀登路線,登頂後我躲在草木後邊,窺探著山下經過的客商。我在一本圖冊上的《茂林遠岫圖》裡遊蕩了一禮拜,想像自己如何從溪流邊走到崖底,如何躲避山中猛獸,最後到達安全的山洞。老師經常向我爸媽告狀,說我注意力不集中,上課老走神。
當鋼琴教師的母親決定教我學琴,來培養專注力。我開始苦不堪言地練指法,黑鍵白鍵在我眼中一會變成熊貓,一會變成企鵝。最後我覺得自己在給斑馬撓癢癢。為激起我的興趣,我媽給我彈了幾首莫札特,說等你練好就能彈這麼好聽的曲子了。我呆呆地聽了半天,在一首曲子裡,我乘著熱氣球忽上忽下地飛,最後飛進銀河裡去了。另一首說的是一個小男孩在湖面上用凌波微步跑來跑去。最後一首描繪夜裡亮著燈的遊樂場。我媽見我聽得入神,問我感覺怎樣。聽我說完,她歎了口氣,合上琴蓋,說:「你去玩吧。」原先我只能對畫面胡思亂想,從此對聲音也可以了。
初中後我對歷史地理蠻有興趣,但只是隨便聽一點,不甚了了。用這點零星知識作養料,幻想越發繁茂地滋長起來。我的腦袋像伸出了萬千條藤蔓,遇到什麼就纏上去,纏得密密實實的,還要在上面旋轉著開出一朵花。我隨時隨地開小差,對著什麼都能走神,時不時就說些胡言亂語,同學們都覺得我是怪人。成績自然一塌糊塗。爸媽先是帶我找了學校的心理輔導老師,後來又看了幾次心理醫生和腦科專家,有說我妄想症的,有說沒毛病只是想像力太豐富的,總之都沒轍,說等過幾年孩子大了沒準就好了。爸媽常常歎氣,我倒覺得沒什麼。我能在蓮蓬裡睡覺,到雲端游泳,在黑板上行走,追蹤墨水瓶裡的藍鯨,我能一邊挨老師的罵一邊在太空裡漂浮,誰也管不著我,誰也捉不住我。無數個世界任憑我隨意出入,而這世界只是其中的一個罷了。
此外,我覺察到一些不同尋常的現象。當我想像自己在某幅山水畫中攀爬,如果想得很投入,幻想結束後我會覺得渾身酸痛。有一晚睡前,我看了好久莫內的睡蓮,夢中我變得很小很小,在那些花瓣間遨遊,清晨醒來後,枕邊還有淡淡幽香。早飯時母親問我是不是偷噴了她的香水。由此我推測,只要將幻想營造得足夠結實,足夠細緻,就有可能和現實世界交融,在某處接通。如果我在幻想中被山林裡跳出來的老虎吃掉,也許現實中的我也會消失。當然我沒有嘗試過。我只樂於做一個夢境的體驗者,並不想研究它的機理。而且我相信,當幻想足夠逼真,也就成了另一種真實。
初二那年,我發明出了新遊戲:對著陽光裡的浮塵幻想。這時我已經有了點粗淺的歷史知識。我想像一粒塵埃是一顆星球,我把這顆星球的歷史從頭到尾想像出來,從學會用火開始,一直想到造出飛船去探索別的塵埃。其間當然參照了地球上的歷史。隨後我發現用一整天來設想幾千年的事,結構太鬆散,破綻太多,因此幻想容易流逝。只要我樂意,我可以用一天來想那星球上的一天,但工程太大,也不好玩了。最後我決定用一天來編造一百年的歷史,我設定好物種、資源、國家、陸地形狀等等,想了幾天,一切就自行發展起來。想像這回事,就像順水推舟,難的只是把舟從岸上拖進水裡,然後只消一推,想像就會自行發展。白日夢的情節,常常會延伸進我的睡夢裡。有時我甚至覺得我們星球上所發生的一切,其實只是另一個人對著塵埃的幻想罷了。但我發覺這遊戲有個缺點,就是無論我如何設置開頭,塵埃上一定會發生世界大戰。試了好多次,都無法避免。我被戰陣廝殺聲、火光和蘑菇雲弄得連夜失眠,只好終止了幻想,像用手掐滅一個菸頭。
接下來,我發明出了最讓我著迷,也是最危險的一個遊戲:我造了一艘潛水艇。
我爺爺是個海洋學家。我七歲那年,他不顧家人反對,以六十歲高齡,受邀參加了一次海洋考察,具體去哪裡做什麼,沒對我們說。然後再也沒有回來。我很小的時候,每晚睡前,都聽他講海裡的故事。我父親小時候也聽過那些故事,他至今認為那是造成我妄想症的根源。我時常思念我爺爺,在我的想像中,他和大海融為一體。十四歲那年,初三上學期,我決定開始經營一次海底的幻想。我在課堂筆記的背面畫了詳細的草圖,設計出了一艘潛水艇。材料設定為最堅固的合金,具體是什麼不必深究。發動機是一台永動機。整艘潛艇形狀像一枚橄欖,艇身為藍色,前方和兩側還有舷窗,用超強玻璃製成,帶有夜視功能,透過玻璃看出去,海底是深藍的,並非漆黑。潛艇內部結構和我家二樓一模一樣:父母的房間,我的房間,擺著鋼琴的小客廳和一個衛生間。我的設想是這樣的,白天時,這層樓就是這層樓,坐落于群山環抱的小縣城裡;夜晚,只要我按下書桌上的按鈕,整層樓的內部空間就轉移到一艘潛水艇裡邊去,在海中行駛。我爸媽在隔壁睡著,一無所知,窗外暗摸摸的,他們也不知是夜色還是海水。我的房間就是駕駛室。我是船長,隊員還有一隻妙蛙種子和一隻皮卡丘。
每天夜裡,我坐到書桌前,用手指敲敲桌面,系統啟動,桌面就變成控制台,上面有各種儀錶。前方的窗玻璃顯示出深藍色的海底景象。副駕駛位上的皮卡丘說:皮卡皮卡!它的意思是,Captain Chan,我們出發吧!妙蛙種子說:種子種子。這是說,一切準備就緒。我看了看桌上的地球儀,上面亮起一個紅點,那是我們所在的位置。現在已經位於太平洋中央了。掛鐘其實是雷達螢幕,顯示附近沒有敵情。我們制定的航線是從縣城的河流到達閩江,再從閩江入海,繞過台灣島,做一次環球旅行。在河流和江水裡,潛水艇可以縮小成橄欖球那麼大,不會惹人注意。到海底再變回正常大小。航行的時間,我設定為一九九七年。因為那時我爺爺還在進行海上考察,沒準能遇上他。我握住檯燈的脖子(這是個操縱柄),往前一推,果決地說:出發!潛艇就在夜色般的海水中平穩地行駛起來。
這一路我們經歷了很多冒險。我們被巨型章魚追擊過,一整夜都在高速行駛。後來潛艇急降到海底,啟動隱形模式,偽裝成一塊岩石,章魚就在頭頂上逡巡,蜿蜒著滿是吸盤的長長觸手,納悶地張望。我們在下面屏住呼吸,體會著甜蜜的刺激。我們在珊瑚的叢林裡穿行了三個晚上,那裡像一座華美的神殿。遇到一艘潛艇卡在那裡,不知是哪國的,我們出手救了它。有可能我們穿透進了現實的海底,也可能那艘潛艇是另一個人的幻想,我們沒有深究。還有一回海溝探險,黑暗中無聲遊出一頭史前的滄龍,險些被牠咬住。利齒刮擦過艇身的聲音,至今想起還覺得頭皮發麻。隔著舷窗細看牠遍體的鱗甲,滑亮如精鐵所鑄,倒是好看。我們還和一隻性情溫和的虎鯨結成了好友,每次在危難中發出信號,它總像守護神一樣及時趕到,同我們並肩作戰。
自從開啟了這場幻想,我白天的胡思亂想少了許多,因為要把想像力集中在夜間使用。但是依然不怎麼聽課,我不斷完善著潛水艇的設計圖紙,制定新的冒險計畫。晚自習回來後,我在書房裡開始構思這一夜的大致輪廓,然後敲敲桌面,坐著陷入幻想。幻想中的情節按著構思來,但也會有我無法控制的演變,這樣才有意思。入睡後,之前的劇情在夢裡延續。珊瑚的光澤和水草的暗影夜夜在窗外搖盪。
有一天晚上,我爸和朋友小酌,很晚還沒回來。我很焦急。因為如果我把二樓的空間轉移到深海的潛艇中去,原先的位置會變成怎樣,我沒有想過。也許等我爸上了樓,打開門,會看到一片空白,或滿屋的海水。我只好等著。入冬後,坐書桌前太冷,我把操控台轉移到床上來。枕頭上的圖案是各種按鈕。床頭板是顯示幕,開啟透視功能和照明後,就能看見被一束光穿透的深藍海水、掠過的游魚和海底沙石。我蓋著被子趴在床上,雙手放在枕邊,蓄勢待發。十點半,老爸終於到家了。聽著他鎖門,上樓,輕輕合上臥室門的聲音,幸福感在被窩裡油然而生。彷彿鳥棲樹,魚潛淵,一切穩妥又安寧,夜晚這才真正地降臨。門都關好了,家閉合起來,像個堅實的果殼。窗外靜極了,偶爾聽見遠處一陣急促的狗吠聲,像幽暗海面上閃動的微光。我真想待在這樣的夜裡永遠不出來。按下啟動鍵,我進入潛艇裡。妙蛙種子問:種子種子?(今晚這麼晚?)我說,久等了,出發吧!那晚我們在北冰洋的冰層下潛行。我忘了設計取暖裝置,結果第二天醒來,感冒了。
高二的一天夜裡,我下了晚自修,興奮地小跑回家,今晚要去馬里亞納海溝探險了。為這一天我們做了好久的準備工作,皮卡丘早就急不可耐了。進門,發現爸媽都坐在客廳裡,沉默地等著我。茶几上放著我的筆記本,攤開著,每一頁都畫著潛水艇。我臉上發熱,盯著本子,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父親開了口,他說,透納,你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我看著他們在燈光下的愁容,第一次發現父母老了很多。這幾年我整天沉浸在海底,根本沒仔細打量過他們。那晚他們對我談了很多,傾訴了他們這些年的憂慮。母親哭了。我從未在父親臉上見過那種無助的神情。那是一次沉重的談話,又在快樂的頂峰迎頭罩來,以至多年後想起,語句都已模糊,心頭仍覺得一陣灰暗。高考、就業、結婚、買房,這些概念從來都漂浮在我的宇宙之外,從這時起,才一個接一個地墜落在我跟前,像灼熱的隕石。我才意識到這是正常人該操心的事。正常一點,他們對我的要求也僅限於此。其實我除了愛走神、成績差,沒什麼反常的舉動,但父母能看出我身上的游離感,知道我並非只在這個世界生活。而我渾渾噩噩,竟從未覺察到自己的病態和他們的痛苦。想到那麼多時間都被我拋擲在虛無的海底,我第一次嘗到什麼是焦慮。
當晚入睡後,我沒有進入潛水艇,只做了許多怪誕的夢。夢中景物都是扭曲的,像現代派的怪畫。
第二天,我試圖專心聽講,發現已無法做到。走神。不可抑制地走神。看著教室牆壁上的裂紋走神,想像那是海溝的平面圖。對著一束陽光走神,無數星球在其中相互追逐。盯著橡皮走神,它的味道和潛水服的腳蹼相似—我在淺海中採摘珍珠時穿過。我翻開書來看,結果又對著課本前頁十來個編者姓名發了半小時的呆,從名字揣測這些人的性格、相貌和生平。我腦中伸出萬千藤蔓,每一條藤蔓又伸出無數分叉,漫天枝葉在教室中無聲地蔓延,直到把所有人都淹沒。
這樣過了三天。這三天我都沒有下到潛艇中去。我當然可以想像出一個世界,那裡邊的爸媽並不為我擔憂,我依然能每夜開著潛艇,而他們毫無察覺地睡在隔壁,陪我在海底漫遊。但那晚他們憔悴的面容和疲憊的聲音已經刻進我腦中,我做不到那樣自欺欺人。同高考相比,去馬里亞納海溝探險實在是太無關緊要的事了。我不忍心再讓他們難過。我要爭氣。
第三天晚上,我想好了對策,關了房門,坐到書桌前。閉上眼。我讓所有的想像力都集中到腦部。它們是一些淡藍色的光點,散布在周身,像螢火蟲的尾焰,這時都往我頭頂湧去。過了好久,它們彙聚成一大團淡藍色的光芒,從我頭上飄升起來,漸漸脫離了我,像一團鬼火,在房間裡遊蕩。這就是我的對策:我想像我的想像力脫離了我,於是它真的就脫離了我。那團藍光向窗外飄去。我坐在書桌前,有說不出的輕鬆和虛弱,看著它漸漸飛遠。最後它像彗星一樣,沖天而去。
次日醒來,我拿起一本書來看,看了一會,驚覺自己真的看進去了。課堂上聽講也沒有問題,居然整整一節課都沒開小差,老師說什麼,我聽什麼,完全跟得上,再也不會抓住一個詞就開始浮想聯翩。聽課時,對身邊一切都能視而不見,這種適度的麻木真是令人舒適。我好像從熱帶雨林裡一下子跑到了馬路上。這裡不再有繁密的枝葉、柔軟的泥沼、斑斕的鸚鵡和吐著信子的蛇,眼前只有確鑿的地面和匆匆的人流。於是我一路小跑,追了上去。
高三一年我突飛猛進,老師們都說我開了竅,同學們背地裡說我腦子治好了。後來的事不值一提。我考上了不錯的大學,進了一家廣告公司,結了婚。我的腦中再也不會伸出藤蔓,成了一個普通的腦袋了。想像力也一般,和常人相差無幾。旅遊時,坐在竹筏上,導遊說這座山是虎頭山,我說,嗯,有點像。他說那是美人嶺,我說看不出來,他說,你得橫著看,我歪著頭看了一下,說,有點那個意思。就這樣而已。工作中,有時甲方和領導還說我的方案缺乏想像力,那時我真想開著我的潛水艇撞死他們。
有時我也試著重溫往日的夢境。但沒有用,我最多只能想像出一片深藍的海,我的潛艇浮在正中央。靠著剩餘這點稀薄的想像力,我根本進不去裡面,只能遠遠地望著。只有一次,那晚我喝了點酒,睡得格外安適。夢中我又坐在駕駛台前,皮卡丘推著我說,皮卡皮卡?(你怎麼了,發什麼愣?)妙蛙種子說:種子種子!(我們向海溝出發吧!)我看了看時間,原來我們還停留在一九九九年的海底。我離去後,潛水艇中的一切像被按下了暫停鍵。它們不知道我多年前已經捨棄了這裡。隨後我就醒了,帶著深深的悵惘。我意識到,當年的對策有個致命的疏漏。當時我急於擺脫想像力的困擾,沒有設定好如何讓它回來。現在我有更好的方案:我可以想像出一個保險櫃,把想像力想像成一些金塊,將它們鎖在櫃中。再把密碼設置成一個我當時不可能知道,若干年後才會知道的數字。比如我結婚的日期,二○二二年我的電話號碼。這樣我就能偶爾回味一下舊夢,來一場探險,怕沉溺其中,再把想像力鎖回去就行了,設置一個新密碼。但是當時欠考慮,畢竟年紀小。現在已經來不及了。我的想像力可能早就飛出了銀河系,再也回不來了。
國慶最後一天,離家前夜,我坐在書桌前,敲了敲桌面。什麼都沒有發生。我握住檯燈,望著窗外的夜色,對自己說:Captain Chan,準備出發吧。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夜晚的潛水艇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夜晚的潛水艇
★ 豆瓣讀書2020年度中國文學(小說類)Top1
★ 第六屆中國單向街書店文學獎年度作品
★ 首屆PAGEONE文學賞 首賞
從微物與唯物中尋求出路。一張照片,一枚錢幣,一把鑰匙,一個音符,一隻筆,一罈酒,都可能是電光石火的契機,突破此刻此身的限制,朝向另一星空或深海開放……
華語文壇卓爾出群的新銳小說家!陳春成首部作品,驚豔出場~
王德威/專文推薦 余華/特別推薦
◎特別推薦——
陳春成的文字清晰典雅,在年輕世代作家中並不多見。他的故事天馬行空,字裡行間在在顯示鍛鍊的痕跡。世界文學和傳統典故巧妙糅合,「舊山河和新宇宙」奇特接軌。而他工整的筆觸其實處理著一個又一個危機:從集權暴政到精神耗弱,從歷史崩毀到記憶錯亂,淒迷的夜,詭異的夢,救贖懸而未決……《夜晚的潛水艇》含蓄蘊藉,而又每每閃爍幽光。在一個文字漫漶、人人競相表態卻又言不及義的時代,這樣的書寫何其難得。知其白,守其黑,在洞穴裡,在古甕中,在匿園裡, 在深海下,「我附體在某個角色身上,隨他在情節中流轉,他的一生就是我的一世。」九篇小說,無數輪迴。藏身其間,陳春成幻化為小說中的人物,幽幽的將他的文學潛水艇駛向下一個時空。——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
我很喜歡《夜晚的潛水艇》,陳春成給了我一個驚喜。在NBA,他們對那些充滿潛力的年輕球員有一個形容,天空才是他的極限,這話也可以用在陳春成的身上。他的寫作既飄逸又扎實,想像力豐富,現實部分的描寫又很扎實,敘述中的轉換和銜接做得非常好。我覺得他是一個前程無量的作家。 ——余華(知名作家)
◎關於本書——
虛構是我最接近自由與狂歡的樣式。
寫作於我即是快馬、長槍、大碗的酒和阻絕兵馬的群山,是內在的狂歡,平息後即歸於日常。——陳春成
1966年波赫士在烏拉圭外南大西洋投下一枚錢幣,啟動了1998年一個中國少年的夢中潛航;公元4876年秋天的一場《紅樓夢》餘孽大搜捕,隱隱回應著明萬曆十四年春夜,神宗皇帝憂鬱的啟悟;文化大革命熱火朝天的時分,福建山裡一個和尚琢磨著如何藏匿一塊明代流下來的石碑;1957年深夜的列寧格勒傳來薩克斯風聲音,是誰有這樣膽子吹奏著違禁樂器……
陳春成的小說風格,開啟了一個世代的新視野。
彷彿鳥棲樹,魚潛淵,一切穩妥又安寧,夜晚這才真正地降臨。
《夜晚的潛水艇》是陳春成的首部短篇小說集。九個故事,筆鋒游走於舊山河與未知宇宙間,以瑰奇飄揚的想像、溫厚清幽的筆法,在現實與幻境間闢開多條祕密的通道:海底漫遊的少年、深山遺落的古碑、彌散入萬物的字句、雲彩修剪站、鑄劍與釀酒、鐵幕下的薩克斯、藍鯨內的演奏廳……
潛入故事深處,感知體內的星雲旋動、草木蔓發;以詞語的微光,探照記憶的海溝。關於藏匿與尋找、追捕與逃遁……
陳春成創作的主角們,身體都潛伏著夜行性動物的習性,他們皆善於躲藏,他們深信值得人沉迷一生的事情太多了,每個洞穴都充滿誘惑。他撰寫的每篇小說幾乎都以古典文學作為基調,再澆灌以現代手法,融會後撰寫出迷人的文學。
陳春成的小說世界,是可供藏身的洞窟,懸浮於紙上的宮殿,航向往昔的潛艇……。他以作品隱喻文學中想像力的重要性,於小說情節摻入推理的元素,每一篇小說各自發展出出色的格局,刻畫令人驚豔。
透過《夜晚的潛水艇》,我們得以理解,當我們在面對現實世界時,方法並非只有一個;我們除了可以如實描摹世界外,應該還有能力再建構另外一個精神世界。
◎單篇精采內容——
〈夜晚的潛水艇〉將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有關硬幣的一首詩,與主角陳透納在年少時的房間內創造一艘幻想潛水艇,彼此連結成故事。透過想像的潛水艇,有無數個世界任憑少年隨意出入。當陳透納長大成為著名藝術家在遺書中回憶起自己的十六歲,他說才華早已離他而去,想像力也被現實磨損消滅,他被迫回到「正常人」生活裡,令人惆悵。
〈竹峰寺〉的小說主角有一天投宿「竹峰寺」的寺廟,竹峰寺有一塊蛺蝶碑,是寺中著名但已佚失的碑銘,然而,因為碑使得出家人衍生非分之心。最終,蛺蝶碑的去處除了老和尚外,還有誰知道呢?
〈傳彩筆〉是一篇思辨文學的短篇,講一個地方傳統文人葉書華在夢中得到一支彩筆,進而寫出令人讚嘆的小說;但得到彩筆的條件是,他可以寫出偉大的作品但只有自己能夠領受,無論生前或死後,都不會有人知道他的偉大;他願意過這樣痛苦而兩難的一生?
因為元首視察時一句無心的話,「雲彩管理局」如驚弓之鳥,立即修訂雲彩修剪條例。〈裁雲記〉中的管理員把剪修雲彩站當作他蟄伏的洞穴,他和他住在山下城內的老師,都喜愛躲在洞穴內鑽研學問。無論世事如何變遷,最終他們還是可以在生活中找到生存下來一種方式。
陳春醪是大白堂的釀酒師,他的釀酒聲名遠播到宮廷內。他釀酒的哲學是,酒是水釀出來的詩,詩有起承轉合,酒亦同此理。他釀的酒有昆侖絳、老春、真一、大槐,還有一種沒名字的酒。酒還分有青紅白黑黃五色,暗合五行。〈釀酒師〉的最終,陳春醪會教導童子如何釀酒呢?
〈《紅樓夢》彌撒〉是一篇引人入勝的科幻小說,書寫《紅樓夢》在三十二世紀的4876年之一國家中失傳了。被關押的無名囚犯據傳是唯一記得該書內容的人,官方的認知《紅樓夢》與《聖經》具同等地位,它的中心思想也許能發揮出戰無不勝的治國奇效。而《紅樓夢》的彌撒是否盛宴必散?被未來國家刑求的無名囚犯,可能回憶起內容嗎?
因為生於父母離婚的破碎之家,李茵唯一完整的記憶是全家出遊照片中的一面湖水。〈李茵的湖〉講述主角為了女友李茵的湖,找遍了城市打聽湖的下落。這個謎團終能解開嗎?李茵果真能辨別記憶的真偽?
〈尺波〉篇幅雖短卻很精悍,宛如一部魔幻色彩濃重的精采電影,講述一把劍與鬼的故事。這把劍長約二尺,黑中泛藍,紋理自動,流轉不停,像一道被約束的波瀾深淵。鑄劍師給它起名叫尺波。鑄劍師為了鑄造這把國王夢中的劍,他是如何辦到的?
中篇小說〈音樂家〉,描述1957年蘇聯列寧格勒一個老音樂家的故事。警察庫茲明為了追查吹奏違禁樂器薩克斯風的人,從自列寧格勒樂曲審查辦公室退休的古廖夫與大學生瓦爾金二人檔案下手。庫茲明耐心的抽絲剝繭,這場鬥智的推理,將會引爆神經質的音樂家古廖夫其神祕命運中如何巨大的風暴?
作者簡介:
陳春成
男,1990年出生,福建省寧德市屏南縣人,現居福建泉州。
作品曾獲《亞洲週刊》2020年十大小説,豆瓣2020年度中國文學(小説類)Top1,第六屆單向街文學獎年度作品獎,第一屆PAGEONE文學賞首賞。
首部小說集《夜晚的潛水艇》。
章節試閱
夜晚的潛水艇
一九六六年一個寒夜,博爾赫斯(波赫士)站在輪船甲板上,往海中丟了一枚硬幣。硬幣帶著他手指的一點餘溫,跌進黑色的濤聲裡。博爾赫斯後來為它寫了首詩,詩中說,他丟硬幣這一舉動,在這星球的歷史中添加了兩條平行的、連續的系列:他的命運及硬幣的命運。此後他在陸地上每一瞬間的喜怒哀懼,都將對應著硬幣在海底每一瞬間的無知無覺。
一九八五年,博爾赫斯去世前一年,一位澳洲富商在航海旅途中無聊,借了同伴的書來看。對文學從無興趣的他,被一首題為〈致一枚硬幣〉的詩猝然擊中。一九九七年,在十餘年成功的商業生涯...
一九六六年一個寒夜,博爾赫斯(波赫士)站在輪船甲板上,往海中丟了一枚硬幣。硬幣帶著他手指的一點餘溫,跌進黑色的濤聲裡。博爾赫斯後來為它寫了首詩,詩中說,他丟硬幣這一舉動,在這星球的歷史中添加了兩條平行的、連續的系列:他的命運及硬幣的命運。此後他在陸地上每一瞬間的喜怒哀懼,都將對應著硬幣在海底每一瞬間的無知無覺。
一九八五年,博爾赫斯去世前一年,一位澳洲富商在航海旅途中無聊,借了同伴的書來看。對文學從無興趣的他,被一首題為〈致一枚硬幣〉的詩猝然擊中。一九九七年,在十餘年成功的商業生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隱秀與潛藏——陳春成《夜晚的潛水艇》/王德威
夜晚的潛水艇
竹峰寺
傳彩筆
裁雲記
釀酒師
《紅樓夢》彌撒
李茵的湖
尺波
音樂家
夜晚的潛水艇
竹峰寺
傳彩筆
裁雲記
釀酒師
《紅樓夢》彌撒
李茵的湖
尺波
音樂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