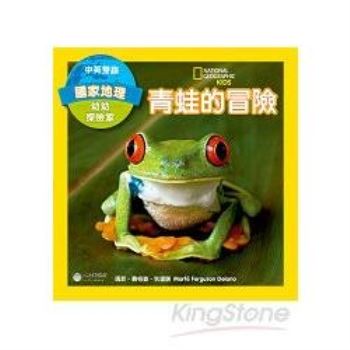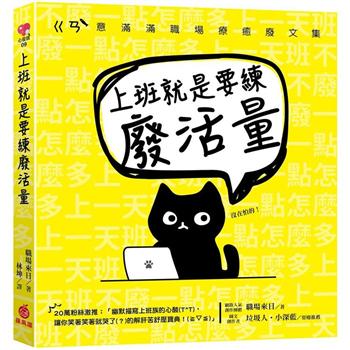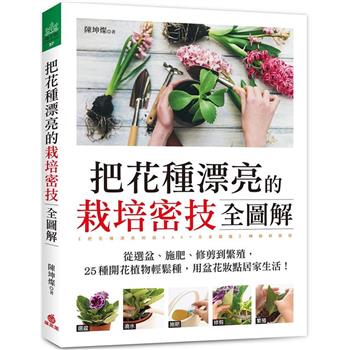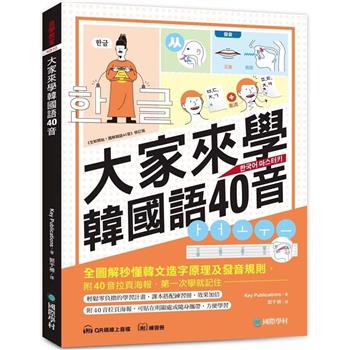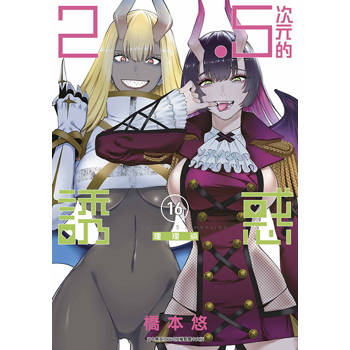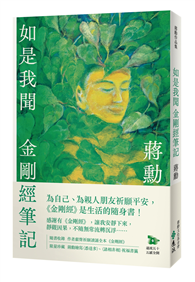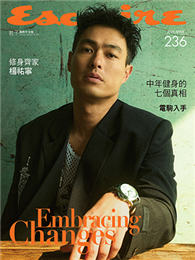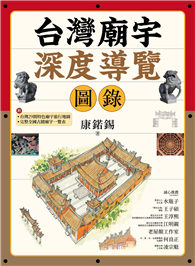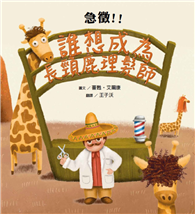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公民不盲從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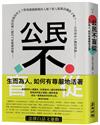 |
公民不盲從:生而為人,如何有尊嚴地活著——國家能賜死人民嗎?能投票就是民主?防疫就能限制出入境?收入低就該餓肚子嗎?……30堂基本人權思辨課 作者:法律白話文運動、李柏翰(編者)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22-06-3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4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66 |
法律 |
$ 300 |
法學總論 |
$ 300 |
中文書 |
$ 300 |
迷誠品今天讀什麼YT |
$ 323 |
社會人文 |
$ 342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人權不是特權。人權到底是什麼?
一本適合所有人閱讀的人生教科書
納稅者權利法跟我有什麼關係?家長有權利對「同志教育」說不嗎?歌手不能唱自己的歌?紅燈何時亮,幾時可尋芳?……
最實用的人權讀本,30條基本人權的探索與思辨,幫助我們真正理解人權的意涵,成為一個更進步的世界公民。
●特別推薦
一起讀判決 (人氣法律粉絲專頁)/(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周威同(國教署兒童權利公約教育人員培力計畫種子教師)/林辰(知識型Youtuber、《台灣吧Taiwan Bar》共同創辦人)/邱伊翎(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祕書長)/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張瑜鳯(資深法官,《章魚法官來說法》作者)/許全義(台中一中社會科教師)/黃丞儀(中研院法律所研究員)/黃惠貞(歷史教師深根聯盟發言人、板橋高中歷史科教師)/蔡中岳 (地球公民基金會顧問)/錢建榮(最高法院法官)/蘭天律師(依姓氏筆劃排序)
人權並非國家所賦予的權利,而是先於國家、任何社會與法律制度出現前就存在了,而人權的內涵就在於體現對人之尊嚴的尊重,每個人都是有自主性的主體,而不會淪為被他人或國家所支配的客體。
1948年12月10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那是第一份全球性的人權保障文件,這一天也被訂為人權日。
二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的人們看盡殘暴的國家機器如何輾壓自己或其他國家的人民,因此聯合國成立時,各國即把人權保障視為這個國際組織最重要的目的之一,並迅速通過了《世界人權宣言》。
/
人權法典化是為了賦予人民對抗國家暴力和歧視的武器——雖然締約或修改條文都太困難,但我們能透過重新詮釋、擴充文義,讓人權法持續保持其活力和韌性。反之,若任由政府恣意排除或限制人權內涵,將失其最初捍衛個人尊嚴及促進社會正義的精神。這也是一開始想編輯這本書的主要目標,希望提供讀者有關人權與基本自由的基本認識,學習相關語彙後,用以觀察自己與其他人的生活處境,進而勾勒出心目中理想社會的藍圖。——法律白話文運動
本書邀請一群年輕有想法、寫過多部暢銷法普書的「法律白話文運動」執筆,以明確好讀的文字,把嚴肅的法律知識,轉化為一般大眾容易理解的常識。內容以聯合國特別為青少年編寫的《世界人權宣言》簡易版三十條為基礎,從每一則法條的核心精神作闡釋,並援引國內外的案例,輔助說明該法條我們應該具備的正確觀念,探索人權樣貌,傳達人權基本知識,幫助我們更確認與思索人權的重要。
也許我們對這些人權條文並不陌生,但我們對它的內涵確實為何,其實仍然一知半解,甚或明知故犯;在世界仍然到處充斥忽視人權、侵犯人權的情況下,我們如何理解並維護自身的人權,已是一個當代的重要課題。
作為自許尊重人權的台灣,其實我們還有許多可以努力的空間,這本書深入淺出的書寫,提醒我們正視人權的重要,我們才能更往前成為一個進步的世界公民。
●內容大要
美國知名歌手小甜甜布蘭妮為何害怕父親的監管?性工作者真的不配擁有工作權?反送中運動為何衍生出抗議者被受虐酷刑?維吾爾族被中國奴役生產棉花,引起許多名牌商品抵制,中國真的吃西方人權這套?跨國同婚是否是夢一場?棒球員曹錦輝的假球案如何引用「無罪推定原則」? COVID-19 核酸檢驗報告成了遷徙自由的絆腳石?新加坡少年余澎杉(Amos Yee)在網路上批評李光耀為獨裁者,他是否「傷害他人宗教或種族情感」?土耳其海面上漂浮了一名紅衣小男孩的屍體,他足以召喚難民的無辜嗎?原住民自傳統部落領域取回木材,是否竊盜觸法?禁止穆斯林婦女穿罩袍是錯誤的法令?……
全書談及的領域眾多,包括身心障礙者、遊民、勞工、維吾爾族、人權工作者、難民、愛滋感染者……;議題多元,包括反送中、八仙樂園火燒案、死刑存廢爭議、打假球、隱私權、出版管制、兒少言論權利、集會遊行示威、罷工、迫遷、恐同、受教育權、著作權、國際人權……
從個人到社會,從台灣到世界,各式各樣的基本人權議題,在在凸顯人權脆弱的面向。當大眾被侵權時是否真能知法而保護自己的權利?「法律白話文運動」有條不紊地整理出人類與生俱有的權利,不僅讓普羅大眾閱讀本書而獲得啟蒙,更可以觀照自身本該擁有的權利,避免因為對權利的懵懂與知識的薄弱,進而喪失權利而讓生命深陷恐懼的泥淖之中。
這本書每一章談論的都是人權的缺角,唯有把破碎的缺角拼圖起來,才能更接近人權的真相。
每章末附有「思辨與討論」,延伸引導讀者對該章作進一步思考;書末並有相關人權工作者的筆記(例如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身心障礙聯盟、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等),作為對照參考,豐富對人權的探討。
●全書30章內容主旨(呼應《世界人權宣言》簡易版三十條)
第1章:我們天生自由而且平等
﹝核心概念﹞:我們生來就是自由的。我們都擁有自己的觀念和想法。我們應該被同等對待。
﹝內容要點﹞:以美國天后小甜甜布蘭妮(Britney Spears)爭取打破被監管的人生為例,談「不能以監護為藉口,限制其他權利」,並擴及台灣的情況作闡述,儘管是刑事案件中的被告也享有基本人權保障。
第2章:不該有差別待遇
﹝核心概念﹞:不管我們的差異是什麼,這些權利是屬於每一個人的。
﹝內容要點﹞:從古亭「小作所」事件談身心障礙者的困境及反歧視法。
第3章:生存的權利
﹝核心概念﹞:我們都有生存的權利,並且可以自由與安全的生活。
﹝內容要點﹞:身為遊民有罪嗎?從台北市議員應曉薇提議向無家可歸的遊民潑水驅離案例談起。國家能賜死人民嗎?人權法中最難解的爭議之一——死刑存廢的百年論辯。
第4章:不要有奴隸制度
﹝核心概念﹞:沒有人有任何權利把我們當奴隸。我們也不可以把任何人當成奴隸。
﹝內容要點﹞:國家、法律為什麼要管勞雇關係?紅燈何時亮?幾時可尋芳?探討性工作合法化之必要。
第5章:沒有折磨或不人道的待遇
﹝核心概念﹞:沒有人有任何權利傷害我們或折磨我們。
﹝內容要點﹞:從香港反送中運動談「酷刑」,看國家執法界線在哪裡。
第6章:不管到哪裡,你都有被視為人的權利
﹝核心概念﹞:我和你一樣都是人,享有的尊重和權利都一樣。
﹝內容要點﹞:新疆維吾爾族受中國壓迫,引起許多名牌商品抵制所產的棉花,中國說「不吃西方人權這一套」有理嗎?八里媽媽嘴咖啡店命案的判決,為何引發軒然大波?
第7章: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核心概念﹞: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必須公平對待我們所有的人。
﹝內容要點﹞:外國人在台工作權益差很大,白領是人才,藍領的人權呢?跨國同性婚姻在台灣的演進情況。
第8章:你的人權應該受到國家法律的保護
﹝核心概念﹞:當我們沒有受到公平對待時,我們可以要求法律的協助。
﹝內容要點﹞:從八仙樂園火災事件訴請國賠,看國家對人民的保護義務。醫療人員於工作場所遭受性騷擾與暴力相對,法律能否保障他們的人權?
第9章:沒有不公平的拘留
﹝核心概念﹞:如果沒有正當理由,沒有人有權利把我關到監獄裡裡,或把我從自己的國家驅逐出去。
﹝內容要點﹞:從台灣人權工作者李明哲入境中國被拘禁談「強迫失蹤」所帶來的傷害。
什麼是羈押?你說羈押就羈押嗎?縱使是重大刑案的被羈押人,因尚未被定罪,其人身自由仍應盡量受到平等保護。
第10章:公平審判的權利
﹝核心概念﹞:如果被審判,就應該公開進行。不該有任何人,告訴審判我們的人應該要怎麼做。
﹝內容要點﹞:即便是犯罪被告,也應享有公平審判的程序權利;情節最嚴重的罪行一定會判死?從湯景華縱火案談起。
第11章:在被證明有罪前,我都是清白的
﹝核心概念﹞:除非有證明,否則任何人都不應該被要求為某件事負刑事責任。當有人說我們做了壞事時,我們有權利去表明那不是真實的。
﹝內容要點﹞:從曹錦輝假球事件談「無罪推定」原則。「無辜人被判有罪,沒有人是自由人。」被誤關了14年的鄭性澤案帶給我們的司法正義省思。
第12章:隱私的權利
﹝核心概念﹞:沒有人可以破壞我們的名聲。如果沒有正當的理由,沒有人可以進入我家、拆開我的信件、干擾我或我的家人。
﹝內容要點﹞:祕密被人知道了是侵害我什麼權利?不想被Google不行嗎?——被遺忘權與言論自由的權衡。
第13章:行動的自由
﹝核心概念﹞:在自己的國家裡,我們有權利到我們要去的地方,並且到我們想去的地方旅行。
﹝內容要點﹞:防疫不外人權——可用提供檢疫報告當作國人入台的條件嗎?被陌生人跟蹤了怎麼辦?各國法規大不同,在許多國家甚至無能為力!
第14章:尋求安全居所的權利
﹝核心概念﹞:如果我們在自己國家裡害怕被迫害,我們有權利跑到另一個國家讓自己更安全。
﹝內容要點﹞:新加坡少年余澎杉(Amos Yee)因批評李光耀為獨裁者遭判刑後,他尋求美國的庇護,什麼是庇護?阿拉伯之春到今日,世界上出現了許多難民,更別說以前歷史上不同時期的難民,我們對難民的認知有多少?
第15章:取得國籍的權利
﹝核心概念﹞:我們都擁有權利,屬於某一個國家。
﹝內容要點﹞:從越界者與無國籍人的眼中,看見人權法的極限。從難民到無國籍兒童到台灣的新移民,關於追求國籍保障,歸化移民應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思索。
第16章:婚姻與家庭
﹝核心概念﹞:每個成年人,當他們想要的時候,都有權利結婚並擁有家庭。男人和女人結婚或分居時,都擁有相同的權利。
﹝內容要點﹞:婚姻平權里程碑:南非Fourie案。從通姦除罪化討論背後暗藏的性別壓迫。防疫時期不讓中配孩子來台是否違反《兒童權利公約》。
第17章:擁有屬於你東西的權利
﹝核心概念﹞:每個人都有權利去擁有東西並分享它們。沒有人可以毫無正當理由就拿走我們的東西。
﹝內容要點﹞: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是什麼?跟我有什麼關係?原住民自傳統領域取回木材,是否竊盜觸法?
第18章:思想的自由
﹝核心概念﹞:我們都有權利相信我們要相信的,有權利信仰某個宗教,或是當我想要的時候,可以改變想法。
﹝內容要點﹞:曾經台灣有部法律控制你的思想。國家該管制宗教嗎?民主國家有辦法讓宗教歸宗教嗎?
第19章:表達的自由
﹝核心概念﹞:我們都有權利自己做決定,去想我們所喜歡的東西,去說我們所想到的,並且與其他人分享我們的觀念。
﹝內容要點﹞:從《出版法》看台灣的民主進程。從烏克蘭感染愛滋病毒的女孩所寫的〈讓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談兒童也有說話且被聽見的權利。
第20章:公眾集會的權利
﹝核心概念﹞:我們都有權利接觸我們的朋友,並且一起和平地保衛我們的權利。如果我們不願意,沒有人能命令我們加入任何團體。
﹝內容要點﹞:遊行抗議沒錯,除非它造成危險或蓄意破壞法治。從香港反送中事件談「禁止蒙面」上街頭的合法性問題。
第21章:參與民主政治的權利
﹝核心概念﹞:我們都有權利參與我們國家的政治。每個成年人應該被允許選擇他們自己的領袖。
﹝內容要點﹞:從日據時期台灣人推動「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爭取頭一次的民主成果談起。
能投票就是民主嗎?罷免案如何進行?2019年的香港議會選舉給台灣的提醒。
第22章:社會保障的權利
﹝核心概念﹞:我們都有權利負擔得起住宿、醫療、教育與兒童照顧,當我們生病或年老時,有足夠的錢去生活及獲得醫療協助。
﹝內容要點﹞:生計出現困難時,人人都應受到來自國家的支持。礙知與愛滋的無間道:從不歧視原則談起。
第23章:工作者的權利
﹝核心概念﹞:每一個成年人都擁有工作、公平的工作報酬,以及加入工會的權利。
﹝內容要點﹞:談勞工的不合作運動——罷工權。「職業災害」哩干災?
第24章:休息和休閒的權利
﹝核心概念﹞:我們都有放下工作,休息和放鬆的權利。
﹝內容要點﹞:工作誠可貴,身體價更高——談超時工作的法律問題。最陌生的熟悉人:台灣長期照顧政策中的外籍家庭看護工應該有的保障。
第25章:良好生活條件的權利
﹝核心概念﹞:我們都有權利好好過日子。母親和孩子、老人、失業的或有障礙的人,都有權利被照顧好。
﹝內容要點﹞:華光社區的迫遷安置難道是種恩賜,而非權利?從「恐同」現象談性/別少數群體的健康權。
第26章:接受教育的權利
﹝核心概念﹞:受教育是一種權利。上小學應該免費。我們應該了解如何與他人相處。家長能優先選擇我們該學的是什麼。
﹝內容要點﹞:學校與學生間的「特別權力關係」指的是什麼?家長有權對「同志教育」說不嗎?從英國「伯明罕抗議事件」反思台灣現況。
第27章:著作權
﹝核心概念﹞:著作權是用特別的法律,來保護個人的藝術及文學創作;其他人如果沒有得到同意,不可以複製。我們都擁有權利以自己的方式生活,並享受藝術及科學所帶來的好處。
﹝內容要點﹞:歌手不能唱自己的歌?談林暐哲訴吳青峰案的合約問題。台灣第一起傳統智慧創作侵權事件——奇美部落提告原民會。
第28章:生活在一個在乎人權的世界的權利
﹝核心概念﹞:好的秩序必須要存在,我們才能夠在自己的國家和全世界各地享受權利及自由。
﹝內容要點﹞:人權保障不僅僅靠規範,更有賴健全的監督機制;良善的全球秩序,取決於良善的國內與國際環境。
第29章:責任
﹝核心概念﹞:我們對其他人是有責任的,而且我們應當保護他們的權利及自由。
﹝內容要點﹞:從菲律賓的賈巴里被槍殺案,談「生命權」是一項不得減損之最高權利,即使在武裝衝突和其他威脅國家存亡的公共緊急情況下。對於女性生育與墮胎權利的探討。
第30章:沒有人可以剝奪你的人權
﹝核心概念﹞:人權宣言是最低標準。不應該用保障某一人權當作藉口,合理化對其他人權的侵害。
﹝內容要點﹞:從英國商人林克穎在台酒駕致死案,談台灣監獄的人權問題。人權不是特權:「反毒戰爭」的健康權爭議。
後記:人權工作者的筆記
作者簡介
法律白話文運動
由一群致力於散播法治種子的法律人成立的媒體公司。對一般人而言,本該為人民服務的法律,因為內容有如文言文難懂,反而離人民愈來愈遠。於是,我們想透過網路與科技,發揮內容媒體的各種想像,提供值得信賴的知識,並減少廉價批評的出現。我們相信,法律是人類史上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搭起一座理性的橋梁,用共存與共榮連結立場衝突的人們,而法律白話文運動希望為閱聽眾們打造這座橋梁,一同思考議題、關懷彼此,並一起塑造屬於臺灣的法律文化。
網站:plainlaw.me
Facebook粉絲專頁:法律白話文運動 Plain Law Movement
Instagram:plainlaw.me
Podcast:《法客電台》
編者/李柏翰
國立台灣大學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助理教授,對人權與全球衛生政治很敏感。跨領域研究者,是法律白話文運動國際法資深編輯,常常在法律書寫中偷渡性別與解殖觀點。現在亦擔任學術期刊《女性主義評論》(Feminist Review)編輯,成為勞碌日常的逃逸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