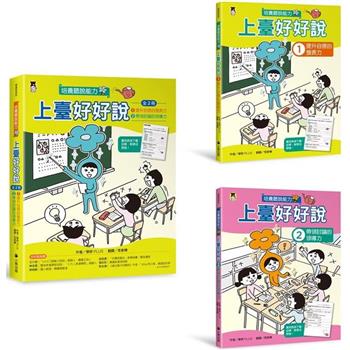「我們身在何方?我在黑暗之夜寫下此文。在戰爭中,黑暗不與任何人為伍;在愛裡,黑暗確認了我們緊緊相依。」——約翰.伯格
最具影響力的藝術批評家、美學理論大師當代評論短文集
「留住一切親愛的」
我們如何支撐自己生存下去?權力在誰手上?我們又如何正在改變自然?
約翰.伯格充滿啟發性的優雅散文,不僅對「人」投以深情的關注,
透過又輕又重的文字,也是這位作家最靠近卑微人性的思索,
引領我們通往每個濃烈卻清徹的心靈。
政治抵抗在今日有何意義?
約翰.伯格以發自內心的熱情,提出深刻而激進的反思。
*「我在這黑暗之夜書寫,但我看見的不只是暴虐。倘若只有暴虐,我將沒有勇氣繼續執筆。我看到人們沉睡、忙碌、起床喝水、低訴他們的計畫或恐懼、做愛、祈禱、在家人的鼾聲中烹煮食物,在巴格達,在芝加哥。(是的,我也看到永不屈撓的庫德人,其中有四千人在美國的默許下,在海珊政權的煤氣室被毒死。)我看到糕點師父在德黑蘭工作;被當成盜匪的薩丁尼亞牧羊人在羊群旁小眠;我看到柏林腓特烈森林區一名男子穿著睡褲、拿著啤酒、讀著海德格,他有雙無產階級的手;我看到一艘非法移民的小船停在西班牙亞利岡特海岸附近;我看到馬利的一名母親正搖著嬰兒入睡,她叫阿雅,意思是「誕生於週五」;我看到喀布爾的廢墟,一名男子正在返家途中;而且我知道,儘管痛苦,但倖存者尋覓並聚集能量的聰明靈敏並未稍減,甚且不斷精進,這其中蘊藏著某種精神價值,某種類似聖靈的東西。儘管世局黑暗如夜,但我對此深信不疑,雖然我道不出其中緣由。」——〈我們身在何方?〉
「約翰‧伯格書寫重要之事,而不只是有趣之事。在當代英語文字圈內,對我而言,伯格擁有無與倫比的地位。自D. H. 勞倫斯之後,不曾有其他作家像他這般對感官世界投以如此關注,並對道德良心寄予如許同情。」——蘇珊.桑塔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