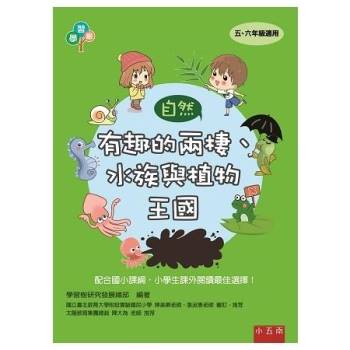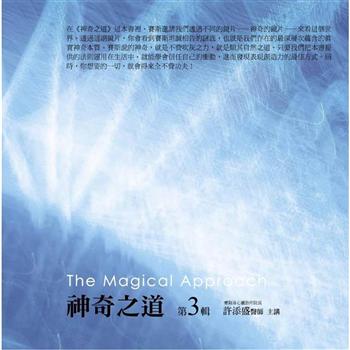圖書名稱:我還能再看到幾次滿月?
【台日同步出版,坂本龍一最後親校作品】
創作,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世界級的音樂家.人生的精彩終章
從《音樂使人自由》到《我還能再看到幾次滿月?》,以文字為樂器書寫留給後世的決定性自傳。
【感動推薦】
BTS・SUGA
林強 音樂工作者
侯孝賢 電影導演
馬世芳 廣播人、作家
陳德政 作家
廖偉棠 詩人
蔡明亮 電影導演
因為音樂,因為電影,四年前的五月坂本龍一來台北時,林強約我們一起吃飯,我們一見如故好像老朋友,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他。今年三月他去世,比我還小五歲。這本書他講到滿月。我想著波赫士的詩,寫給他最後的伴侶瑪麗亞.兒玉的,他說那輪金燦,因人們無數世紀的凝視使它蓄滿了淚水,他說你看,它就是你的明鏡。我想,有許多不斷從地球上消失的東西,只存放在月亮那裡吧。──侯孝賢
♯藝術千秋,人生朝露
「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壽命就只剩半年。」二○二○年十二月,坂本龍一發現癌細胞轉移時,醫師告訴他這句話。但是在那一天來臨前,他還有些話必須要說。無論是支撐著他創作活動與社會運動的哲學思想、對坂本家歷史與家族的感情,還有關於自己離去後的世界……
♯工作、思想回顧,親校參與的最後作品
二○二二年七月開始,由日本資深媒體人鈴木正文採訪坂本龍一,在日本文學刊物《新潮》開始主筆專欄。雜誌專欄以二○○九年出版的《音樂使人自由》續集為出發點,回顧這十多年來的人生經歷:與癌症共存、參與震災活動、對戰爭及核能的觀察,也講到旅行與創意,在工作上從能樂講到指揮,也有提到二○一九年來台灣參與活動、研究原住民音樂的所見所聞。
♯記錄生命最後一段日子的日記
坂本龍一曾說:「夏目漱石因為罹患胃潰瘍而死的時候也才四十九歲。相比之下,即使我在發現癌症時的二○一四年就以六十二歲身亡,也算是非常長壽……我所尊敬的音樂家們直到臨終前都持續寫著曲子。我希望能像敬愛的巴哈和德布西一樣創作音樂,直至最後一刻。」書末收錄鈴木正文代坂本龍一撰寫的後記,公開坂本龍一大量手寫、打字的最後隻字片語,都能感受得到其對音樂與生命的濃烈情感。
作者簡介
坂本龍一
一九五二年出生於東京,東京藝術大學碩士。
一九七八年推出出首張演奏專輯《 Thousand Knives》,同年與細野晴臣、高橋幸宏合組音樂團體「YMO」,後於一九八三年解散。之後以個人名義發表了《音樂圖鑑》、《Beauty》、《async》、《12》,不斷追求創新的態度贏得世界的迴響。參與演出及配樂的電影《俘虜》曾獲得英國影藝學院最佳電影配樂,《末代皇帝》則分別獲得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最佳電影配樂,以及葛萊美獎最佳影視媒體作品配樂專輯殊榮。他同時也積極跨界,創作《LIFE》、《TIME》等舞台作品、在韓國與中國有大型裝置展。對於環保、和平議題也多所建言,創立森林保育團體「More Trees」,並成立「東北青少年管弦樂團」,支持三一一受災地區青少年的音樂活動。
二○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辭世。
譯者簡介
謝仲庭
音樂工作者、翻譯。熱愛音樂、書本、堆砌文字及轉化語言。譯有:《悠悠哉哉》、《攻殼機動隊1.5》、《寺島町奇譚》、《Designs》、《寶石之國》等。
謝仲其
譯有:《我是漫畫家》、《光年之森》、《引路者》、《失蹤日記》、《我很好》、《攻殼機動隊1》、《攻殼機動隊2》、《世界第一簡單傅立葉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