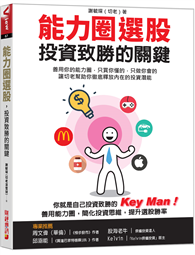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後來,我告了報社老闆的圖書 |
 |
後來,我告了報社老闆:一本直擊新聞製造內幕的前總編輯回憶錄 作者:大衛‧希門內斯 出版社: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12-0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40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94 |
報導文學 |
電子書 |
$ 294 |
報導/紀實文學 |
$ 332 |
新聞學 |
$ 332 |
大眾傳播 |
$ 332 |
讀書共和國 |
$ 370 |
中文書 |
$ 370 |
Books |
$ 37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對從業二十多年的資深新聞記者來說,
最險惡的新聞現場,不在阿富汗、北韓等地──
而在總編輯辦公室!
★西班牙新聞業最不樂見出版的一本書,頂尖跨國製片公司影視改編中
★一段捍衛新聞獨立性、決心抗衡政經勢力宰制的戰鬥人生
★西班牙大報《世界報》前總編的良心告白!好奇新聞製造真相者必讀
新聞媒體信誓旦旦地說,他們會告訴你真相;
這位前總編輯將告訴你,什麼是新聞媒體的「真相」。
「我永遠和記者與讀者站在同一陣線。
該我離開這裡的那天,我的背包會與今天帶來的一樣,輕盈沒負擔。」
──大衛.希門內斯的總編就任演說
大衛‧希門內斯成為《世界報》總編輯之前,二十年來奔走於世界各地的戰爭、災難及革命現場,發出一則則新聞報導。但他沒萬萬想到,回到報社總部擔任總編,才讓他真正涉身最槍林彈雨的新聞製造現場,看見那些不可告人的「真相」:
#「教主」這位老謀深算的上司令人疲於應付:表面說支持數位轉型改革,卻不給資源;一再干預新聞報導內容,為權貴朋友們說情;甚至利用裁員策略,讓總編裡外不是人。
#「當權派」始終如揮之不去的頂上烏雲:舉凡政治人物、財閥總裁,每天傳來無止境的抗議訊息,並透過利誘、脅迫等種種手段,從不放棄插手控制新聞走向。
#報社內的人事政治也一樣棘手:守舊的「貴族們」不思長進;野心勃勃的「副座」隨時想奪位;「鼠輩」記者自甘墮落收取外部好處,還以在社內散布流言為樂。
大衛‧希門內斯以獨特視角,闡述他如何度過在報社編輯總部裡的那一年。擔任總編輯,原本是令人心生嚮往的挑戰,但後來,卻漸漸演變成一場維護新聞獨立性的防衛戰。在作者筆下,操控一國運作的各方派系勢力盡顯無疑:國家總理、王室成員、政府部會首長、政治人物、企業財閥──當然,還有新聞媒體與記者們。他以犀利的文字,描繪出這些力量如何盤根錯節地交織成新聞業內最幽暗的祕密,充分解釋了新聞媒體與權貴人士之間如何相互運作著「恩惠遊戲」──以及不願意參加這項遊戲的人(如他本人),究竟得付出什麼代價。
作者不僅如實寫出他與上述各路人馬斡旋交鋒的受創與致勝經驗,與此同時,身為總編輯的他還要因應當前全球新聞業所共同面臨的考驗:讀者流失、數位轉型、罷工、裁員──這些危機他一項也都沒少碰上。
本書是作者的深刻自白,是來自西班牙大報之一的總編輯辦公室的現場紀實,歷歷在目地刻畫出一位新聞從業人員必須面對的倫理道德、人際關係、人性考驗等兩難境遇。
‧從編輯台後的祕密交易,一路直探組織內核的腐敗氣息,新聞媒體的祕辛與詭計無所遁形,更清楚感受各方勢力如何共同形塑「媒體第四權」。
‧作者寫志業的實踐,寫抉擇的艱難,更寫重重人性考驗中的莫忘初衷,細述在龐大組織中仍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者的心情。
「現在換作是我,也願意與我們駐外記者之中任一人交換,將總編輯室裡該做的事都留給他,換我前往世界上衝突最嚴重的地方採訪──在那些地方,人們幹壞事,為的是比升職要嚴重許多的事,而且你會比較清楚知道子彈是從哪飛來。」──大衛‧希門內斯
作者簡介
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énez)
屢獲殊榮的作家和記者,也是西班牙重要媒體《世界報》的前總編輯。目前是西語版《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並持續為多家著名雜誌,如《浮華世界》等等做專案報導,同時也在新聞院所授課。
作為一名駐外記者和戰地記者,希門內斯報導了全球數十個國家的衝突、革命、自然災害和危機。大衛‧希門內斯曾獲選為哈佛大學尼曼學人獎學金得獎人(Nieman fellow)。他所寫的新聞報導刊載在國際各大主流媒體上,包括《衛報》、《星期日泰晤士報》、《多倫多星報》(The Toronto Star)和《晚郵報》(Corriere della Sera)上,他也為 CNN 和 BBC 撰稿。
他的著作《雨季的孩子》、《被遺忘的亞洲碎片》、《喀布爾的門僮》(暫譯)也已被翻譯成六種語言出版。本書則是一部關於他在《世界報》擔任總編輯的暢銷回憶錄,目前正由頂尖跨國製片公司 Fremantle 進行影視改編。
譯者簡介
馬巧音
西班牙語口筆譯者,講台語長大的屏東人,進入輔大西語系邂逅了不同世界的各種美麗可能。
醉心藝術電影及文字寫作,外派西語國家工作多年,回台後現為專職的接案西語譯者。歡迎交流:veritomcy@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