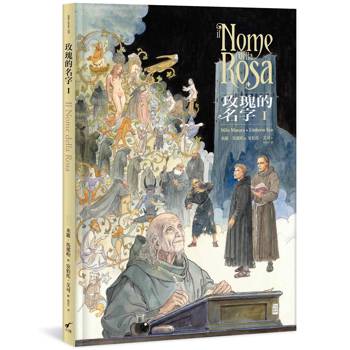「文學或許能成為那顆照見未來的水晶球,以當下的經驗為養料,去記住現在、揣想將來。」──黃宗潔
從台灣到香港,柏林到紐約,各地視角一次到位
34位華文名家為疫情寫下的文字
上田莉棋/川貝母/牛油小生/何曼莊/利格拉樂.阿𡠄/吳俞萱/宋尚緯/李欣倫/林俊頴/阿 潑/洪昊賢/洪明道/洪愛珠/孫梓評/振 鴻/郝譽翔/馬尼尼為/馬翊航/張亦絢/張怡微/連明偉/陳浩基/陳 慧/黃 怡/葉覓覓/廖偉棠/廖 瞇/潘國靈/蔣亞妮/謝曉虹/隱 匿/韓麗珠/騷 夏/龔萬輝
病毒的威脅逼迫我們重新去量度自己與世界的距離,封城、限聚、居家隔離……
人成了名副其實的孤島。
2020年始,疫情時代降生,人們不得不習慣口罩竄上自己的臉孔,拉遠與親愛之人的距離。世界劇烈地移動著,然而我們生活的方式究竟有何改變?
關於「日常」的崩解,郝譽翔〈日常生活的恐怖〉寫及疫情期間一位在家的母親無處可躲,日日是重負;張亦絢〈稀奇古怪的故事〉則大膽揣測口罩將改變一世代人們的表情;馬翊航〈間格與旋轉的裝置〉提到居家工作期間,只有UVC消毒燈罩能帶來太陽溫暖的氣味。
關於「異域」的現場,何曼莊〈寂靜中的聲音〉道出紐約封城的焦慮與出口;潘國靈〈役年・疫年——窗外・窗內〉描繪反送中運動到疫情爆發後香港的變動;孫梓評的〈漂流物〉談及前往柏林駐村卻遇疫情折返的窘境。
關於「超現實」的境遇,龔萬輝〈時鐘旅館〉揣想了當欲望不會因疫情停歇,填補內心的匱乏需要什麼樣的代價;川貝母〈鼴鼠雨果〉則描繪出封城後最熱門的行業竟是理髮師,只好列由政府規管,成為最自由也最不自由的職業。
本書邀請了34位華文作家為疫情進行創作,當中有詩、散文以及小說。來自不同世代與地區,多種觀察的面向,讓你一次看完大疫之年的人生百態,也借此書寫作為連結,願在困頓的時刻,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內文摘選
「疫中種種,如發生在塑膠泡中,透明而抽離。這是一次集體的靈魂出竅,彷彿我與我身世界,從來是一個巨大而抽象的概念,而我們經此一回,終於知道。」──洪愛珠〈與世有隔〉
「疫情遮蔽下,究竟該如何與靈魂保持親近?太遠,宛如兩人對峙談判;太近,逾越了,你腦中被電視機裡各種令人憂懼的報導所構成的警報器即刻大響,倏而掩去了靈魂聲音。」──振鴻〈抵達之前〉
「人總想看被遮掩起來的事物,其實底下什麼都沒有,誰說埋在土下的盒子裡一定有祕寶,有時候,只是想要掩埋一些什麼的過程。」──蔣亞妮〈聖母時間〉
「蜂群如風起的黃昏,他拍死一隻/在茶杯或者歌唇的旁邊/暮色就蜚短流長了/他的尾指沾了酸掉的蜜。」──廖偉棠〈愛在瘟疫蔓延時〉
「因為只有內心強壯,才能讓我們在絕望時仍能作出選擇,擁抱存在,受傷害而沒有被擊倒。」──陳慧〈白蝶〉
本書特色
★一本當代華文作家對於疫情的觀察與書寫!
★東華華文學系教授黃宗潔主編
★從台灣到香港、柏林到紐約,各地視角一次到位
名人推薦
江鵝(作家)
李金蓮(作家)
李屏瑤(作家)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孤絕之島:後疫情時代的我們 (電子書)的圖書 |
 |
孤絕之島:後疫情時代的我們 作者:黃宗潔主編 出版社: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12-2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25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315 |
小說 |
$ 338 |
Books |
$ 356 |
現代散文 |
$ 356 |
現代散文 |
$ 356 |
Books |
$ 396 |
中文書 |
$ 405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孤絕之島:後疫情時代的我們 (電子書)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編者簡介
黃宗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及香港當代文學、家族書寫、動物書寫等。著有《倫理的臉:當代藝術與華文小說中的動物符號》、《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本書獲Openbook 2017美好生活書)、《生命倫理的建構:以臺灣當代文學為例》、《當代臺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與黃宗慧合著有《就算牠沒有臉:在人類世思考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難題》(本書獲Openbook 2021年度生活書)。其他書評與動物相關論述文字散見《鏡文化》、《鏡好聽》、《新活水》等專欄。
封面插畫簡介
陳沛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現職插畫接案工作者。 作品散見國內出版之童書、雜誌、繪本,近年開始創作圖像小說。喜歡樸拙手感 的畫風、情感內斂的敘事風格。
黃宗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及香港當代文學、家族書寫、動物書寫等。著有《倫理的臉:當代藝術與華文小說中的動物符號》、《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本書獲Openbook 2017美好生活書)、《生命倫理的建構:以臺灣當代文學為例》、《當代臺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與黃宗慧合著有《就算牠沒有臉:在人類世思考動物倫理與生命教育的十二道難題》(本書獲Openbook 2021年度生活書)。其他書評與動物相關論述文字散見《鏡文化》、《鏡好聽》、《新活水》等專欄。
封面插畫簡介
陳沛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畢業,現職插畫接案工作者。 作品散見國內出版之童書、雜誌、繪本,近年開始創作圖像小說。喜歡樸拙手感 的畫風、情感內斂的敘事風格。
目錄
輯一、在我回不去家的路上
在我回不去家的路上 /馬尼尼為
漂流物 /孫梓評
寂靜中的聲音 /何曼莊
聖母時間 /蔣亞妮
與世有隔 /洪愛珠
抵達之前 /振鴻
那一天,那一年 /阿潑
疫期之異與常 /利格拉樂.阿𡠄
日常生活的恐怖 /郝譽翔
他給我一團草莓衛生紙 / 無處安放 /廖瞇
離‧散‧聚 /上田莉棋
放風 /黃怡
輯二、愛在瘟疫蔓延時
愛在瘟疫蔓延時 /廖偉棠
殘響 /吳俞萱
如何測量插管的深度 /洪明道
彼岸的信鴿 /連明偉
在記憶力不及的迂迴管線中迴響 /牛油小生
出了象牙之塔 /張怡微
方舟 /李欣倫
時鐘旅館 /龔萬輝
稀奇古怪的故事 /張亦絢
鄰人哥吉拉 /陳浩基
歡樂時光 /洪昊賢
輯三、病從所願
病從所願 /隱匿
在人的底部抵達神的地步 /葉覓覓
黎明前的夜 /宋尚緯
阿基里斯的腳踝 /騷夏
間隔與旋轉的裝置 /馬翊航
夜行與日走 /林俊頴
鼴鼠雨果 /川貝母
空琴演奏會 /韓麗珠
役年・疫年——窗外・窗內 /潘國靈
隔離 /謝曉虹
白蝶 /陳慧
孤絕之島-作家簡介
在我回不去家的路上 /馬尼尼為
漂流物 /孫梓評
寂靜中的聲音 /何曼莊
聖母時間 /蔣亞妮
與世有隔 /洪愛珠
抵達之前 /振鴻
那一天,那一年 /阿潑
疫期之異與常 /利格拉樂.阿𡠄
日常生活的恐怖 /郝譽翔
他給我一團草莓衛生紙 / 無處安放 /廖瞇
離‧散‧聚 /上田莉棋
放風 /黃怡
輯二、愛在瘟疫蔓延時
愛在瘟疫蔓延時 /廖偉棠
殘響 /吳俞萱
如何測量插管的深度 /洪明道
彼岸的信鴿 /連明偉
在記憶力不及的迂迴管線中迴響 /牛油小生
出了象牙之塔 /張怡微
方舟 /李欣倫
時鐘旅館 /龔萬輝
稀奇古怪的故事 /張亦絢
鄰人哥吉拉 /陳浩基
歡樂時光 /洪昊賢
輯三、病從所願
病從所願 /隱匿
在人的底部抵達神的地步 /葉覓覓
黎明前的夜 /宋尚緯
阿基里斯的腳踝 /騷夏
間隔與旋轉的裝置 /馬翊航
夜行與日走 /林俊頴
鼴鼠雨果 /川貝母
空琴演奏會 /韓麗珠
役年・疫年——窗外・窗內 /潘國靈
隔離 /謝曉虹
白蝶 /陳慧
孤絕之島-作家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