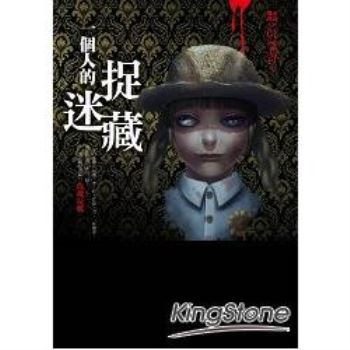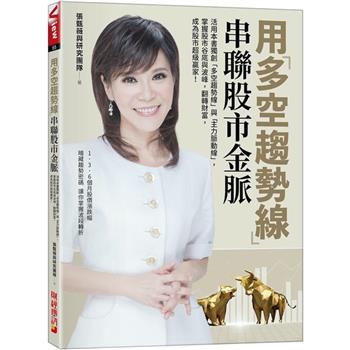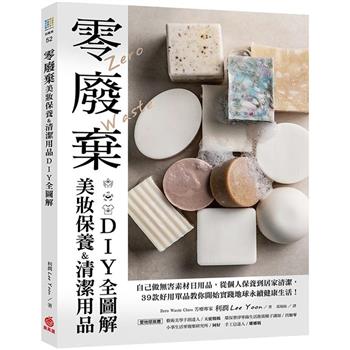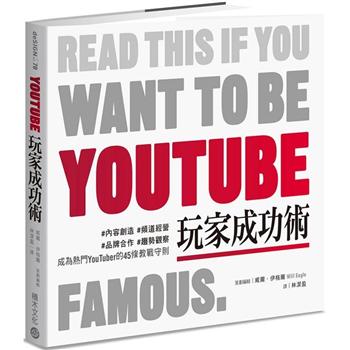★2000年後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小說之一
★新增收錄:〈再次相信:寫在《永別書》初版十年後〉、〈字母會S:精神分裂〉、圖輯
▎奇形怪狀的台灣歷史,慘絕人寰的愛欲重生
▎獻給所有孩子氣的痛苦與悲傷
千萬別幻想著,你可以毫髮未傷地從這個故事中脫離。
你不知道的是,你可能會多恨這個故事,或是說故事的人。
記憶會傷人——這是賀殷殷,從出生始,就難逃的命運。父親告訴她:「賀殷殷的殷,是殷海光的殷。」但是這故事並不單單勾起早期的民主運動記憶,有一天,還要溯及日治時期閩客通婚的變形家庭。在此誕生的賀殷殷之母,將是文學中非常難以消化的角色——口口聲聲保衛客家文化的她,能把最簡單的台灣事說得破爛不堪。然而這全只因為國民黨政權施加於台灣島的噤聲歷史使然嗎?
除此之外,透過私密、甚至是檯面下的小恩小怨小彆扭,作者刻畫了比使命感更複雜的,那些催生,或延誤同志書寫的頡抗因素。那些,文學史絕對不會告訴你的事⋯⋯
●
張亦絢:「雖然我個人有點不甘願,但我最後還是發現,這終究是一個關於愛的故事。——認同,有那麼難嗎?無論是族群的、或是性別的認同⋯⋯我的答案是,沒有錯,認同有夠難,難上還加難。——但這不代表我們會轉身離去。這本書的企圖,仍然是種共患難,一個『我在這裡』的認真回聲。關於寂寞及其未被毀滅。」
「《永別書》在我看來,最根本的,不過就是它保存的『震驚』。文學並不先天地,為所有苦難預備好語言。(⋯)二〇二四年,因為到愛荷華駐村,我有機會以英文朗誦《永別書》。在旅館練習時,我每每泣不成聲。這對我自己來說,也是震撼的教育。我到這一刻才知道,完成這部小說,最難的部分,其實是『忍住淚水』。」
作者簡介:
張亦絢
出生於台北木柵。巴黎第三大學電影暨視聽研究所碩士。早期作品曾入選同志文學選與台灣文學選。著有《愛的不久時》、《永別書》(以上國際書展大獎入圍)、《性意思史》(Openbook與鏡文學年度好書獎)、《我討厭過的大人們》、《晚間娛樂:推理不必入門書》、《感情百物》等數種。專欄「我討厭過的大人們」獲金鼎獎最佳專欄寫作。「麻煩電影一下」(BIOS Monthly)、「想不到的台灣電影」(《FA電影欣賞》)作者。曾任台北藝術大學、臺灣大學川流臺灣文學講座駐校作家。曾於德國柏林駐村、二〇二四年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作家。《永別書》獲《文訊》頒發「二十一世紀上昇星座」榮譽,並為二〇一七法蘭克福國際書展臺灣館選書。她也為臺灣文學館策展。
網站:nathaliechang.wixsite.com/nathaliechang
章節試閱
▎致讀者
各位《永別書》的讀者,大家好:
現在您手上的當然是一本虛構小說。儘管如此,我仍舊好心提醒您,在所有情節上,如有雷同,純屬巧合。書中述及現實世界中確有其蹤的人事物,採取的是小說保存巷議雜談的傳統。此書既非考據文章,更無意代筆歷史。若想了解任何細節真相,請求教於嚴謹的研究與書籍,或是親身查證。小說在使用外文時,有時選擇將中文譯出,有時否,這是作者基於對小說樣貌的考慮,並非編輯上的遺誤。對於不能講述一個更甜美的故事,我滿懷歉意,但並無悔意。如果在此有什麼祝禱之話好說──我深深希望,相信小說,終究能夠促進各位的幸福。
__張亦絢 二〇一五.十.十六
▎第一章
我真的打算,在我四十三歲那年,消滅我所有的記憶。
這是個狂野的夢想?是嗎?我倒沒想到可以用幽默感來面對這事。幽默感啊,總是不錯的。是我喜歡的東西。這背後有個悲劇吧?這一點我還沒開始想呢。或許吧,但我還不知道呢,究竟什麼可以稱為悲劇──。什麼可以不稱為悲劇。說是悲劇好像有點太唬人了,簡直像穿了戲服,在轟隆轟隆的音樂裡面。
或許有些政治意味吧?別嚇我,消滅記憶怎麼會是政治呢?一向就只有記得、不忘記,才稱得上政治呀。更何況,我是自願地、自動自發地,消滅我的記憶,這不牽涉到任何別人,不,這跟政治絕對扯不上什麼關係,至少在政治這詞的高尙意涵上。
這麼說來,你不打算政治也不打算高尙──或許你是打算犯罪吧?哎呀呀,事情說得越來越有趣了,真令我煩惱。如果是,你打算告發我嗎?去哪裡告發呢?告發一個消滅記憶的人,這可是比消滅記憶更困難的事吧?尤其是我將消滅的,不是任何其他人的,而是專屬於我一人獨有的記憶。
說起來,不高尙或是犯罪的事,人人都在不知不覺中進行。說真的,我想我要做的事是很普遍地,不同的人,因為不同的原因,每天都做上一點。但是像我這樣,把計畫訂得如此明確,又如此重視過程,或許,就沒那麼普遍了。
我想把話說得更清楚些。我八十六歲的老阿嬤在世時得了失憶症,她既認不得家門口的街道,也分不清我們這些孫子孫女誰是誰,變得非常麻煩──我所想要的,不是這種。當然我也不打算拿根棍子敲昏自己,或是把腦袋往牆上撞那樣,這或許會使我腦震盪,或是變傻,但未必會真的消滅我的記憶。我對我的目標是認真的,消滅記憶是多麼要緊的一件事,要是我變傻了,我看恐怕成功率就不大了。我要消滅最特殊的成分,不是像記得自己的住址,或是如何騎自行車這樣的記憶。
在我的理想藍圖中,記憶消滅後的我,可以跟一般人無異地生活與社交,可以工作,也可以說笑話,或許還更博學多聞,可以背誦莎士比亞的長句,再加上五湖四海中所有的水壩名稱──為什麼要記得水壩的名稱?我也不一定要記得水壩的名稱,把它換成別的東西也成。總之,我想我可以在外觀上打扮成一個有記性的人,但就是不需要有「我的記憶」了。這很難了解?難懂?讓我先說說,我是怎麼發現這件事是可能的:我完全是無意之中發現的。
我第一次夠有意識到這件事,是在惠妮休斯頓死去的那幾天。
惠妮休斯頓是誰,現在你很容易可以在網路上查到,如果你想知道她這部分,你自己去查就是了。假如資料有錯,我也沒辦法,畢竟我對她知道的也不多。雖如此,我這一生至今為止,卻一直小心翼翼提防著她,彷彿她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敵人,那樣提防她活了過來。但是她始終陰魂不散。我想想看,這要打哪裡說起呢?
惠妮休斯頓唱過一首歌,叫做〈心碎者何去何從?〉。在我十三歲時,有個人,提示了我這個歌名:我說提示,真的是種提示。這人說:如果妳想聽英文歌,妳可以聽這四首。然後有張字條就交到我手上,上面用英文字寫了四首歌的歌名與歌手名。
這四首歌分別是芝加哥、混、皇后合唱團以及那首我說的惠妮之歌。我之所以把它們都交代出來,是因為這些歌與我的記憶關係錯綜複雜。混與皇后合唱團的主唱,他們竟然都同志甚深──皇后的弗萊迪,我之後還會提到,他因為愛滋去世,還是這四個歌手中最長年陪伴我,成為我整個精神上美學空氣的一個──一個聲音。
弗萊迪是個在英國的帕西人,他跟坦尙尼亞和印度都有些關係,我們談了那麼多的後殖民大師霍米巴巴,巴巴的帕西背景什麼孟買雜燴之類,但是天啊天啊──啊不是的,我的重點並不是同性戀或後殖民,何況,我雖然知道一個男人的樂團,叫自己皇后叫自己QUEEN,大概不會正常到哪裡去。但要說我就嗅出什麼同性戀的東西,可就差遠了。我沒特別感覺到這部分,就像「性」一樣,我不是不知道它的存在,也不是全無聽聞或經驗,但它終究是很混沌。當一切還在我年紀輕輕的生命裡時。
QUEEN對那時的我來說,自自然然地──只等於音樂──當我崇拜地說到,QUEEN的人聲與配器真是無與倫比,我從沒想到什麼同性戀或是後殖民東西。直到有天,我已經過了三十歲,我在上完床後,在床上提到QUEEN的音樂特殊性,從當時男人深受傷害的臉色,我才忽然意識到:我可真是漏掉某些許多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了。附帶一提,當時我人不在台灣。我雖然離QUEEN的所在地只有一個海洋,只要坐個什麼之星的火車就會到達,但我對它的認識仍完好地以台灣青少女的記憶所保存,我的地理位置並沒讓我新學到什麼,我想到有個「理所當然之事」,是在床上發言不慎之後。
理所當然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呢?我之後也許會說到,也許不會。但現在讓我回來說惠妮休斯頓。在我的青春期,我沒聽過其他三人的事蹟,我喜歡音樂,但我是對流行慢半拍的那種青少女。一直到「混」解散了,我才知道有這個樂團。我可以說一件事,讓你明白我是多麼經常不在狀況內:當我讀國中時,我的國中發起過美化廁所的運動,是真的,不只是運動,而且還是全校競賽。敝班級還拿了冠軍。哪個國中那麼無聊?就是台北市的一個國中。你覺得這很無聊?那我很慶幸地告訴你,我對這個競賽一點貢獻都沒有,但我還記得這事,是因為在美化廁所的過程中,我得罪了班上的一個同學。她把心愛的「杜蘭杜蘭樂團」的海報帶來,深情地將她的偶像指給我看,因為我是一個樂意與人為善的好同學,我於是認真地看了那海報,並以同樣深情地回答她:「這人的臉長得像小鳥的臉耶!」──結果導致這個同學,氣得一星期都不願意跟我說話。
大家崇拜的都是歐美的樂團歌手嗎?也不盡然。那時還戒嚴啊。現在的七年級對戒嚴是怎麼回事,一點概念都沒有。有天有個七年級告訴我:「『戒嚴』這兩個字只會讓我們想到,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發生的事,就像『古早味』一樣。」我差點沒翻臉:「台灣戒嚴三十八年,是全世界戒嚴最長時間的國家,別的不知道,至少這點妳要記得呀。」但她會記得什麼呀?就算她如我所說,記得「戒嚴三十八年以及破世界紀錄」,你說這就算記得嗎?那不過就是一堆字罷了。不可能地,記得──是不可能地。
所以我說記憶這事不是那麼簡單,用文字記起來的東西,或許是最空洞的。七年級的絕不會像我們六年級的那樣記得戒嚴,但四五年級的,你知道嗎?我覺得,他們又記得太牢了,有時會讓我想說:難道你們都忘記,已經解嚴過了嗎?真的。去年我碰到個四年級的做紀錄片的,他說到二二八,竟然還很噤寒,他說到王添灯的弟弟,卻不敢把王添灯的名字說出來。散場後我忍不住去找他,問:「你說的王姓二二八受難者,是不是就是王添灯呢?」果然就是。
我為什麼知道?我告訴你,這裡面有個很美的東西,我始終忘不掉。王添灯是開茶行的(紀錄片的主題是茶不是二二八,但茶和紀錄片說真的也不是我的興趣,我在因為走錯地方才聽到這場演講的),他們說,王添灯女兒小的時候,茶行的工人們會把她擲到茶行中的茉莉花茶叢裡讓她玩,當然這一切是發生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啊,我真是忘不了這個意象,茉莉花茶叢我從來沒見過,茶我也老實告訴你,我沒什麼研究。不過這個把小女孩丟到茉莉花叢裡的故事,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忘不了,如果有天我忘記了,我真希望有人能記得。
▎致讀者
各位《永別書》的讀者,大家好:
現在您手上的當然是一本虛構小說。儘管如此,我仍舊好心提醒您,在所有情節上,如有雷同,純屬巧合。書中述及現實世界中確有其蹤的人事物,採取的是小說保存巷議雜談的傳統。此書既非考據文章,更無意代筆歷史。若想了解任何細節真相,請求教於嚴謹的研究與書籍,或是親身查證。小說在使用外文時,有時選擇將中文譯出,有時否,這是作者基於對小說樣貌的考慮,並非編輯上的遺誤。對於不能講述一個更甜美的故事,我滿懷歉意,但並無悔意。如果在此有什麼祝禱之話好說──我深深希望,相信小說,終...
目錄
致讀者
第一部|在妳的心裡有風景,還有暴風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二部|如果你看得到我的記憶,你會吃不下飯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後記
作者致謝詞
附錄一|再次相信:寫在《永別書》初版十年後
附錄二|字母會S:精神分裂
附錄三|別後通訊:在揮手的時間裡╱孫梓評.張亦絢
附錄四|情不自禁及其他:答編輯問
附錄五|圖輯
致讀者
第一部|在妳的心裡有風景,還有暴風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二部|如果你看得到我的記憶,你會吃不下飯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後記
作者致謝詞
附錄一|再次相信:寫在《永別書》初版十年後
附錄二|字母會S:精神分裂
附錄三|別後通訊:在揮手的時間裡╱孫梓評.張亦絢
附錄四|情不自禁及其他:答編輯問
附錄五|圖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