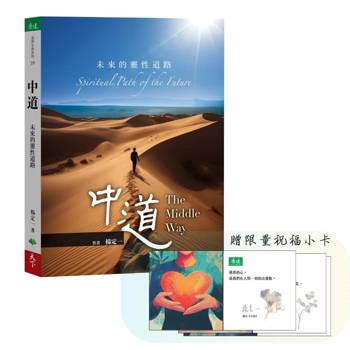|
繼克林伊斯威特x《神祕河流》
|
|
|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隔離島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隔離島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
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出生於美國麻州多徹斯特,愛爾蘭裔,現居住在波士頓。八歲便立志成為專職作家,出道前為了磨練筆鋒、攥錢維生,曾當過心理諮商師、侍者、代客停車小弟、禮車司機、卡車司機、書店門市人員等,以支持他邁向作家之路的心願。
一九九四年以小說《戰前酒》出道,創造了冷硬男女私探搭檔「派崔克/安琪」系列,黑色幽默的對話與深入家庭、暴力、童年創傷的題材引起書市極大回響,五年內拿下美國推理界夏姆斯、安東尼、巴瑞、戴利斯獎等多項重要大獎,外銷二十多國版權,並以此系列寫下北美一百三十萬、全球兩百四十萬冊的銷售成績。
勒翰真正打入主流文學界,登上巔峰的經典之作是非系列作品《神祕河流》。小說受好萊塢名導克林伊斯威特青睞改拍成同名電影,獲奧斯卡六項提名,拿下最佳男主角、男配角兩項大獎,小說也因此一舉突破全球兩百五十萬冊的銷售佳績。二○○七年,好萊塢男星班艾佛列克重返編劇行列,取材勒翰的派崔克/安琪系列第四作改拍成同名電影《Gone, Baby, Gone》(中文書名:再見寶貝,再見;中文片名:失蹤人口),首週便登上北美票房第六名。小班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勒翰的作品氣氛懸疑、人物紮實,以寫實的筆法書寫城市犯罪與社會邊緣問題,是他將小說改編搬上大銀幕的主要原因,原著小說也隨之攻占紐約時報暢銷小說榜第三名。
二○一○年二月,勒翰另一部暢銷小說《隔離島》也搬上大銀幕,由馬丁史柯西斯執導、李奧納多狄卡皮歐主演,本片是兩人繼《神鬼無間》後再次攜手合作,這也是馬丁史柯西斯首次嘗試驚悚懸疑風格的影劇作品。
相關著作:《一月光哩的距離》《再見寶貝,再見》
相關著作:《雨的祈禱》《聖潔之罪》《戰前酒》《雨的祈禱》《神祕河流》《隔離島》
譯者簡介
尤傳莉
生於台中,東吳大學經濟系畢業。著有《台灣當代美術大系:政治.權力》,譯有《殺人排行榜》、《伺機下手的賊》、《繁花將盡》、《達文西密碼》、《圖書館的故事》、《逮捕耶穌》、《誰在看你的部落格》、《騙子的遊戲》等多種。現為專職譯者。
丹尼斯.勒翰Dennis Lehane
一九六五年八月四日出生於美國麻州多徹斯特,愛爾蘭裔,現居住在波士頓。八歲便立志成為專職作家,出道前為了磨練筆鋒、攥錢維生,曾當過心理諮商師、侍者、代客停車小弟、禮車司機、卡車司機、書店門市人員等,以支持他邁向作家之路的心願。
一九九四年以小說《戰前酒》出道,創造了冷硬男女私探搭檔「派崔克/安琪」系列,黑色幽默的對話與深入家庭、暴力、童年創傷的題材引起書市極大回響,五年內拿下美國推理界夏姆斯、安東尼、巴瑞、戴利斯獎等多項重要大獎,外銷二十多國版權,並以此系列寫下北美一百三十萬、全球兩百四十萬冊的銷售成績。
勒翰真正打入主流文學界,登上巔峰的經典之作是非系列作品《神祕河流》。小說受好萊塢名導克林伊斯威特青睞改拍成同名電影,獲奧斯卡六項提名,拿下最佳男主角、男配角兩項大獎,小說也因此一舉突破全球兩百五十萬冊的銷售佳績。二○○七年,好萊塢男星班艾佛列克重返編劇行列,取材勒翰的派崔克/安琪系列第四作改拍成同名電影《Gone, Baby, Gone》(中文書名:再見寶貝,再見;中文片名:失蹤人口),首週便登上北美票房第六名。小班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勒翰的作品氣氛懸疑、人物紮實,以寫實的筆法書寫城市犯罪與社會邊緣問題,是他將小說改編搬上大銀幕的主要原因,原著小說也隨之攻占紐約時報暢銷小說榜第三名。
二○一○年二月,勒翰另一部暢銷小說《隔離島》也搬上大銀幕,由馬丁史柯西斯執導、李奧納多狄卡皮歐主演,本片是兩人繼《神鬼無間》後再次攜手合作,這也是馬丁史柯西斯首次嘗試驚悚懸疑風格的影劇作品。
相關著作:《一月光哩的距離》《再見寶貝,再見》
相關著作:《雨的祈禱》《聖潔之罪》《戰前酒》《雨的祈禱》《神祕河流》《隔離島》
譯者簡介
尤傳莉
生於台中,東吳大學經濟系畢業。著有《台灣當代美術大系:政治.權力》,譯有《殺人排行榜》、《伺機下手的賊》、《繁花將盡》、《達文西密碼》、《圖書館的故事》、《逮捕耶穌》、《誰在看你的部落格》、《騙子的遊戲》等多種。現為專職譯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