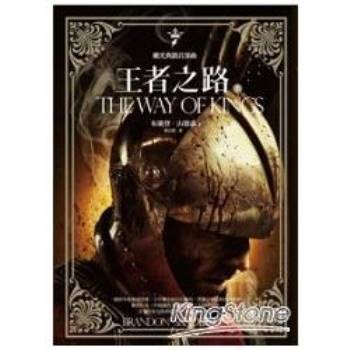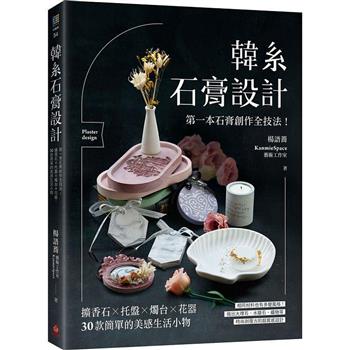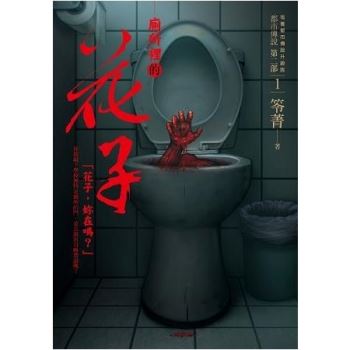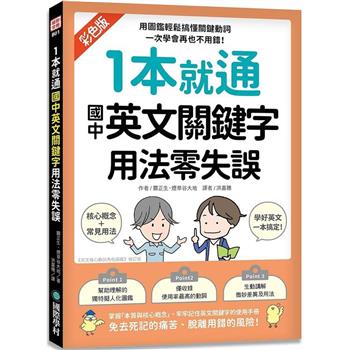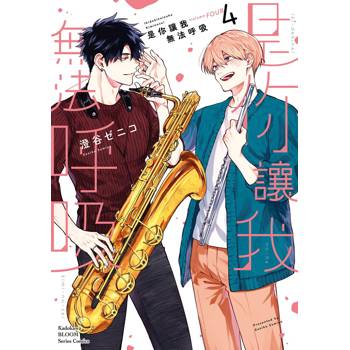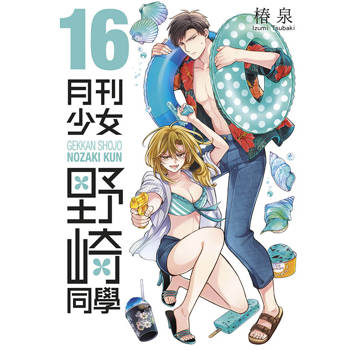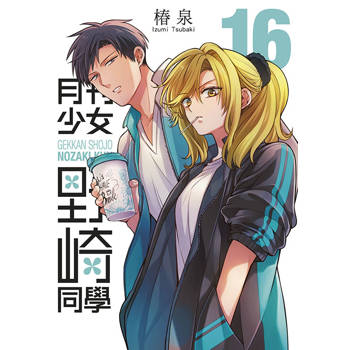「這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數學書」
2021年美國數學協會歐拉數學著作獎(Euler Book Prize)獲獎作品
――――――
2021年美國數學協會歐拉數學著作獎(Euler Book Prize)獲獎作品
――――――
★美國數學協會首位華裔主席最動人之作,在數學裡實現不一樣的自己!
★個人反思、寓言與謎題交織,深入探索數學與生而為人的深刻連結!
★用故事切入,從解謎探索,翻轉僵固型思維!
★Amazon 4.7顆星、Goodreads 4.4顆星,讚譽不斷!
▌好評圓滿推薦
王夏聲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
任維勇 ∣ 北一女中數學老師
李信昌 ∣ 數學網站「昌爸工作坊」站長
李政憲 ∣ 林口國中教師、教育部師鐸獎得主、「藝數摺學」臉書公開社團創辦人
林信安 ∣ 建中數學科教師
洪士薰 ∣ 台南女中數學教師
洪雪芬 ∣ 超腦麥斯創意思維數學課程總監
翁秉仁 ∣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高敏慧 ∣ 臺北市民生國中校長、臺北市數學輔導小組副召集人
康明昌 ∣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名譽教授、前國立臺灣大學理學院院長
許德田 ∣ 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數學領域召集人、新店國小校長
陳國璋 ∣ 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與通識中心教授
單維彰 ∣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與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賴以威 ∣ 臺師大電機系副教授、數感實驗室共同創辦人
蘇恭弘 ∣ 臺南市創思與教學研發中心專任研究教師
我們不是數學機器。
我們活著,我們呼吸,我們體會。我們是具有形體的人類。
如果數學沒有連結到人類的某種渴望,不管是遊戲、追尋真理、追求美、尋找意義或是為正義而戰,為什麼還有人要學數學呢?
這本書不談數學多麼偉大,儘管數學確實是輝煌的志業。
這本書也不特別關注數學可以做什麼,儘管不可否認數學可以做很多事情。
這本書要讓數學建立在生而為人、活出更圓滿人生的基礎上。
對數學家蘇宇瑞來說,沒有數學喜好的社會,就像沒有音樂會、公園或博物館的城市。錯過了數學,就是生活中沒有領略過一些最美麗的觀念。
蘇宇瑞小時候接受填鴨教育,大學時代被視為「沒數學天分」而放棄。但他後來不但成為數學家,還擔任美國數學協會主席。他揭露數學不是一種天才,而是一種探索的美德。
這本博大精深的著作是為廣大讀者而寫的,尤其是為那些因過往經驗而不抱幻想的人所寫。在書中,這位屢獲殊榮的數學家暨教育工作者編寫出寓言故事、謎題及個人省思,告訴大家數學如何滿足人類的基本渴望,如何培養讓人圓滿幸福的重要德行。這些渴望和德行,以及書裡講述的故事,都透露了數學與生而為人的密切關係。
有些教訓來自那些曾經奮力搏鬥過的人,包括克里斯多福・傑克森,這位關在美國聯邦監獄裡的囚犯發現了數學。克里斯多福寫給作者的信貫穿全書,顯示了這種知識活動能夠且必須向所有人開放的方式。
數學讓我們看到人類的潛能,它所揭露的事物可能面貌遠比眼前看起來更多。
▌教授與囚徒,做數學的藝術與圓滿人生的練習
■ 第1堂課:圓滿幸福
為什麼要做數學?答案是:數學可以助人圓滿幸福。適當地做數學可培養出助人圓滿幸福的德行,而且可能是以一種與眾不同的方式培養出來。
故事:你不具備成為有成就的數學家的條件「囚犯與教授」
謎題:切布朗尼蛋糕、切換電燈開關
■ 第2堂課:探索
做數學的核心意義是探索和理解。探索會培養想像力的德行,設想新的可能性。探索培養你對魔力的期待,感受發現意外事物的刺激感。
故事:井字遊戲的策略思維「偷策略論證」
謎題:「整除」數獨
■ 第3堂課:意義
尋求意義,會建立起重要的德行。首先是建構故事的德行,其次是抽象思考,另外還有鍥而不舍和深思熟慮的德行。數學是模式的科學,也是銜接這些模式的意義的藝術。
故事:畢氏定理的啟示「困在高架橋下的卡車」
謎題:紅黑撲克牌魔術、水與葡萄酒
■ 第4堂課:遊戲
數學把心智變成它的遊樂場,好好做數學就是在玩某種遊戲:探索模式,然後運用歸納推理。數學遊戲會建立起努力拼搏的信心,培養改變視角的能力。
故事:從魔術方塊到躲貓貓、從球類比賽到音樂和弦
謎題:幾何問題
■ 第5堂課:美
數學之美只會對有耐性的追隨者展露:感官之美,絕妙之美,洞悉之美,超凡之美。追求任何一種美,都會在我們身上培養出深思熟慮、喜樂與感恩和超凡敬畏的德行。
故事:碎形、歐拉公式與雪梨歌劇院
謎題:棋盤問題
■ 第6堂課:永恆
永恆是全人類的渴望,數學探險家喜歡常數,尋找不變量。我們之所以追尋永恆,是因為永恆是個慰藉,是衡量人生歷練的準繩,也是我們可以信賴的立足點。
故事:法蘭絨襯衫與「我慢」的哲學
謎題:鞋帶鐘
■ 第7堂課:真理
求真是人的基本渴望,對於深入了解與深究數學真理的追尋,可培養出許多生活領域的德行:獨立思考、嚴謹思考、審慎、面對知識時保有謙遜、認錯。
故事:謊言與真相
謎題:魏克禮拍賣(次價密封投標拍賣)
■ 第8堂課:努力
追求成長的努力是數學閱歷中最吸引人之處。主動解決問題、不斷試驗各種策略、樂意冒險,這種纏鬥會培養沉著的品格,獲得解決新問題的能力,建立自信,達到嫻熟。
故事:論文作弊的誘惑
謎題:五連塊數獨
■ 第9堂課:力量
數學力量強大:解釋的力量、定義的力量、抽象化的力量、視覺化的力量、想像的力量、制定策略的力量、建構模型的力量、多重表徵的力量、推廣的力量、結構辨識的力量。
故事:撲克牌的數學實踐
謎題:權力指標
■ 第10堂課:正義
尋求正義可以成為學習數學的動機,替數學裡的弱勢者矯正存在於數學學習空間的不公不義。在數學上追求正義的人,會培養出以同理心對待邊緣化群體、關切受壓迫者的德行。
故事:數學世界的歧視與偏見
謎題:分租協調
■ 第11堂課:自由
知識的自由產生出機敏的德行,探索的自由讓我們大膽發問與獨立思考,理解的自由建立對知識的自信,想像的自由促進發明創造與快樂的德行,做數學歡迎其他人也享有這些自由。
故事:自由的隱喻「海灘」
謎題:未知的多項式
■ 第12堂課:社群
渴望數學社群的人都必須培養出慇懃的德行,包括傑出的教學、優異的指導,以及傾向於肯定他人,由此發展出減少階級的合作能力,從多元的觀點獲益。
故事:階級與障礙「我不適合待在這裡」
謎題:球上的五個點
■ 第13堂課:愛
愛是所有德行的源頭和終點,它是每一種德行的核心。由於數學而愛就是在創造出樂觀的感覺,培養創造力,引發省思,培養對深奧知識和深入探討的渴望。
故事:終極問題「為什麼要做數學?」
▌對本書的讚譽
李信昌 ∣ 數學網站「昌爸工作坊」站長
亞里斯多德認為圓滿幸福的人生,必須透過德行的實踐。作者主張數學可以助人圓滿幸福,做數學可以喚醒我們追求內在善的渴望,書中舉出人類的12種渴望,包含遊戲、美麗、真理、正義、愛等等,每一種渴望的實現都會產生一些美德,都是圓滿幸福的徵象。例如,數學老師引導學生探索的渴望,探索會培養想像力的德行,激發創造力的德行,培養學生對魔力、驚奇的期待。書裡文章字字珠璣,值得讀者細細品味,或許您也會認同作者的觀點:基於人的渴望,做數學會讓您生活得更充實,體驗更美好的人格層面和心智習慣。
李政憲 ∣ 林口國中教師、教育部師鐸獎得主、「藝數摺學」臉書公開社團創辦人
「學數學要做什麼?」
「沒有數學我也可以過得很好啊!」
如果你有這樣的想法,這本書你一定不能錯過;這是一本有數學的標題與內涵,卻看不到什麼複雜數學公式的好書。
如果你喜歡數學,不妨挑戰一下這本書每個單元後面附的解謎、遊戲或魔術,附錄先給提示再給答案的設計,讓你不會一下子得到答案,循序式的解題。如果你不怎麼喜歡數學,建議看看書裡面有關於數學跟我們生活與問題解決的介紹,你會發現有時候不是數學沒用,只是你不知道怎麼去用它。
你熱衷於數學探索嗎?還是想看看數學中的美有哪些種類?或者你常常處於努力後得不到成就的沮喪,甚至覺得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平,不妨從標題裡找到你最有興趣的單元先看起吧!相信你對數學的看法會有所改善,將可得到更多正向面對它的能量。
林信安 ∣ 建中數學科教師
每次對初次見面的人介紹我是數學老師,接下來對方總會說:自己數學不好!
雖然日常生活中我們都離不開數學,然而大部分的人都會認為數學不是他的強項,甚至會認為自己的數學糟透了。如果你也有這樣的想法,嘗試讀這本書吧。作者會帶你遊歷數學不同的風貌,思索數學如何對我們的人生產生意義,透過許多例子讓讀者了解數學不只是課堂中定理、定義與解題的學習而已,像文中作者透過一個囚犯自學數學的信件,貫穿整本書的章節,讓讀者體驗雖然身體沒有自由,不過心靈的成長學習是不會受限。我想對於許多畏懼數學的人來說會有激勵的效果,我覺得這是很棒的內容。另外書中在每章後面都會附上一篇有趣的數學小品文,還會附上參考資料與網站。內容是關於遊戲、魔術、謎題、拍賣方式、權力分配、分租房間的公平性等等,呈現數學在各種領域扮演的角色,這些文章都很吸引人,讓我覺得讀起來很有趣。此外對於身為數學教學第一線的工作者,本書提供了數學對於增進人生圓滿幸福與激勵學生學習數學的指引,這是閱讀完這本書之後,另外一個印象深刻的收穫。
洪士薰 ∣ 台南女中數學教師
這是一本很不一樣的數學科普書籍,值得細細品味咀嚼。作者的生活背景經驗造就了關於正義丶自由丶社群等等,有意識的生命都會面對的問題。書中的一些篇章往往會觸及讀者內心的情感。原來,數學不只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另外,分散在書中各章節的數學問題都是經典而有趣的。
洪雪芬 ∣ 超腦麥斯創意思維數學課程總監
作者語重心長地說,幾十年來不斷有人呼籲要改變數學的教學法,然而變革一直很緩慢,以致學生無法體會數學是可以探索的迷人領域。
其實,透過創新的教材和學習方法,可激發學生內心對數學探索的渴望;透過實物操作數形觀察,可體驗數學的感官之美;透過數學遊戲謎題的祕訣探討,可讓學生驚嘆數學的絕妙之美;透過不同視角的邏輯推導與猜想論證,可感受數學的洞悉之美。
甚至,在享受學習數學的過程中,也會培養出深思熟慮、鍥而不舍、獨立思考、改變視角、好奇、審慎、沉著、自信、謙卑等美德。
這是一本很特別的談論數學的書,值得您細細品味。
翁秉仁 ∣ 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蘇宇瑞的美國數學協會主席卸任演講〈數學與你的幸福〉被形容為「深刻、寬廣、難以言表……許多聽眾眼眶含著眼淚,包括蘇自己」。這篇演說曾翻譯刊登在《數理人文》,如今蘇以更多篇幅細訴他的終極關懷,我當時的編輯感言也適用在這本妥善翻譯的譯本:「這裡的幸福,是意義深刻的eudaimonia,這是亞里士多德倫理學裡的善中之善,是德行實踐的最終目標。但是蘇宇瑞給的不是哲學演說,也不是由上到下的演繹論證,他信手捻來的各種案例,讓你領會數學與幸福的議題就在我們身邊。蘇是美國數學協會第一位有色人種主席,長年關懷數學教育如何走出因性別、種族、背景而蔓生的困境。數學研究雖有其菁英性,卻不應以背景來劃分。數學教師的任務是化解虛假高牆的行動,而不是反過來鞏固它的漠然。文中的例證和訊息都令人動容。」
高敏慧 ∣ 臺北市民生國中校長、臺北市數學輔導小組副召集人
《生而為人的13堂數學課》對數學的深入剖析,讓數學不僅僅是計算、解題,更是與圓滿人生連結。
陳國璋 ∣ 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與通識中心教授
生而為人,我們有一些共同的、也是最基本的心靈渴望,例如追求幸福、知識、真理、美、人生意義、正義、自由、社會認同、愛……。作者以這些最基本的心靈渴望為主軸,串聯許多數學的小故事,講述這些成就心靈追求的大道理。貫穿全書的核心人物,不是讓人感到遙不可及的大數學家,而是在社會邊緣掙扎的受刑人克里斯多福,以及曾經因為哥哥的數學天才而感到被忽視、甚至懷疑自我,心中默默吶喊渴望認同的哲學家西蒙。當然,還有曾經在求學道路上挫折的作者本人。數學對他們生命的積極影響,是許多躊躇於人生道路者的明鏡。本書平易近人、文理俱惬,既有富饒趣味的數學遊戲,亦有充滿生命關懷的數學思考,譯本忠於原著,精準而專業,值得大力推薦!
單維彰 ∣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與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人文者,人之所作。故人文不限於道德文章戲曲圖畫,舉凡數學與一切分科之學皆為人文。社會挑選一部分人文化成文化,華人社會還沒將數學化入文化。蘇教授這本書肯定名列人文之林,更希望它能潤化眾人的心,幫助數學化入我們的文化。
賴以威 ∣ 臺師大電機系副教授、數感實驗室共同創辦人
這是一本感性的數學科普書,作者不急於推銷各種數學知識的實用或趣味性(僅供它們真實存在),而是透過他或他人的生活經歷出發,讓我們看見數學在知識面之外,它還可以作為一種思考方式、一門藝術、能夠帶給我們生活喜悅,讓我們獲得一直在追求的――更圓滿的人生。
蘇恭弘 ∣ 臺南市創思與教學研發中心專任研究教師
――不像數學書的數學書
本書是獨特的,它是以人為底蘊、數學為媒介、生命為依歸的一本書。
介紹數學的書,有的以知識為脈絡,所以會生硬;有的以故事為經緯,或許顯得牽強,但本書透由每個人心中都有的構念,例如「圓滿幸福」、「探索」、「意義」……等,讓讀者有共鳴,進而接受作者對於做「數學」的終極目的。
另一個特別之處,本書內容也像是迷惘時的解籤書或是心靈雞湯,作者配合文中主題安排的名言佳句,總會讓讀者有醍醐灌頂的豁然開朗。「如果我們沒有幾何的天分或喜好,並不代表我們不能靠思索問題或研究定理培養出專注力。相反的,這幾乎是一種優勢。」您瞧,是不是對孩子很受用!
它的確是本數學書,因為每一個章節末都有一些有趣的數學謎題,挑戰您解決問題的能力,而做「數學」到底有什麼用?以前這個答案很難回答,不過閱讀完本書13 堂數學課後,您會說:「所有的努力都是為了『圓滿幸福』。」
因為「數學之美只會對更有耐性的追隨者展露出來」。
保羅・坎貝爾(Paul J. Campbell) ∣ 《數學雜誌》(Mathematics Magazine)
鼓舞人心之作⋯⋯寫給想知道數學在何處及如何融入生活的所有人。
鄭樂雋(Eugenia Cheng) ∣ 《邏輯的藝術》(The Art of Logic in an Illogical World)作者
如果你關心數學、社會正義或人,請讀這本優美、扣人心弦、激勵人心的著作,我也希望每個人都這麼做。
約翰・庫克(John Cook) ∣ 奇異值顧問公司(Singular Value Consulting)
哲學、數學插畫與惻隱之心的悅人混合體。
凱文・哈奈特(Kevin Hartnett) ∣《量子雜誌》(Quanta Magazine)
古希臘人認為,最美好的生活應充滿美、真理、正義、遊戲和愛。數學家蘇宇瑞知道可去哪裡找到這些事物。
娜里妮・賈許(Nalini Joshi) ∣ 雪梨大學
這本超越群倫的書令我入迷。原創的見解和迷人的謎題讓我再次覺得年輕,發現了通往禪與數學藝術之道。
班・歐林(Ben Orlin) ∣ 《塗鴉學數學》(Math with Bad Drawings)作者
蘇宇瑞相信數學可讓我們成為更好的人――他也以身作則。每一頁都是慷慨與惻隱之心的結晶。還有,書裡的謎題會在你腦海中縈繞好幾週。
愛德華・謝納曼(Edward Scheinerman) ∣ 《數學愛好者的同伴》(The Mathematics Lover’s Companion)作者
對數學與人類精神的頌揚。學習數學可以豐富人生,蘇宇瑞希望每個人都是這場宴席的座上賓。
詹姆斯・坦頓(James Tanton) ∣ 全球數學計畫(Global Math Project)
這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數學書。蘇宇瑞說明了數學是心智的體驗,最重要的是,是內心的體驗。
約翰・烏舒爾(John Urschel) ∣ 《心與物》(Mind and Matter)作者
蘇宇瑞寫下了探討數學之美及它與共通人性如何產生連結的抒情之作。
塔莉西亞・威廉斯(Talithia Williams) ∣ 《數字的力量》(Power in Numbers)作者
蘇宇瑞優雅揭露數學的美與力量,因為數學攸關我們想被人愛、信任、接受的渴望。這本書是對數學之美的有力敘述,是矯正數學僵固型思維的良方。
Eddie Woo ∣ 《喚醒大腦裡的數學家》(Woo’s Wonderful World of Maths)作者
世人對於數學是什麼,為何重要,極需要這種全面又深刻的人性化觀點。數學思維發展出來的重要素質,是我們大家應該重視並渴望的特質。
《美國數學月刊》(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這是攸關我們這個時代的信念和著作⋯⋯對那些不太相信這些理念對學業成績和人類都很重要的人來說,這本書是必讀之作。
《美國數學協會書評》(MAA Reviews)
好書讀起來有趣。很棒的書像一面鏡子,讓我們把自己和所生活的世界看得更清楚。蘇宇瑞的這本書既是好書,也是很棒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