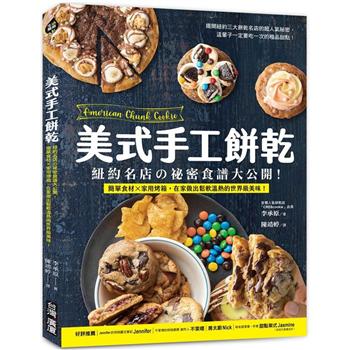愛倫坡獎終身大師獎得主卜洛克給台灣讀者的短信──
「追記我踏入文壇之初的回憶錄,A WRITER PREPARES,從某些角度來看,是我最私密的作品。希望你們會喜歡。」
熟悉卜洛克的讀者都知道,有兩件事情,他不大願意提及:一是他一度酗酒成癮,那時的掙扎,投射在他筆下最動人的主角,馬修.史卡德身上;二是剛出道時大量製造的通俗作品,以筆名發表,是他不會否認,但也拒絕承認的起步,其中包括了好些他遊走在法律邊緣的情色小說。
好幾次,他想要回顧這段歲月,但終究沒有完篇,直到他來到年紀「輕得還有記憶,卻老到並不在乎」的現在。他終於寫下史卡德走進酒店前,他在創作歷程初期的嘗試、挫折與探索。
這是一本寫給卜洛克老朋友的生涯前傳。細心的讀者可以驚喜的發現他的風格與系列主角成形的線索。殺手凱勒為什麼會有這麼豐富的集郵知識?譚納為什麼會睡不著覺?卜洛克是哪來的突發奇想?
當然,還有帶著濃濃醉意的馬修.史卡德。
如今的卜洛克看來比以前更能正視自己的過往,除了詳列早期以筆名發表的作品,甚至計畫重新發行之外,更揭露了他如何以及為何沉醉於酒精,難以自拔的起因。行文中,他有意無意的點到他參加過AA的活動。他跟馬修一樣,「只聽就好」嗎?
這本書對於卜洛克的書迷而言,充滿了解謎的趣味。更好奇的讀者可以找到史卡德系列的初期,為什麼篇幅都偏短的原因以及他對於紐約的情感,甚至迷戀。
這本書嚴格說起來,有兩個作者、兩個卜洛克。一個是一九九四年的中年卜洛克,那時的他,完成了這本書的前五萬字,從他的幼年啟蒙,大致寫到他靠撰寫情色小說,闖出名號為止。另外一個作者是二〇二〇年的卜洛克,記憶變得模糊,但是心境更加平和、態度更加成熟,而且說不定,還更有智慧呢。
老卜洛克補充了後續的發展,埋下了他即將開始創作史卡德系列的伏筆,同時也記下了新冠疫情對於紐約生活的衝擊,還有跟他跟琳的因應之道。他說,除了他的書迷之外,這本自傳對於想要成為作家的人,多少會有點啟發。如果這本自傳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前就問世,或許不會這樣包容、這樣坦誠、這樣深情。文末,卜洛克還收錄了他在五十二歲寫下對父親的追思與一個至今無法解開的謎團。
二〇二〇年,卜洛克終於續完了他的前傳,在序文中請讀者先讀一九九四年、五十五歲他的寫好的五萬字,「且看這段過往能把我們引領到哪裡去」,讀這本卜洛克的自傳的心情,可能亦復如此,深愛他的讀者,大概也想知道在他打造的迷人情境裡,他年輕時的經歷,會引領我們到哪裡去?
名家齊聲推薦
冬 陽 推理評論人
李屏瑤 作家
李桐豪 作家
房慧真 作家
臥 斧 文字工作者
崔舜華 作家
張國立 作家
陳正菁 浮光、春秋書店主理人
陳國偉 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所優聘副教授暨所長
陳 雪 小說家
陳祺勳 個人意見
傅月庵 資深編輯人,作家
黃宗潔 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楊士範 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內容長
楊富閔 小說家
劉梓潔 作家、編劇
盧建彰 導演、作家
譚光磊 國際版權經紀人
蘇洋徵 獨立編導
這是一本「卜迷限定」之作。我無法推薦給不認識甚至不熱愛勞倫斯.卜洛克的非特定讀者一讀,因為那毫無「解謎」的樂趣、缺乏閱讀的「動機」,這些在犯罪推理類型底下是極為重要的。也因此,我不覺得閱讀這本《酒店開門之前︰卜洛克的作家養成記》是一種刺探窺視,而是好好理解令我喜愛的故事是如何從豐饒的真實生命化為精采的虛構情節,再次溫習那一本本迷人的書冊,享受其中的美好。(推理評論人 冬陽)
他出生於1938年,一輩子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寫作。不用問寫了多少本?也無需問得過多少獎?又聽到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這名字,就足夠讓人驚喜:「居然還有新書!?」——過了這個村,就沒那個店,看一本少一本的老卜之作,非讀不可!(資深編輯人、作家 傅月庵)
知名作家撰寫回憶錄並不是罕見的事,但是如《酒店開門之前》這樣的回憶錄形式,卻相當罕見。用卜洛克自己的話形容,是「三個不甚牢靠的敘事者,組成的三頭馬車」——八十一歲的他,介紹五十五歲的自己寫下的,二十來歲的回憶。而這特殊的結構,讓本書完美地符合了他心中撰寫回憶錄的合適年齡:「輕到還記得,老到不在乎」。五十五歲的他夠年輕,還記得往事;八十一歲的他夠老,老到足以面對回憶。
老實說,如果你從未讀過卜洛克,這未必是一本合適的入門書,因為它更接近某種「補完」、某種「番外篇」;但如果你已經是他的小說讀者,這絕對是一本幫助你更接近「前‧馬修史卡德年代」的作品,儘管它拆解的並非這位偵探的心路歷程或創作脈絡,而是卜洛克年輕時代,在代筆與情色小說產業一路走來的人生軌跡。它是來自過往歲月的回聲,是凝視深淵浮現的倒影。面對盛年時未必很想談論的過往,這是他用時間凝練出的,對回望的回望。(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黃宗潔)
做一個卜洛克書迷超過20年的讀者,當收到詢問是否願意幫最新一本卜洛克將個人出版的生涯前傳推薦,我幾乎是想都不想的就點頭答應。而讀完此書,我相信我腦中混亂的程度不比看完近日熱映的電影《媽的多重宇宙》。我一直知道卜洛克生涯早期寫過一些情色文學(小說),但我還真的不知道原來他不是寫過一些,而是幾乎寫了快10年相關的小說。當然,台灣這邊我想應該不會有機會翻譯,就算有緣看到英文原版我也不確定是否看得完。但對於一個「卜粉」來說,光是多知道這個軼事也就足夠了。卜洛克前一本小說《死亡藍調》我印象中讀者評價並不高,在Amazon上也看到一些不甚滿意的評論,但我自己卻讀得挺開心,倒不是說只要掛上他的名字的書我都喜愛,而是我自覺讀了一個有趣的故事,對我來說,這也是很多時候我讀小說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或許這本生涯前傳有些混亂、有些遙遠,但能一窺「酒店開門之前」發生了什麼事,看見60年前卜洛克還超級年輕、真正「年少輕狂」時的往事,遙想60年前的紐約和作者/編輯在做的事情,我真的非常心滿意足。(關鍵評論網媒體集團內容長 楊士範)
作者簡介: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
歐美當代冷硬派偵探小說書寫第一人
一九三八年出生於紐約水牛城。除了極少時間之外,卜洛克幾乎都定居於紐約市內,並以該城為主要背景,從事推理文學創作,成為全球知名推理小說家,因而獲得「紐約犯罪風景的行吟詩人」美譽。
卜洛克的推理寫作,從「冷硬派」出發而予人以人性溫暖;屬「類型書寫」卻不拘一格,常見出格筆路。他的文思敏捷又勤於筆耕,自一九五七年正式出道以來,已出版超過五十本小說,並寫出短篇小說逾百。遂將漢密特、錢徳勒所締建的美國犯罪小說傳統,推向另一個引人矚目的高度。卜洛克一生獲獎無數。他曾七度榮獲愛倫坡獎、十次夏姆斯獎、四次安東尼獎、兩次馬爾他之鷹獎、二○○四年英國犯罪作家協會鑽石匕首獎,以及法、德、日等國所頒發推理大獎。二○○二年,繼一九九四年愛倫坡獎當局頒發終身大師獎之後,他也獲得夏姆斯終身成就獎。二○○五年,知名線上雜誌《Mystery Ink》警察獎(Gumshoe Award)同樣以「終身成就獎」表彰他對犯罪推理小說的貢獻。
相關著作:《在死亡之中》《死亡藍調》《聚散有時》《蝙蝠俠的幫手(增訂新版)》《烈酒一滴》《繁花將盡》《死亡的渴望》《每個人都死了》《向邪惡追索》《一長串的死者》《惡魔預知死亡》《行過死蔭之地【《鐵血神探》電影原著小說】》《屠宰場之舞》《到墳場的車票》《刀鋒之先》《黑名單》《八百萬種死法》《酒店關門之後》《謀殺與創造之時》《黑暗之刺》《在死亡之中》《父之罪》《八百萬種死法》
譯者簡介:
劉麗真
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資深編輯工作者。譯有《死亡的渴望》《奪命旅人》《譚納的非常泰冒險》《小城》《搭下一班巴士離開》《聚散有時》《死亡藍調》《卜洛克的小說學堂》《改變歷史的聲音》等書。
章節試閱
十五歲,剛上高中一年級的我,就知道我想當作家。這個想法是怎麼冒出來的,我記得一清二楚。
我的英文老師是玫.傑普森(May Jepson)小姐。她出了很多作文功課,對我很好。寫作,素來難不倒我。有一次,老師要我們寫足兩頁,說明自己的生涯計畫。我知道我會上大學,這是家裡的規矩,但畢業之後要幹什麼,卻沒有清楚的概念。我父親是律師,但這些年來卻只零星執業過幾次而已;其他時間,他投資酒店、銷售保險、開了一間玩具店、參與開發計畫,蓋了幾棟房子,還從事好些自認會發財的事業,幾乎全部鎩羽而歸。我一點都不想尾隨他的腳步。他曾經希望我能當個醫生,但我不認為自己對行醫有絲毫的興趣。我不知道我能幹什麼,在作文中流露出徬徨,列舉了我很小很小的時候,見識過的幾種職業。我一度想要當清潔隊員,直到我媽說,做那行手掌很容易皸裂,這才作罷。
通篇作文行筆輕快。我還記得結尾。「讀過這篇作文,」我寫道,「有件事情倒是很清楚——我絕對當不了作家。」
傑普森小姐給我A。更重要的是她寫的眉批,就在我結尾最後一句的旁邊,她寫道,「我可沒這麼確定。」
讀了她的評語,我立定決心,我要當作家。
我已經得到某些證據:我或許稱不上才華洋溢,但對於文字的運用,相當得心應手。八年級,校方要求我們參加由《水牛城晚報》(Buffalo Evening News)與美國退伍軍人協會聯合主辦的徵文活動。那年的主題是:「什麼是美國主義?」艾利郡的所有學校都必須要投稿。最後,從普通高中、重點學校湧進的徵文,分成三類:城區、郊區、教區,決選出最後的十二篇優勝作品,而我的作品正是其中之一。
我已經不記得我寫些什麼了。想來跟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的牧師反對罪惡一樣,我肯定擁護美國主義。有關內容,只記得這麼多了。交稿前,媽媽幫我看了一遍,做了一兩個小修正,這裡、那裡潤色一下。我的英文老師,詹森女士,選了兩篇:一篇是我的,另外一篇的作者是代表第六十六公立學校的羅蘭.琥珀(Lorrain Huber)。她沒動內容,卻對筆名有點意見。
沒錯,筆名。所有的文章必須用假名進入評審程序,不能讓評審認出某某投稿者是朋友的孩子、是出自主流或是少數族裔,以免偏見作祟,影響最終結果。
所以,我必須想好我第一個筆名。為了符合這次徵文的精神,我決定從三任總統的名字中,各取一個,組成盧瑟福特.戴蘭諾.昆西(Rutherford Delano Quincy)做為筆名。這名字來自盧瑟福德.伯查德.海斯(Rutherford Birchard Hayes)、佛蘭克林.戴蘭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與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
(我依舊記得歷任美國總統的名字,以前可以——如今還是可以——按照順序背出來。但我不是靠死記,而是因為我蒐集郵票,當時流通市面的常用郵票,就是以總統的頭相為主題,面額對應任職順序。比方說,第十九任總統,盧瑟福特.戴蘭諾.昆西,面額就是一毛九分;約翰.昆西.亞當斯印在六分錢的郵票上。總統系列在一九三八年發行,並不包括羅斯福總統。當時他還在世,是現任總統。活人不能出現在美國郵票上,唯一的例外是貓王〔Elvis Presley〕。)
所以,我給自己取的筆名就是盧瑟福特.戴蘭諾.昆西;但詹森老師另有盤算。盧瑟福特這個字太長了,直接縮成福特就好;戴蘭諾可能冒犯崇拜羅斯福的死忠分子,被她改成了戴蘭尼,昆西她沒有意見。
福特.戴蘭尼.昆西。第一眼覺得很蠢;但詹森老師也許真的是見多識廣。那一年,神來一筆,我贏了,更厲害的是,羅蘭.琥珀也榜上有名。
史無前例。我不知道當時水牛城有多少公立重點學校,算算少說八十來個。詹森老師堪稱是綜合中學界的麥斯威爾.柏金斯(Maxwell Perkins,譯註:美國出版界的傳奇人物,他曾經是海明威、費茲傑羅的編輯),羅蘭跟我的文章都登在報紙上,跟其他十名獲獎者一起到華府歡度耶誕節假期。
你可能以為成功的經驗,讓我興起不妨以寫作為生的念頭。研究一下投報率:兩百字的文章讓我出了一回鋒頭跟旅遊招待;日後,我寫更多,回報卻更少。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當時的我並沒有這些算計。我根本不曾意識到一般人所謂的「寫作」。我讀書,也知道每本書都有作者。但我寫的短文並非寫作。要我交功課,我就寫好交出去。
真正把寫作這個點子,栽進我腦海裡的是傑普森小姐。我開始認真琢磨當作家的可能性。首先,我喜歡讀書,鑑賞能力比以前更精進。我在不經意間發現二十世紀的美國寫實小說,深得我心,一路讀了下去,找到什麼,就孜孜不倦的讀什麼:詹姆士.法洛(James T. Frrell)、約翰.史坦貝克(John Steinbeck)、厄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埃爾斯金.柯德威爾、約翰.奧哈拉(John O’Hara)、湯瑪士.沃爾夫(Thomas Wolfe)。大多數的作品掠過我的腦海,有些卻是船過水無痕,但我覺得這些小說實在是非常的寫實。
當作家?我想這是一個很不賴的想法。就連傑普森小姐都覺得我有這個能耐。那麼,何妨一試?
所以,我拿定主意,只要有人問我大學畢業之後要幹什麼?我一律回答當作家。好些人就此以為我想去報社上班,的確,在畢業紀念冊上,我的生涯規畫寫的是「新聞業」來掩人耳目。但我心裡清楚,我並不想幹這行。幹嘛糾纏陌生人,問一些跟我沒關的問題?我怎麼可能做這些?又為了什麼要做這些?
不,我知道我要幹什麼。我可以寫詩、寫短篇、長篇小說,一定可以印行。大家愛不釋手,由衷欽佩我的偉大。
從這個時間點起,我寫出來的文字,絕大部分就是要讓人歡喜讚嘆。
我決定從傑普森小姐開始。已經有證據顯示,她傾向支持我的決定。我打點精神寫好每一篇作文,不管是詩,還是其他的形式,只要落筆,絕不掉以輕心。韻文,信手拈來,並不費力,一度懷疑是我與生俱來的專長。我的母親也喜歡吟詩作對,沒什麼天賦,只是在致贈生日或者新婚禮物的場合上,謅上幾句。舉個例子,我表姊菲—安.李普曼(Fay-Anne Lippman)嫁給了菲利浦.柏尼斯(Philip Bernis)。她準備一套特百惠(Tupperware,譯註:風行美國的塑膠食物容器品牌)慶賀,還在流理台邊,朗誦這首小詩:
他們說要開車送你回家
禮物裡少了首詩怎麼像話?
搜索枯腸絞盡腦汁,只能作罷
輕巧實用,心意滿滿,才是無價。
「曼」慢地以「菲」常有愛的方式裝滿它
俗話不也這麼講?哪壺不開就別提哪壺
至少你們彼此還有容器可以填補
或者,你寧可稱之為快樂廚房
在這裡你們彼此的情緒可以安心釋放
我當然不能說這首打油詩會讓奧格登.納許(Ogden Nash,譯註:美國的大詩人)嫉妒到椎心刺骨;但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這首詩的「格律」不算差,韻腳押得工穩,別提哪壺與填補這兩個收尾也頗出色。(廚房與釋放差了一點點,但我們經常掛在嘴上,對民歌而言,這麼點誤差實在算不了什麼。Home跟Poem在水牛城是押韻的,相信我。)
到了第二年,我媽還把開場第一聯掛在嘴上,複述個十來次,樂此不疲。雖說她從來沒想要以賣文為生,卻展現相當專業的態度:只要常有佳作,一步一腳印,自然行穩致遠。
在高中剩下的那幾年裡,逮到機會,我就賦詩一首。在諸多兄弟會的舞會宣傳中,只有我們兄弟會的廣告,別樹一幟——幾首小詩,出自我的手筆。我幫朋友梅爾.賀威茲(Mel Hurwitz)代寫一首情詩,獻給他正在追求的女性朋友,增添約會情趣。(我收了他一塊錢,這是我靠寫作賺進來的第一筆現金。不要問我這一塊錢拿去幹什麼了。也別問我梅爾究竟追上那個女生沒有。)
高中最後一個學期,不知道誰決定舉行「年級詩作」的選拔活動。優勝作品可以刊登在我們的畢業紀念冊——《班內特燈塔》(Bennett Beacon)上,頒贈作者「年級詩人」封號,照片跟畢委會幹部放在一起。
我投了兩篇作品。第一首是是標準的抑揚五步詩格律;另外一首是印象派的自由詩。主辦單位全程保密,在決定優勝者前,評審無從知道投稿者的身分。我早就備好筆名等在那裡,福特.戴蘭尼.昆西,如果他們有需要的話。
「此處風景無限好,但我迫不及待,只想離開」的無韻詩獲選為「年級詩作」。「我知道這首詩是你寫的。」傑普森小姐偷偷告訴我。「我還認出你的另外一首。自由詩體。得到第二名。」
畢業之後,我就再也沒有看到傑普森小姐了。
我從來沒有回學校看過老師。有些老師真的很好,比方說,達莉小姐,教我三年拉丁文,影響之深,沒有任何一堂課能夠相比。雪曼小姐,一年級的西班牙文老師,很快就發現我不願意參加自習,想用每天最後一堂課的時間,做自己的事情。「現在我把你分到『西班牙文二』的非正式自修組,還是留在我班上。」她這樣跟我說——但我得在一年內,把兩年的西班牙文課程念完。
還有賴金先生,高二的歷史老師。他上課的時候喜歡在課堂上走來走去。開學沒多久,他抓到我在筆記本上塗鴉。「賴瑞,」他若無其事的說,「下課後來找我。」我去了,他叫我別在筆記本上亂畫,我說好,以後不會。第二天,我故態復萌——「賴瑞,下課後來找我。」我去了,保證這是最後一次。那週最後一堂歷史課,賴金先生臨時小考。週一早上,他把打好分數的考卷還給我,又說了一次,「賴瑞,下課後來找我。」那次我考了一百分。下課後,我去找他,他說,「賴瑞,筆記本只是協助你的工具罷了。你愛在上面塗鴉,就去塗吧。」
這個反應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沒騙你,至今難忘。賴金先生是偉大的老師,教育體系給他很豐厚的回報,直接升他為校長;只是這麼一來,後來的學生就無法在教室內,感受他的春風化雨。
我從沒回過班內特中學,或者參與六六年班聚會,也不曾見過詹森老師,或是葛林先生,他是一個妙趣橫生的人,也是很好的歷史老師。還有戈德法斯女士,五年級的導師,非常了不起;就是她說服我父母跟校方同意我跳過六年級課程,讓我在六年間都能脫離社會群體,冷眼旁觀。創作小說不可或缺的局外人觀點,難道不是來自我青少年時期的適應不良?我的家庭健全,不曾受到凌虐或者不當干擾。如果,我沒有放棄六年級的學習,說不定我的成長會更符合外界期待,當醫生、律師,或者去經商。
我再也沒見過我生命中的優秀師長,真希望我曾經探望過他們。如果真有機會,我尤其想去找傑普森老師。七○年代末期,我出版第一本談寫作的書,特別講到她給我的提攜。我想寄給她一本,但是沒人知道她的地址。她在很久以前就退休搬去加州。我想她已經過世了,只是不確定她知不知道我當上作家,知不知道我的賣文念頭,就是受到她的啟蒙。
我希望我能夠好好的謝謝她。
我在高中的時候,首度使用筆名,還看到它被印出來,於是養成每天看晚報讀者投書版的習慣,非常喜歡來函中毫不造作的幽默。在電視上,看到「霍曼名人堂」版的《馬克白》之後,為了某些原因,決定自己也寫一封抒發心聲。我痛斥節目中的暴力內容,開頭是內容摘要(「他們先是殺了國王……」),結尾疾呼(「讓我們團結在一起,淨化我們的電視節目!」)使用筆名「艾勒爾.布里克」(Allor Bryck,譯註:他把Block拆在兩邊,名字的部分l跟A互換,再把ry搬過來幾乎就是Larry了)取代勞倫斯.卜洛克。不算太高明的文字遊戲。
看到自己的文章被印出來,滿足感之強烈,至今還是覺得訝異。見報之後,引發莎士比亞捍衛者反擊,甚至為此動怒,看起來更是過癮。這麼多傻瓜把我的文字當回事,讓我受寵若驚。我不知道史帝夫.亞倫(Steve Allen,譯註:美國知名節目《今夜》的第一任主持人)有沒有把「艾勒爾.布里克」當回事。他曾經在《今夜》秀裡面讀過我的那封信,不過目的是告訴觀眾,外面的怪胎還真不少。
我真想看那集節目,但知道有這麼回事,就夠我開心的了。
幾年之後,我為作家開設研討課程,取名為「為你的生命寫作」(Write for Your Life,我誠心誠意發誓,當年真的應該取別的名字。因為聽起來,人們可能誤會我辦的是Right For Life〔生命權利〕,搞不清楚是支持還是反對墮胎。有兩家旅館拒絕我們的預約,他們說,他們不想捲進爭議裡。「爭議?」我聽到自己在尖叫。「我們只是教人寫作而已,有什麼爭議啊?」「這樣一來,我們更加確定講師沒什麼好講,學生也沒什麼好學的了。」他們這樣回答。)
我跟琳主辦的「為你的生命寫作」,目的是告訴與會者寫作的幕後遊戲(可惡!我應該取這個名字),日後發展成「最高級別」的講座。有一堂核心課程想說明我們這行業有哪些根深柢固的錯誤信念,又會對寫作帶來怎樣的負面影響。我們巡迴全國各地,必上這門課,久而久之,發現好些作家圈裡以訛傳訛的流言。其中一個誤解是:「洩漏我們的真實身分,並不安全。」
大家把這句話奉為圭臬,但渴望成名,又是驅動小說作家創作的主要動力。兩者明顯矛盾。我一路走來,覺得自己多半也是這種心態組合。
一方面,我吶喊希望自己能被看到、被聽到、被欣賞;另外一方面,我很確定:如果人們真的認識我,一定不會喜歡我。隱藏真我非常關鍵。下面這個故事就能說明我緊張到什麼程度。好些年來,我一直擔心哪天我接受手術,全身麻醉;麻醉消退之後,開口講話。講話到底是有什麼好怕的?拜託。我是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嗎?只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一開口,別人就可能察覺到真正的我。這很危險。
寫小說是完美的解決方案。「看!」我的故事會叫道,「這是我啊!但千萬不要看偏了,這並不是真正的我,只是個故事罷了。」
筆名在這過程中助益甚大。筆名,讓我能夠避開其他人可能的負面評價,賜給我無比的自在。只要別洩漏太多關於我的私事,愛怎麼下筆,都無需憂慮。絕大多數的讀者不知道作者是誰;而我的朋友心裡清楚,那只是我的遊戲文章,犯不著冠上我的真實姓名。
此外,筆名也能讓我自己扮演一個角色。小說創作,自始至終,都在演戲,心思從軀殼釋放出來,進到小說角色裡面。最後,筆名會發展出自己的人格,讓這個偽裝成作家的人,再去偽裝成某個角色;在原本就戴著面具的臉上,再加上一層面具。我有幾個筆名,被歸類成「現代作家」。其中兩個——吉兒.艾默森(Jill Emerson)與約翰.華倫.威爾斯(John Warren Wells)曾經相互奉獻作品給對方。我發現我意圖把兩人送做堆,在《時代》上面刊登一則結婚啟事。
但是時機尚未成熟。當時的我,日日夜夜都在寫小說。晚上寫的,用我的真名,寄出去賣;白天寫的,則以信件的方式呈現,筆名叫做「史考特.梅雷迪斯」。
十五歲,剛上高中一年級的我,就知道我想當作家。這個想法是怎麼冒出來的,我記得一清二楚。
我的英文老師是玫.傑普森(May Jepson)小姐。她出了很多作文功課,對我很好。寫作,素來難不倒我。有一次,老師要我們寫足兩頁,說明自己的生涯計畫。我知道我會上大學,這是家裡的規矩,但畢業之後要幹什麼,卻沒有清楚的概念。我父親是律師,但這些年來卻只零星執業過幾次而已;其他時間,他投資酒店、銷售保險、開了一間玩具店、參與開發計畫,蓋了幾棟房子,還從事好些自認會發財的事業,幾乎全部鎩羽而歸。我一點都不想尾隨他的腳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