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空的,
不代表什麼都沒有
不代表什麼都沒有
《孤獨的美食家》、《深夜食堂》、《今日的貓村小姐》松重豐
以「演員」為主題的首部創作
以「演員」為主題的首部創作
王盛弘│作家
李屏瑤│作家
李桐豪│作家
李冠潔│日文譯者
那些日劇沒有教我的事
重點就在括號裡
劉梓潔│逢甲大學人社院助理教授
龍貓大王通信│影評人
謝盈萱│演員
——曖曖內含光推薦
12篇二線演員牢騷系連作短篇
+
25篇工作札記、幕後花絮及日常生活小品
+
25篇工作札記、幕後花絮及日常生活小品
「好的刑警、壞的刑警、熱血刑警、老練刑警、溫情派刑警、智慧派刑警、行動派刑警、被打入冷宮的刑警、比流氓更流氓的暴力刑警、只負責在搜查會議上進行報告的刑警、一登場就死的刑警、跟故事沒有太大關係的刑警。
以上這些,我全部都演過。」
上半部為短篇連作小說〈愚者妄言〉,為松重豐於疫情期間拍攝空檔所作。描寫一名上了年紀又不甚知名的二線演員,一日至京都拍戲,偶遇一名歐吉桑向他開示:「佛陀與演員內在都是中空的」。自此之後,一再接演刑警、黑道、法官、醫師等眾多配角的主人公,不僅在戲內不斷搞混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連在戲外也分不清現實生活與劇中生活的界線。看似通篇抱怨與碎念,轉折處又不禁令人嘴角失守的奇想之作。
下半部〈演者戲言〉,集結松重豐連載於《SUNDAY每日》的散文小品。讓喜歡松重豐的讀者,得以一窺他出名以前的生活樣貌,以及大多圍繞著吃食的片場花絮及日常觀察。隨著蜷川幸雄的劇團遠赴海外,卻因爲太想吃壽司而誤入傳教現場;常被人問要吃什麼才能長那麼高,身為演員身高太高反而是一種困擾;私底下用餐,老闆與店員竟退至一旁,默默觀察他是否如同井之頭五郎一般,會將餐點都津津有味地吃完……
小說與散文看似各自獨立,卻又巧妙連結,讀來不禁令人嘴角失守,松重豐「掏空才得以成就」的演員之道。
國內粉絲推薦──
還在配音圈時,恩師曾經告訴我:「要提升演技,就要懂得觀察人。」松重豐筆下細膩而幽微的心境敘述顯示出他之所以能成為這樣的好演員,正是對人心觀察入微。
在囈語與現實間遊走的連作短篇集〈愚者妄言〉,寫出了所有表演人員的夢魘──就算不是表演者,誰又不曾從在台上手足無措的惡夢中醒來?而散文〈演者戲言〉一轉小說的意識流文風,樸實日常的語調就像跟松重大叔坐在桌邊閒話家常。先行連載的散文出現的元素也與後來在疫情期間創作的小說內容巧妙連結。松重豐的身分自然讓本書多了一層玩味,但就算把名字遮起來,說是出自文學界大作家之手也毫不意外的文筆,讀來依然充滿驚喜。
空洞,是為了盛裝些什麼;而曾經盛裝過的事物消失、回歸空洞,是為了容納更多新的事物。以演員的身分盛裝過這麼多的角色,松重豐的空洞,如此豐盛。
──李冠潔│日文譯者
長年的配角經歷讓寫作裡的現實諷刺、自嘲顯得充滿智慧且溫柔帶點幽默風趣,人生一場一場的戲,也可以像「孤獨的美食家」這樣,一個人平靜享受美食的時光,沉浸自我,更勝世間一切。
《空洞的內在》充滿幻想也令人反思,質樸不華的文字帶有喜感令人會心一笑,像在訴說自己一無所有也是一種價值。為了生活兢兢業業的小人物,何等平凡的煩惱卻又如此與我們的心靠近。這股笨拙直接卻無比感人,庸碌中的掙扎時刻,反而累積出小人物的奇妙高光視角。
──那些日劇沒有教我的事
「松重豐」這名字,從字面看來有飽滿厚實之感,與他身形修長外形有點反差。給人幾分靦腆感受的byplayer,文字如人謙虛,真誠的謙虛,自承演員是空洞「容器」,唯有如此,才能將五花八門的角色裝進容器,下戲再將角色取出,以便放進下一個角色。而《空洞的內在》,就是松重豐填實並飽滿內容,由他主演的紙上連續劇。
──重點就在括號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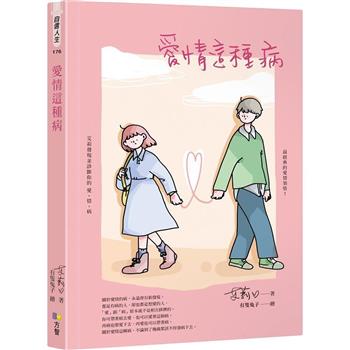




![114年數理邏輯(邏輯推理)[國民營事業] 114年數理邏輯(邏輯推理)[國民營事業]](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4100119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