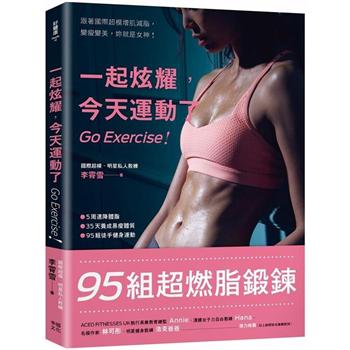美國墮胎權爭議釋憲後,最切時的女性生育自主權寓言
宛如《瘋狂麥斯:憤怒道》加上《使女的故事》
在這個世界生為女性,只有兩種人生選項──
成為母親,或是成為罪人。
除非妳蒙起面、拿起槍,
攀向絕壁上最後的自由之土……
★瑞絲‧薇斯朋、艾瑪‧羅勃茲、歐普拉等巨星讀書俱樂部精選推薦、艾美‧亞當斯製作公司簽下電視劇版權
★美國獨立書商協會、亞馬遜網路書店小說類當月選書
★空降《紐約時報》精裝圖書暢銷榜
林廷璋│私人圖書館「櫞椛文庫」館長、
馬欣│作家、
烏恩慈(烏烏醫生)、
曾彥菁│作家
畫說有一天│IG說書版主、
──好評推薦
┤故事簡介├
「若倖存者依神的形象造人並大量繁衍,將神的子民填滿世界,神將保守他們免於疫病。」
這是一個平行時空般的十九世紀美國西部,原本與我們的真實世界神似,直到一場瘟疫改變了一切──大量人口病死、政府瓦解、病癒者生殖功能受損。教會順勢崛起掌權,以小城鎮為單位重新建立秩序,但新生兒數量仍舊寥寥無幾,眾人開始怪罪於婦女,認為她們不夠溫良虔誠,才招致天罰,並且規定將不願婚嫁的女人或婚後不孕的妻子處以放逐、監禁或絞刑,墮胎和避孕更是無可饒恕的重罪。
艾妲從小跟著當助產士的媽媽學習醫術、擔任助手,拯救了眾多產婦的生命。十七歲時,她幸運地嫁給暗戀的男孩,期待能儘快生下自己的孩子,卻因為遲遲沒有受孕而遭到誣陷與審判。
在警長的同情之下,艾妲雖躲過絞刑台,餘生卻只能在修道院度過。壓抑的禁閉生活中,只有圖書館能作為她的心靈避風港。她讀遍所有醫學書籍,其中一本塵封多年的產科著作證實了她醞釀已久的猜測:新生兒的減少和女人的虔信與美德並無關聯。
為了找到寫下該書的女醫生、也為了尋求更多不見容於教會的知識,艾妲冒險離開修道院,卻被拋棄於荒野,摸黑來到了一個名為「牆洞幫」的盜匪幫派營地,這是一幫身著男裝、劫富濟貧的女槍客,她們以高地絕壁為家,附近的城鎮對這群劫匪聞風喪膽,卻從不知道她們是女兒身,且皆是因為未能完成婚育「責任」而被迫害與放逐的女子。
她們的首領「小子」的目標不只是帶著手下成為英雄義賊,她始終冀望建立一塊不受教會控制、女人無需被強迫生育的樂土,女槍客們也不必再偷拐搶騙。可是,「小子」精心策劃的一樁銀行搶案出了差錯,不僅帶來成員死傷,更有人起了叛離之意。艾妲原本以為自己找到了新的家園,如今卻要重新面對前途抉擇:是要跟隨心生去意的成員們下山、躲藏在社會邊緣生存,或是相信「小子」的理想、再次鋌而走險執行搶劫計畫?究竟哪一條路,才能帶著她和這個世界走向她渴望的真知與自由?
┤推薦好評├
「若活在一個否定你性別的世界,該如何尋找自由與生存的權利?《絕壁上的她們》將性別框架如何被根深蒂固地建立,又如何重新顛覆詮釋得淋漓盡致,但也絕非是只有讓人產生不要小孩、甚至仇女、仇男這樣的二元對立思想。藏在冒險故事背後的仍是希望這個世界真實傾聽個體差異,也要我們面對內心真實的聲音。主角艾妲對於知識的渴望、相信愛人的能力、以及透過知識來幫助他人,扭轉自己曾經遭遇的絕境,都將是能捍衛自己身體自主權的最佳武器。」──畫說有一天(IG說書版主)
「令人目不轉睛的故事,與我讀過的任何書都截然不同!這些女性亡命天涯的冒險激切動人,對於自我定位的追尋和絕境求生的意念是其背後的動力。」──瑞絲‧薇斯朋
「諾思的強勢新作,記錄了一名助產士的女兒如何加入了由女性和非二元性別者組成的一幫亡命匪徒……這些人物掙扎地爭取非傳統的性別角色與非異性戀者的權利,描繪的筆調溫柔且優美,是一則令人不忍釋卷的女性西部寓言。」──《出版人週刊》
「一部關於局外人的故事,寫實地描繪出一個思想封閉、只接受女性服從特定框架的世界。艾妲是一位勇敢無畏的主角,求知欲像血液般在她全身流動。」──《書單》雜誌
「以西部故事混合架空歷史和女性自覺意識,似曾相識地熟悉,內在卻又徹底地改頭換面。諾思以快馬奔馳般的流暢文筆寫出一段充滿電影感的精采冒險。」──《華盛頓郵報》
「諾思筆下的故事既有新奇的實驗性,也具有經典格調,瑪格麗特‧愛特伍的《使女的故事》書迷將格外享受這趟探討性別角色、自主性與自我追尋的旅程。」──《波士頓環球報》
「傳統西部故事中的英雄總是非常肯定是什麼讓他們成為如今的自己、是什麼讓男人之所以為男人。但對於艾妲和這部精采小說中的其他『亡命之徒』而言,性別與性的表現是仍待探索的疆界。」──NPR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絕壁上的她們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280 |
歐美文學 |
二手書 |
$ 282 |
二手中文書 |
$ 316 |
英美文學 |
$ 316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340 |
小說/文學 |
$ 352 |
中文書 |
$ 360 |
美國現代文學 |
$ 36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絕壁上的她們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安娜‧諾思Anna North
生於洛杉磯,現居紐約布魯克林,從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畢業後,曾是《紐約時報》、線上雜誌Salon 和 Buzzfeed的記者及撰稿人,現於網路媒體Vox擔任資深記者。她在二○一一年以反烏托邦文學小說《島嶼末日後》(America Pacifica,暫譯)出道,四年後交出第二本作品《心碎拼圖》(The Life and Death of Sophie Stark,暫譯),在不到三百頁的篇幅中,流轉於七個視角,烘托天才導演主角的崛起與隕落;《絕壁上的她們》則更具有探討性別、母職、孕產議題的宏大企圖心,以流暢的文字讓筆下女主角闖蕩充滿陽剛之氣的西部小說場景,毫不費力塑造富有顛覆意味的獨特反差,既描繪生育自由被控制的灰暗世界,也寫出女性結盟的動人故事。主角群遭逢的蒙昧偏見與規訓迫害,在故事中令人同情且不平,對照「羅訴韋德案」保障的妊娠中止權被保守派大法官釋憲推翻後的美國現狀,更是充滿警醒人心的寓言性。這部突破之作不但屢獲名人讀書俱樂部推薦、空降《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更由艾美‧亞當斯製作公司 Bond Group Entertainment 簽下電視劇版權。
譯者簡介
力耘
六年級生,兼職譯者,動物醫學相關科系畢業,轉介文字十餘年。
安娜‧諾思Anna North
生於洛杉磯,現居紐約布魯克林,從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畢業後,曾是《紐約時報》、線上雜誌Salon 和 Buzzfeed的記者及撰稿人,現於網路媒體Vox擔任資深記者。她在二○一一年以反烏托邦文學小說《島嶼末日後》(America Pacifica,暫譯)出道,四年後交出第二本作品《心碎拼圖》(The Life and Death of Sophie Stark,暫譯),在不到三百頁的篇幅中,流轉於七個視角,烘托天才導演主角的崛起與隕落;《絕壁上的她們》則更具有探討性別、母職、孕產議題的宏大企圖心,以流暢的文字讓筆下女主角闖蕩充滿陽剛之氣的西部小說場景,毫不費力塑造富有顛覆意味的獨特反差,既描繪生育自由被控制的灰暗世界,也寫出女性結盟的動人故事。主角群遭逢的蒙昧偏見與規訓迫害,在故事中令人同情且不平,對照「羅訴韋德案」保障的妊娠中止權被保守派大法官釋憲推翻後的美國現狀,更是充滿警醒人心的寓言性。這部突破之作不但屢獲名人讀書俱樂部推薦、空降《紐約時報》暢銷排行榜,更由艾美‧亞當斯製作公司 Bond Group Entertainment 簽下電視劇版權。
譯者簡介
力耘
六年級生,兼職譯者,動物醫學相關科系畢業,轉介文字十餘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