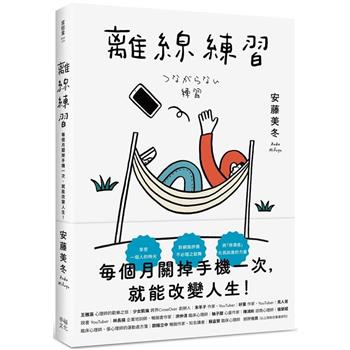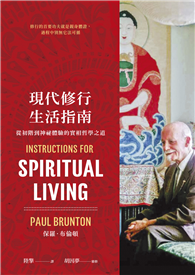/▌ 愛到極致是放手,不愛大概,也是。
請你諒解 我只是太害怕自己 對這場遊戲認真了而已 /▌
商場中強強聯手的King & Queen,私底下卻是相識十三年,縱然身體上時常互相連結,心靈上卻猜不透對方的男女。情場相逢,鹿死誰手?
/他們說出口的真心話──
‧「因為,我得在對你認真以前,愛上另一個人。因為你給不起我的,我不能給你。」
‧他和她之間沒有關係,所以沒有關係。
‧有時想要自清,可話到喉頭卻說不出口。誰要有時候就連她自己,也看不清楚呢。
‧不是妳廉價,我指的是妳認定的愛,都太廉價了。
‧男女朋友之間的關係值幾毛錢?就算結婚也只是一張紙的價值,唯一有價值的只有自己付出的感情。
‧人都有需求,只要雙向符合彼此的供需,自然就會建立關係。那是無關感情的。
‧「這世上所有願意做出承諾的人都廉價嗎?只有你這樣連未來都給不起的人,才夠高尚嗎?」
‧真正高貴的是不顧得失,是賭輸了也感謝上過這場賭局。可是我對你的感情不是那樣的。這才真的讓我感到廉價。
/關於她和他的內容簡介──
業績女王倪樂明豔大方,精明理智,高跟鞋踏出一單又一單的成交,對於成功,寸土不讓。
公司金牌奧杰高大頎長,一身傲氣,身材是最適合西裝的挺拔,舉手投足自帶氣場。
奧杰與倪樂就是King & Queen,合作無間,生意場上所向披靡。
他們看上去如此登對,他們的身體如此契合,他們的傳言到處都是,但他們的心,卻比所有人認知的都要遙遠。
倪樂偽裝成風情十足的高等玩家,其實拚盡全力才能維持從容優雅;奧杰是游刃有餘的情場老手,不相信天長地久,不懂愛為什麼需要框架,有了當下何苦追求摸不到的永遠。
他給不起倪樂想要的,而她不敢跟奧杰索取她想要的──王與后誰能取得勝利?
愛情的賭局,只要入場,不到終局,不知誰輸誰贏......
/成年男女的交遊,最怕真心相待──
「我承認,我有多害怕從你那裡得不到等量的感情,我對你的感情就有多廉價。」她踩著優雅的步伐來到奧杰跟前,眼神輕蔑,「同樣的,你有多害怕給我承諾,我們對彼此而言就有多便宜。我們這十幾年就是各取所需,無聊了就見面,想要了就做愛,還有什麼比我們之間更方便的嗎。」
奧杰近距離看見倪樂回到如常的笑臉,他張口想反駁,卻發現什麼也無法脫口。
倪樂抬頭對上奧杰片吋失序的目光,不由得清脆地笑了,那笑聲太過輕盈,有著直視一切的坦然。
她把她不該說的,都說給了不該聽的人。
於是就再沒能失去什麼了。
──人都有需求,只要雙向符合彼此的供需,自然就會建立關係。
──那是無關感情的。
倪樂思索著他的一字一句,注視著他無關痛癢的模樣,立刻明白,這不會是她要的人。
不能是。
作者簡介:
夢若妍
喜歡貓,喜歡小吉利,喜歡便利商店的熱咖啡。
十二點以前睡覺是天方夜譚。
哦,小吉利是一隻狗。
我希望人生裡都可以有一種特例,就像這樣。
可以在平凡無奇裡。
特別喜歡。
著有十本以上長篇小說出版作品,多部語音創作,現為談個念愛工作室創辦人,平時接案授課、演講,亦接案撰寫客製化小說、雜誌專欄、品牌故事、新聞稿及各式紀念冊等商業文案。
已出版作品:《兔子先生不要跑》、《如果青春滂沱》、《第一次不愛你就上手》
#個人網站:夢若妍 weebly
#臉書專頁:夢若妍(言若夢)
#YouTube語音故事小盒子:夢若妍 說
章節試閱
倪樂十五歲的夏末,在早晨的公車站前第一次見到奧杰。
「為什麼要分手?」
「妳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們都交往四年了!難道這對你來說一點意義都沒有嗎!」
「那不是我該問妳的嗎。」
奧杰的嗓音低沉,比作海的深度,約莫是兩百公尺透光層以下的海。那裡深層無光,那裡可以冰冷得毫無情感。
倪樂坐在候車亭的金屬長椅上,候車亭長方區域架了遮光棚頂,一身休閒裝束的奧杰站在棚頂外,炙熱的烈陽打亮他面無表情的面孔,女方則站在棚頂內,一身碎花洋裝。
女子背對著倪樂,以致倪樂無法看見她帶著什麼樣的神情,可倪樂聽見她斷斷續續地抽泣了。女子的黑色馬尾隨哭泣顫動,嗚咽著似乎想辯解些什麼。
奧杰蒼涼的眼底卻無所動搖,深色的唇尾甚至勾起了微笑。
他的雙手揣入口袋,姿態頹痞地彎身湊近女子的耳。
「妳破壞了協議。破壞協議的時候,妳有想過那四年的意義嗎。」
寒涼而緩慢的語句讓倪樂不由得背脊發麻。那是沒有轉圜餘地的語氣,含著嘲弄的輕蔑。倪樂定睛看著他的臉,她只看見一副不慍不火的雙眼。奧杰壓在濃眉下的眸子炯然,眼尾微幅上揚,他眸色淺棕,在陽光下竟有些剔透。倪樂在那雙眼中看不出人類在這樣情境下該有的任何情緒。那些悲傷,惋惜,在那對目光中並不存在。倪樂甚至能夠篤定,他絲毫沒有隱忍。
奧杰的微笑並不虛假,那並不是壓抑痛苦所強裝的笑臉。
他當真毫無所謂。
「好了,把眼淚擦一擦。」奧杰相當理智地由口袋捉出一包袖珍面紙,遞到女方手上時甚至沒有碰到任何一吋肌膚。
就在這時,一輛公車到站,門開,公車內走下一對老夫婦與一位男學生。奧杰看過去一眼,語氣自然地催促女子:「上去吧,錯過這班,又要等二十分鐘了。」
女子明顯顫抖起來,「你就只會催促我!你連二十分鐘都不願意給我,從以前就是這樣了!別人情侶都會依依不捨十八相送,就你不會!」
奧杰突然笑了。
「是啊,我的錯。」他說,「所以妳為什麼不搭上這班公車,趕快去找那位一直都會和妳十八相送的人呢?」
奧杰轉頭透過大敞的車門,向正準備關門的公車司機喊道:「大哥!不好意思,還有一位要上車!」
他望回面前的女子。
「搞清楚,妳要錯過的不是這班公車。」奧杰又一次湊近她的臉,沉下聲嗓:「妳要錯過的是什麼,妳自己清楚。」
女子抽咽得更加厲害,她哭出聲來,最後像是忍無可忍,轉身逃上了公車。
當公車載著女子遠離目視範圍,奧杰收回目光,走入了候車亭,坐到了倪樂身邊。
誰也沒有說話。
距離座椅三步遠的圓柱旁,站著一對剛從公車上走下的老夫婦,他們看著圓柱上的公車路線圖,專心討論著下一站該轉乘幾號車。
倪樂望過去。
那兩張年邁的臉上盡是和祥,他們無視奧杰與女子的紛爭,他們把世界過得只有他們兩人那麼小,又小得那麼剛好。
「他們會一起搭到下一站。」
奧杰忽然說話,倪樂一下子回神看向身旁的奧杰,卻只看見他姣好的側臉。他直挺的鼻樑沒有眼鏡遮擋,起伏明顯的唇線靜止,目視前方的棕色眼睛直盯著馬路上來往的車流。倪樂看著這模樣,一下子分不清那句話是不是他說的。
「什麼?」倪樂只好試探地問,「你在和我說話嗎?」
奧杰提高了眉梢望過去。
「當我自言自語,」他用著疲懶的神態,說著禮貌的話語:「我只是想把想到的說出來,吵到妳的話很抱歉。」
那張慵懶的神色實在與他說出的話背道而馳,那雙眼毫無抱歉的成分,反倒有種倪樂吵到他的意思在。這副表裡不一的死樣子讓倪樂不由得笑了。
奧杰沒料到倪樂會有這樣的反應。
「為什麼笑?」
倪樂被問得停下笑聲,搖搖頭,「沒什麼,別在意。」她指向一旁仍在討論去向的老夫婦,「你說的對,他們會一起搭到下一站,沒意外的話,我想他們會一起搭到最後一站。」
奧杰勾起一側嘴角,「妳想說人生的終站嗎。」
「不對嗎。」
「沒有不對。」奧杰微笑著伸了懶腰。
他身上有古龍水的氣味,混雜著車輛來往的廢氣,聞上去竟有種焦香。倪樂仔細聞著,觀察著眼前的男子。當年的奧杰正值大學生年紀,年長了倪樂足足六歲,在那一年的倪樂眼中,已足夠形容為男人。他身上有著不羈與穩重並存的氣味。
她看著他的每一道舉止,審視他的每一道面部表情,不由得在一輛輛公車駛過後,脫口而出:「你真奇怪。」
奧杰望了過去,眉間一蹙,「奇怪?」
「你不太像人。」
「什麼?」
「我看不出你的情緒波動,你是不是有感情麻木的問題?」
倪樂問得相當正經,奧杰看著那副搪瓷娃娃般的臉孔說出彷彿心理醫生的台詞,突兀地笑了。
這下換倪樂搞不懂他為什麼笑了。
「我是認真的。」她說,「我先說清楚,我不是故意偷聽,但你們剛才說話太大聲了。你們談分手,你也不難過,你從頭到尾平鋪直述,就事論事,你向她道別得不會太理性了嗎,明明這很可能是你們最後一次見面了。然後你根本就不同意兩個人會一起走到人生的終點,你只是嫌麻煩、不想和我這種小孩子吵,所以告訴我我的想法沒有不對。
「但你其實是不相信天長地久的,對嗎。」倪樂面色平靜地滔滔不絕,「不相信天長地久對你而言,就好像只是不相信垃圾車會準點抵達一樣無所謂。你是不是曾經受到什麼大刺激?研究學家說這是創傷症候群,要去看醫生的。」
「不是、妳拐個彎罵我有病呢?」
「你看,你又轉移話題了。」倪樂指著他的臉,「下意識避開壓力來源也是一種病徵,你很嚴重。」
奧杰自小品學兼優,頭腦靈活,運動神經絕頂,這輩子就是這一刻第一次被人堅定不移的說他有病,還病得很嚴重。奧杰一下子就忍不住大笑了。
「這並不是什麼好笑的事情。」倪樂蹙了眉頭,「你真的很奇怪。」
奧杰笑意未脫地看見倪樂坐遠了一些,她毫無遮攔表達不想扯上關係的模樣,又讓奧杰起了興致。
他兀自湊近,倪樂卻沒地方再退得更遠,她已經抱著書包擠在公車亭的鐵隔牆與鐵座椅之間。她的公車還有二十分鐘才來,她不想因為這人而苦站,只得面色不善地瞪向奧杰。
「你別碰我。」
「我沒碰妳。」
「所以我這是在警告你。」
「否則呢?」
「否則我是可以告你的。」倪樂橫眉豎目,「你這種行為放在剛分手的狀態下,就是渣男你知道嗎。」
「為什麼?」奧杰感到好笑,隻手靠上膝蓋,支著腦袋斜望著她笑,「女友看上別人所以我放她自由,我還得為這份關係守喪?」
「不是,是為你自己的感情。」倪樂吊高了眉梢,半闔著明亮的杏眼,「誰管那段關係的死活,男女朋友之間的關係值幾毛錢?就算結婚也只是一張紙的價值,唯一有價值的只有自己付出的感情。沒有付出感情還好意思稱自己是男友或老公的人,才是最失敗的。你不需要守喪的原因,顯然是你沒有對她付出足夠的感情,她會走向別人也不意外。」
「這麼說來,付出感情才能經營一段關係?」奧杰勾起弧度好看的嘴角,直起腰桿直視她一本正經的臉,笑道,「妳的思想不會太童話故事嗎?社會上多的是為了責任去經營關係的男女,妳是說他們都很失敗?」
「別扭曲我的話。」倪樂同樣直起腰脊,看上去理直氣壯,「舊時代的婚姻建立在責任上,可以理解。但是你和她是指腹為婚還是因為什麼脫不開的責任才在一起的嗎?」
「不是。」
「既然是自由戀愛下的產物,那麼就應該建立在情感上,不是嗎。」
「不是。」
「什麼?」
「沒關係,妳長大點就會明白了。」奧杰笑開了眉眼,伸手搓她的髮,又立刻捏上她的下頷,「人都有需求,只要雙向符合彼此的供需,自然就會建立關係。那是無關感情的。」
奧杰的臉就在倪樂眼前,近距離下,她竟腦子一片空白,頷邊的觸感粗糙溫熱,一時之間讓她什麼也忘了反駁。
當她回過神來想指控他的無禮時,奧杰倏地鬆開了手,坐正了身子。
倪樂簡直不敢置信。
「你自己有發現你滿口歪理嗎?」
然而奧杰只是綻開了笑靨,舒適地靠著椅背,闔上深邃的眼睛哼起柔軟的曲。
──人都有需求,只要雙向符合彼此的供需,自然就會建立關係。
──那是無關感情的。
倪樂思索著他的一字一句,注視著他無關痛癢的模樣,立刻明白,這不會是她要的人。
不能是。
*
高中三年級的時候,倪樂接到一封奧杰的簡訊。
那時她正在學校外掃區打掃操場,冬日的暖陽底下,她半遮著手機屏幕才看清上頭的字:救我,仁樓花圃,現在!
她不禁笑出聲來。
這是她生平第二次接到奧杰的求救,第一次他傳訊息要她打電話給他,電話一接通他就把她給說成他媽,她半句話都沒來得及說,他就在電話裡急匆匆的說他這就回去吃飯,電話就斷了。
斷線以前,倪樂還聽見電話那頭隱約的女聲說著這麼早嗎──那拖長的尾音略帶撒嬌的味道,她就立刻明白這都什麼狀況了。
於是這會兒,十八歲的倪樂很清楚自己要是什麼角色。
她拿著掃把走向校內西側的仁樓,緩著步伐繞著建築物外牆,果真在靠近後門的一個轉角,聽見九十度牆面的另一側傳來相當激烈的談論聲。
「我不需要你的關心!」
「那妳到底要什麼?」
「我要你愛我!」
那樣撕心裂肺的女性嗓音迴盪在冰涼的空氣裡,一身黑白制服的倪樂無聲嘆息,她扣上了第一顆鈕扣,將白色襯衫紮進黑色制服裙,她並且整理了自己尚未染燙過的黑色長髮,確認自己一身乖乖牌模樣,這才走出轉角。
她看見站在花圃裡的奧杰,以及奧杰面前、一位淚流滿面的女子。
這一年奧杰早已將頭髮染黑,身穿一襲乾淨的卡其套裝,他的襯衫與長褲熨燙得整齊俐落,更顯得他面前的女子狼狽不堪。
頭髮散亂的女子一看見倪樂,旋即撇過頭,雙手輪流抹去臉上四散的淚。她清了清嗓子,回過頭時露出嚴肅的表情。
「這位同學,現在是打掃時間,妳為什麼在這?」女子皺緊眉頭,語氣責怪,她輕盈的妝容並未被淚水糊花,可濃重的鼻音與哭啞的嗓子仍然洩露了她痛哭過的痕跡。她試圖鎮定,指著倪樂手上的掃把,「這棟是教師辦公大樓,學生不用來打掃的。妳幾年級了,不知道嗎?」
「報告老師,很抱歉,但我是來找奧杰老師的。」倪樂這一年對於說謊仍舊不熟練,於是她低下了眉眼,努力讓自己的演技好一些,「真的有很重要的急事,是有關我爸媽的事。我剛剛接到消息,所以想馬上和老師商量。」
「什麼事?又是之前的問題嗎?」奧杰演技老練地接了話,蹙起濃眉露出滿是擔憂的神色,隨而向一旁的女子道歉:「抱歉,我們的事之後再談。這學生在我負責的班上,我得處理一下。」
女子一聽事情攸關學生家長,奧杰又是一副憂忡的模樣,她只得勉強軟下態度。
「原來是這樣。」女子上前拍了拍倪樂的肩,轉而附上奧杰一側的耳,「我先回辦公室,我們下班再談。」
「好。」奧杰點點頭,給了對方一個無可挑剔的微笑。
待女子走入大樓,消失在視線範圍,倪樂歪著頭打量起奧杰。
回過頭看見倪樂的眼神時,奧杰笑道:「怎麼了,怎麼那樣看我?」
「剛才那是和你同期的實習老師對嗎?」
「是啊。」
「和你同歲?」
「對。」
「交往多久了?」
「半年。」
「為什麼吵成那樣?」
「她希望我從實習老師升上正式教師後就結婚。」
「你不要嗎?」
「為什麼要?」奧杰的語氣聽上去竟理所當然,「我本來就沒打算結婚。」
「沒打算結婚,還和人交往,這不是相當沒有禮貌嗎。」
倪樂不假思索的一番話,讓奧杰反射性地笑了。
「交往和結婚是兩回事,為什麼大家都要理所當然的把它想在一塊,妳不覺得連問都沒問就幫對方決定要和自己結婚,也是相當沒有禮貌嗎?」
倪樂聽著竟感到佩服,這世上還有這麼個外星人啊。
她搖搖頭,唇瓣勾起無奈的弧,「給不起人家未來,怎麼好意思談交往。你怎麼就是學不會當個正常人呢?」
奧杰低下眸子笑開了嘴。
「妳倒是有進步。」
「什麼?」
倪樂歪了歪腦袋,奧杰提眼看見她困惑的神情覺得可愛,不由得一隻手就掐上了她的臉。
「妳倒是學會說謊了啊。」
奧杰這句話讓倪樂一下子意識到,剛才她確實騙過了那位女子。
倪樂拍開捏在她臉上的手指,思考了半晌,又回到一貫的誠實:「因為要救你,所以我努力了。」
她拙劣的演技,為了這個人,而磨練了一季,又一季。
她為他騙過一個又一個女人。
然後她變成了女人。
她再為了他,騙過一次又一次的自己。
倪樂十五歲的夏末,在早晨的公車站前第一次見到奧杰。
「為什麼要分手?」
「妳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們都交往四年了!難道這對你來說一點意義都沒有嗎!」
「那不是我該問妳的嗎。」
奧杰的嗓音低沉,比作海的深度,約莫是兩百公尺透光層以下的海。那裡深層無光,那裡可以冰冷得毫無情感。
倪樂坐在候車亭的金屬長椅上,候車亭長方區域架了遮光棚頂,一身休閒裝束的奧杰站在棚頂外,炙熱的烈陽打亮他面無表情的面孔,女方則站在棚頂內,一身碎花洋裝。
女子背對著倪樂,以致倪樂無法看見她帶著什麼樣的神情,可倪樂聽見她斷斷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