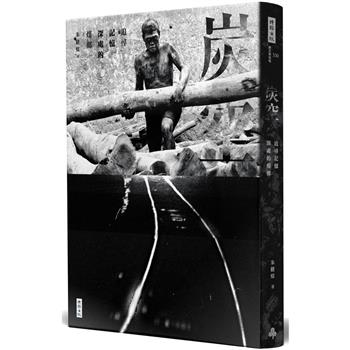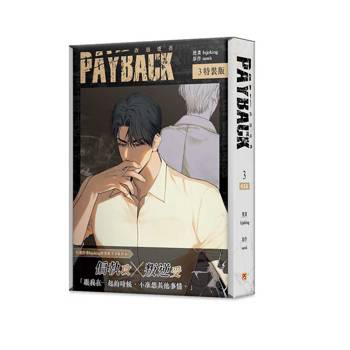你一定聽過這個說法:
全世界至少有一個人,會與你長得一模一樣。
如果這不是訛傳,
而且他願意不擇手段,成為「你」……
《那年雪深幾呎》暢銷作家布萊恩‧弗利曼帶來爆炸性的全新心理驚悚作品,突破所有認知的現實極限!
☆環球影業重金奪下電影版權,王牌編劇Chris Morgan操刀劇本!
☆美國亞馬遜超過上萬讀者評價,罕見超過半數★★★★★五星滿分!
☆「令我無話可說的傑作!」──Goodreads好讀網網友超高分推薦!
▍關於布萊恩‧弗里曼
★作品翻譯成 22 種語言、行銷超過 46 個國家
★獲麥卡維提獎、國際驚悚獎,並入圍愛倫坡獎、安東尼獎、巴瑞獎和金匕首獎四項國際大獎
★被陸德倫家族欽點為下一位《神鬼認證》系列小說的執筆者
你一定聽過,「世上會有至少一到三位和自己長相一樣的人」的說法。
假如這不只是個詭異的都市傳說,而是真實存在的現象呢?
另外一個你,在他的世界裡,
會過著和你截然不同的生活,還是與你走上相似的道路?
若是他痛恨自己的人生,若是他更嫉妒你的生活,
若是他願意不擇手段地成為你……
▍媒體好評
「巧妙的劇情安排,搭配引人入勝的角色。弗利曼一定會透過這部令人愛不釋手的作品贏得更多粉絲。」──《出版者週刊》
「很少有心理驚悚作品不僅能在這方面圓滿成功,還能牽動讀者的心弦,留下令人難忘的閱讀體驗。《無限人生》是非常特別的作品,我強力推薦。」──Bookreporter
▍原文版編輯好評
在一場怪異車禍中失去妻子卡莉的那天晚上,迪倫‧莫蘭確信在河邊看到了他自己。
他也知道這聽起來有多瘋狂:卡莉只有一個,迪倫也當然只有一個。
然而,迪倫上門求助時,精神科醫師伊芙‧布萊爾是這麼說的:他、卡莉和任何人都有無數個版本的「自己」,因為世界有無數個。
有時候,這些版本的自己能進入其他版本的宇宙。
在迪倫的案例中,他的某個版本意圖摧毀其他迪倫的世界,殺死那些迪倫身旁的人,並嫁禍給那些迪倫。
在這部令人費解的驚悚作品中,暢銷作家布萊恩‧弗利曼證明了自己不僅擅長安排曲折劇情,更精通人類心理,他知道是什麼因素驅使我們做出決定……並希望自己能改變這些決定。
希望您和我一樣喜歡這趟旅程。
──潔西卡‧翠柏‧威爾斯,原文版編輯
▍故事大綱
一個下雨的夜晚發生了一起悲劇:
迪倫‧莫蘭的汽車衝出公路,掉進洶湧的河中。
他勉強爬上岸,但他美麗的妻子慘遭溺斃。
事後,悲痛的迪倫出現一種怪異幻覺:
無論他去哪裡,似乎都會看見自己的分身。
迪倫最初將其歸咎於心靈創傷,
直到他遇到一位聲稱迪倫是自己病人的精神科醫師,情況發生了變化。
她說迪倫一直在接受一種獨特的催眠治療,原理是每個選擇都會創造出無數個平行宇宙。
這一切都是極為錯亂的南柯一夢?
迪倫身亡了?這是來世?
又或許,這只是一個男人在失去妻子後因悲傷而發瘋?
假如這真的是一種新的治療方式,能讓人們穿梭於不同世界之間,
那麼這些平行宇宙如今被解鎖,而迪倫的分身正嘗試要佔據他的世界。
迪倫能否利用這些替代現實來獲得第二次機會,奪回失去的生活?
又或許,他會輸給……他自己?
作者簡介:
布萊恩‧弗利曼Brian Freeman
紐約時報暢銷作家,擅長撰寫心理驚悚類的犯罪小說。作品售出四十六國以及二十二種語言,以複雜角色關係、人性描寫、結尾多重轉折的故事獲得各界盛讚。曾榮獲「國際驚悚小說作家獎」與「麥卡維帝獎」,並入圍過英國犯罪作家協會的「金匕首」、美國推理作家協會的「愛倫坡獎」、鮑查大會的「安東尼獎」與《Deadly Pleasures》雜誌的「巴瑞獎」。
二○二○年,繼勞勃‧陸德倫(Robert Ludlum)與艾瑞克‧范‧勒斯貝德(Eric Van Lustbader)之後,被官方欽點為「神鬼認證系列」新一代的續寫作者,在歐美掀起一波的弗利曼旋風。
譯者簡介:
甘鎮隴
從事翻譯多年,工作內容涵蓋各種領域。小說譯作包括:《星河方舟》、《完美世界》、《闇黑之心》、《玻璃王座》、《魔獸世界》、《星際大戰》、《骸骨季節》系列,《魔獸:崛起》電影小說等。
章節試閱
「我們對於您的失去深感遺憾,莫蘭先生。」警察對我說話的同時,把一個盛著咖啡的白色保麗龍杯遞給我。他手裡拿著自己的咖啡,嘴裡吃著一顆糖粉甜甜圈,鬍鬚沾染一層白粉,看起來就像草坪上的新雪。
我不發一語,覺得茫然麻木,彷彿處於昏迷狀態,不確定會不會醒來。寒意凍得我發抖。他們拿走了我濕透的髒衣物,用羊毛毯裹住我赤裸的身體,但這毫無幫助。一名就住在附近的女警表示會幫我把我的衣服洗乾淨再烘乾,明天早上之前還給我。我雙臂和兩腿上的深切傷口已經消毒包紮,但我還是覺得刺痛。我咳個不停,還能嚐到河水的味道。
嚐起來像死亡。
「雨要麼下得太多,要麼下得太少。」警察說。
他看起來大概四十歲,一張圓臉,頭上沒剩多少棕髮,兩邊鼻孔中間有一顆很大的痣,讓人想不盯著看都難。他身形肥潤,整個人乾淨又乾燥,是晚上會坐在辦公桌前的那種警察。另外兩個年輕健壯的警察在原野發現我,我當時臉上湧流著雨水和淚水。
這是哪裡?
這是哪個城鎮?
我毫無頭緒。是警察開車載我來這裡,但我完全不記得過程。我只記得他們把我拖走的時候,我喊著卡莉的名字。她還在河裡。
「雨要麼下得太多,要麼下得太少,」警察重複這句話。「這個地方在這個季節就是這樣。五月和六月乾燥得跟枯骨一樣,快把農夫們搞瘋了,田地硬得就像石頭。結果來了這場暴雨,水全跑進溪裡,河岸根本沒辦法一下子引開這麼多雨水。」
他說的沒錯。我爺爺在北達科他州的平原長大,那裡的河川水位每年都會隨著春天融雪而上漲,他常常警告我注意河流。永遠別相信河川,迪倫。只要給河川一點機會,它就會想辦法要你的命。
我真該聽他的。
「抱歉,這種時候還要你填寫這麼多文件。」警察接著說。他好像名叫華倫,但我實在沒心力抬頭查看他的銘牌。「我知道你現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文件,但既然有人死了,我們就得處理很多步驟,法律就是這樣。就像我剛剛說的,我深感遺憾。」
「謝謝你。」我幾乎不認得自己的嗓音,聽起來根本不像我。
「你能不能再告訴我一次,尊夫人叫什麼名字?」
「卡莉‧錢斯。」
「你跟她的姓氏不一樣?」
「不一樣。」
「她幾歲?」
「二十九。」
「你呢?」
「我三十二。」
「你們倆住在芝加哥?」
「是的。」
「你們怎麼會跑來這個州的這一區?」
迪倫,我們出門幾天吧。我知道你難過又生氣,你也完全有理由,可是我們需要從頭來過。
「抱歉,你說什麼?」
「我說,你們怎麼會跑來這個州的這一區?」
「我們出城度週末,」我答覆:「卡莉有個朋友住在比格內克鎮。」
「你在芝加哥是做什麼工作,莫蘭先生?」
「我在拉薩爾廣場酒店擔任活動籌辦人。」
「尊夫人呢?」
「她為她母親工作,是房地產仲介。」過了幾秒後,我補充道:「她生前是。」
華倫把最後一口甜甜圈塞進嘴裡,再用餐巾把鬍鬚擦乾淨。他不停地在手上的黃色便箋簿上寫筆記,同時哼著小曲。我環視這間警局偵訊室,這裡沒有窗戶,牆上的乳白色油漆斑駁脫落。華倫坐在一張搖搖晃晃的橡木桌的一側,桌子十分老舊,木材上還看得到菸頭留下的燒痕。我坐在桌子的另一邊,像新生兒一樣蜷縮在毛毯裡。我不能信賴自己的任何感官。我呼吸時,只聞到鼻腔裡的潮濕水分。我一閉上眼睛就彷彿回到車裡,被遊行花車般的河水推擠。
「你有辦法回城裡的家嗎?」華倫問我:「有沒有什麼家人、朋友還是誰能來接你?」
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沒有家人,不算有。我爸媽在我十三歲那年死了,這是我給人們的標準答案,比說「我爸殺了我媽然後在我面前自殺」要容易許多。後來,我搬去跟我爺爺一起住。艾德加今年已經九十四歲了,而且不開車。我跟他還算處得來,但不算處得好,如果你瞭解我的意思。我跟他就是這樣。
至於朋友……羅斯科‧泰特是我的兒時玩伴,總是在我出事的時候幫我解圍,他在四年前把我保釋出獄後死了。我就是在那晚遇見卡莉。我當時渾身是血,一條胳臂和一條腿骨折。羅斯科死在駕駛座上,頸骨斷裂。我以為我也死了。我凝視碎裂的車窗外面,看到一個天使凝視我,她的裙襬在風中飄揚,她把手伸進窗裡,握住我的手。她用輕柔嗓音呢喃,說很快就會有人來救我、我會沒事的、她不會離開我。
她是卡莉。
如今她死了。又一場車禍。
「我沒有任何人能幫我。」我告訴華倫。
「噢,」警察皺起鬍鬚。「這個嘛,我們會想辦法。別擔心,我們會把你送回家。」
「謝謝你。」
我們坐在這裡的時候,偵訊室的門打開。副警長一臉驚訝,跳起身,拍掉袖子上的糖粉。一名五十多歲、苗條矮小的女子站在門口。她雖然個頭嬌小,但散發十足的威嚴感。她的金髮在腦後紮成一個緊緻的髻,幾縷瀏海覆蓋額頭。她的棕色眼眸顯得彬彬有禮,平靜的嘴角不喜不怒。她的制服有點潮濕,彷彿是從室外進來,但線條筆挺。
「警長,」華倫驚呼:「抱歉,我不知道妳會來。」
警長不耐煩地瞥副警長一眼,表示他一點也不該因為她在凌晨四點到來而驚訝。有條河泛濫成災,有個女人死在她掌管的縣郡。這種事在這裡是大事。
「我來接手,華倫。」
「是,長官。」
華倫迅速離去,同情地對我點個頭。警長坐下,打開一個資料夾,裡頭有一小疊文件。我瞥向最上頭那張,看到一份來自芝加哥警察的事件報告。我相當確定上頭寫著我的名字。
「你好,莫蘭先生,」她說:「我是辛克萊警長。我向尊夫人之死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謝謝妳。」
我意識到,人們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其他臺詞可說,而且說出這種話會讓他們感覺更好。我為你的失去感到遺憾。但身為就在剛剛失去一切的那個人,我可以告訴你,這句話毫無幫助。
「我想知道,你能不能幫助我瞭解事故的細節。」
「我已經這麼做了,警長。」
「是的,我知道你已經向我的手下說明,我也知道這對你來說多麼困難,但如果你能再跟我描述一次,這會很有幫助。」
我照做。
我重播了整起事件,就像一部沒辦法停止播放的的恐怖片。我描述雙車道道路如何消失,被漫過河岸的如墨黑水吞沒。我們如何陷入泥濘水流,水像海怪一樣蠕動翻騰。我們的車子如何在水面上搖晃,就像拼命試著做出趾尖旋轉的舞者,然後車子的前端突然向下傾斜,泥水充斥車內。
「真悲慘。」我說完後,辛克萊警長開口。她的視線自始至終都在我身上。我感覺就像被綁在她腦海裡的測謊機上,探針追蹤著我的每次呼吸和心跳。這女人讓我聯想到我媽,她當年也是警察;在我小時候,她只要看著我的臉,就知道我有沒有說謊。
「你知不知道你們入水的時候,車速是多少?」警長接著問。
迪倫,開慢點。
「抱歉,妳說什麼?」
「你知不知道你們入水的時候,車速是多少?」
迪倫,求求你,開慢點。
「不,我不知道,顯然太快了。我看到洪水的時候,已經來不及停下來。」
「車子立刻沉進水裡?」
「是的。」
「你們倆都被困住?」
「是的。」
「那麼,為什麼你能從車裡出來,但你妻子沒有?」
我整個人抽搐一下。在我的腦海裡,車子在水中上下翻轉。氣泡湧出車外。靠近我的車窗碎裂,某個東西像標槍一樣穿過。
「有條樹幹穿過車裡,」我解釋:「我成功脫身。我有試著救出卡莉,可是車子挪開,把她從我身邊帶走。」
「你有沒有潛入水裡找她?」
「當然有。」
「你是什麼時候放棄的?」
「我沒有放棄,警長,」我對她厲聲道:「我是失去了意識。後來應該是水流把我甩到岸上。我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在岸上,而且警察在場。」
「原來如此。」警長用指尖推推資料夾裡的一些紙張。雖然她的口氣維持中立,但我在她的語調裡聽見指控。「我還有幾個問題,莫蘭先生。你在發生車禍前有沒有喝酒?」
「沒有。」
「完全沒有?沒喝酒,沒嗑藥?」
「妳的副警長們已經給我做了檢查,結果都是陰性。」
「是的,我知道。不過我得說清楚,他們花了一些時間才完成測試,所以結果不一定可靠。我有在系統中查找你的名字。發生了這種案件,這麼做是例行公事。你有酗酒史,是嗎?我在你的資料裡看到兩次酒駕紀錄。」
「那是好幾年前的事。沒錯,我有時候會貪杯,但今晚沒喝酒。」
「了解。」
辛克萊警長轉動指間的鉛筆。她的視線依然鎖定我,彷彿在評估眼前這個男人。我總覺得女人會對遇見的男人迅速做出判斷,無論這麼做對她們來說究竟是好是壞。她們會在幾秒內判斷一個男人是否可靠。
「你的脾氣滿大的,是吧,莫蘭先生?」
「什麼意思?」
「除了酒駕以外,我看到你還曾因傷害罪而被捕,酒吧鬥毆之類的。你的紀錄顯示你可能有暴力傾向。」
「我曾在喝醉的時候犯過幾次錯,」我承認。「我為我做過的事深感後悔。」
「有沒有打過老婆?」
「沒有。我從沒打過卡莉或任何一個女人,從來沒有。」
「言語虐待呢?威脅?」
「完全沒有。」
「你們倆之間的關係怎麼樣?」
迪倫,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我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你能不能原諒我?
「什麼?」我問。
「你的婚姻狀況如何?」
「我們的婚姻還行。」我撒謊,這麼做很蠢。人們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卡莉有告訴她母親,我也跟我的一個同事說了。但我沒辦法大聲告訴這個警察,我的妻子給我戴了綠帽。
「你太太來自富貴人家,是吧?她姓錢斯,也就是錢斯房地產?」
「沒錯,錢斯房地產是她母親的房仲公司。卡莉替她母親工作。我不確定這有什麼關聯,警長。」
「我只是想弄清楚發生了什麼事。你當時開得太快,也許有人會說你是危險駕駛,而且你有酒駕和暴力行為的紀錄。」
我臉龐漲紅,能感覺隨著充血而來的熱氣。「妳究竟在說什麼?妳暗示是我故意把車開進河裡,害我老婆溺死?」
「我什麼也沒暗示。」
「這個嘛,妳似乎覺得我就是做得出那種事的人。」
「我根本不知道你是什麼樣的人,莫蘭先生。我沒說這場車禍是你的錯,我只是在盡我本分,查明事實。」
我俯身越過桌面。毯子從我赤裸的肩上滑下,我聳肩擺脫它。我提高嗓門,但嗓音帶有雜音,聽起來就像訊號不良的電臺。「妳想知道事實?事實是我太太死了。我愛她。我盡力試著救她,但失敗了。如果人生能給我第二次機會,我現在就會回去水裡救她。這樣夠清楚了嗎,警長?」
她的表情稍微變得柔和。「是的。我很抱歉,莫蘭先生。」
「我真的很想獨處,」我說:「這一切令我難以承受,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
「是的,當然。」
辛克萊警長闔起資料夾。她在桌上來回滾動鉛筆,然後把筆收進口袋。她站起身,走向門口,但開門時又轉身回來,再次打量我。
我知道她接下來要說什麼。
「還有一個問題,莫蘭先生。我的副警長們說,他們發現你的時候,你算是語無倫次。」
「這很令人驚訝?」
「不,當然不。可是他們說,你一直說你在事故現場附近的河岸上看到一個人。你一直問他為什麼沒幫你、他為什麼沒試著救你太太。」
我覺得口乾舌燥。這就是我說出來也不會有人理解的部分。
「我不記得這麼說過。」我回話。
「你真的有在河邊看到人?」警長問。
我閉上眼睛,深吸一口氣,再次覺得肺臟缺氧;我的臉浮出水面時,胸腔即將炸裂。我當時吞下一口氣,正準備再次潛入水中時,看到他。
一名男子。
有個男的站在不到十呎外的急流河岸上。閃電劃過的瞬間,我清楚看到他。我絕對沒看錯,而就算我看到的景象不可能是真的,這也不重要。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對他呼喊。懇求。哀求。
那名男子就是我的救命繩索。我需要他。他能救卡莉。
幫幫我!我太太溺水了!幫我找到她!
「沒有,」我告訴警長,保持嗓音平穩。「沒有,那時候是晚上,而且在下雨,我什麼也沒看到。」
她額頭上浮現少許皺紋。她顯然不相信我,但也搞不懂我為什麼要在這種事上說謊。但她只是再次對我綻放禮貌的微笑,走出房間,把門在身後關上。這裡變得安靜。我獨自一人,周圍只有乳白油漆剝落的牆壁,河水的臭味在我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沒錯,我剛剛說了謊,但我不能讓她知道我為何說謊。
我不能向她描述我看到的那名男子,因為我甚至沒辦法向自己解釋這件事。你大概以為我當時看到錯覺,這可能是事實。我當時驚慌失措,腦袋缺氧,而且那時候確實是晚上,確實正在下雨。
話雖如此,我知道自己看到什麼。
河岸上的那名男子就是我。
他就是我。
「我們對於您的失去深感遺憾,莫蘭先生。」警察對我說話的同時,把一個盛著咖啡的白色保麗龍杯遞給我。他手裡拿著自己的咖啡,嘴裡吃著一顆糖粉甜甜圈,鬍鬚沾染一層白粉,看起來就像草坪上的新雪。
我不發一語,覺得茫然麻木,彷彿處於昏迷狀態,不確定會不會醒來。寒意凍得我發抖。他們拿走了我濕透的髒衣物,用羊毛毯裹住我赤裸的身體,但這毫無幫助。一名就住在附近的女警表示會幫我把我的衣服洗乾淨再烘乾,明天早上之前還給我。我雙臂和兩腿上的深切傷口已經消毒包紮,但我還是覺得刺痛。我咳個不停,還能嚐到河水的味道。
嚐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