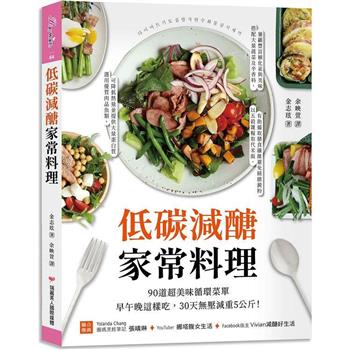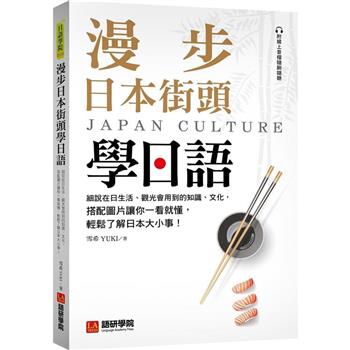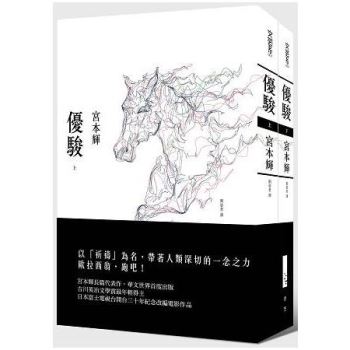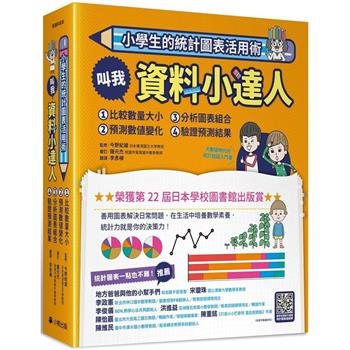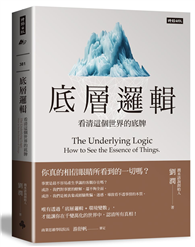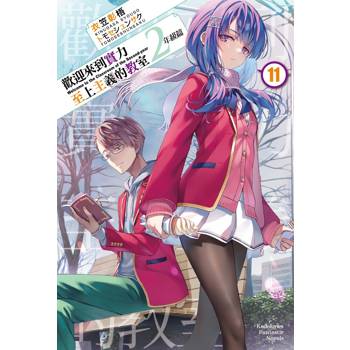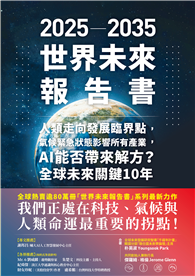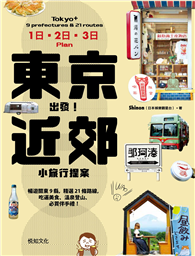任何一個年代,教師們都肩負者生命價值傳承的使命。然而,如何傳承?
對人心靈的看法影響我們對教育的理念與作法,西方學者指出如果相信「人心為白紙」,白紙需要外力介入才能產生色彩,就會認為教學的任務是促進學生思維能力的發展和客觀知識的獲得,類似於計算機似的輸入、作用、輸出過程;如果相信「人心像是一顆種子」,而種子裡面蘊含它成長所需要的養分,則重視提供滋養的環境,讓人擁有於內心世界與自己相處、以及面對外在世界的生活能力。中華文化的道統裡,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認為人本身就具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故能以盡心養性,陶養自身。荀子以人性本惡的觀點,認為人需要教化,才能積善成德,也指出人為萬物中最為貴者,「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作為一個人,身處於世,最可貴的是具反省感知能力。
處於基因體醫學與人工智慧科技不斷更迭的資本主義潮流中,身為教師的反省是,大學如何維護其追求知識真理的清流?大學的學術殿堂裡,教師、學生與知識,誰是主人?如何教?教什麼?
追求知識的教育歷程裡,當大學被資本化,知識被量化,知識成為主人,教師與學生都淪為追求知識社會價值的工具,那麼難以被量化的師生互動,就容易被邊緣化。當學習被量化、人性化約成數字,身體僅被視為知識的載體,忽略身體的需要與情感的訴求,也就輕忽學習的情境性與文化性。
實際上,學習是身、心、靈同步,經由對話促成身體與環境互動,學習主體通過認知、情緒、意志、行為的整體活動,不斷完善與豐富自身的心智體驗,不僅由環境中學習,也塑造著環境。尊重身體經驗的體知學習,可以減少知識導致的異化,不會盲目服從於知識生產體系。心理學家Maslow認為教育應培養健康的潛意識、健康的潛能、健康的直覺,學習不僅是知識與技能的成長,更要學習健康、愉悅、創造性的人生。他進而指出,人不是僅滿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自我實踐的需求,還有更高層次的超越個人之靈性需求(圖1-1)(李安德,1997;Maslow, 1993a)。小組教學,提供一個對話與體知的場所,促進人的超越性。
對話教育
對話教育,是透過對話激發學生的思維與好奇,開啟其內在的意識與思想,產生意識的覺醒。意識覺醒的重點,是幫助學生自我肯定而避免盲從,由依賴教師或權威規範的被動學習型態,轉化成反思實踐的主動學習型態,活用所學的知識技能(Freire, 2000)。
對話需要多感官的身體參與,包括書寫、言談、演劇、感觸、實作。對話不同於辯論,辯論著重的是以邏輯意義說服他人;對話是要了解他人和自我,產生新的意義,認識到自己是如何與人互動,成為一個勇於聽自己內在聲音的強者。小組對話時,大家依據過往的經驗和觀點,在此時此刻共同地思考,形成對於未來行動的期待。當人真誠地面對自己的生命經驗,透過他者經驗的映照、他人的話語、以及現場他者激發的對話,自身不僅向外觀察聽者的回應,同時也向內體察自身的反應,真實地訴說自己的感受想法,同時也挑戰自己的陳述(第十章)。使人由填鴨式堆積知識、忽略主體特殊性的「為他存有」壓迫結構,轉為嚴肅地反省自身存在的「為己存有」思維(宋文里,1995;陳榮華,1998;Buber, 1988)。源自現實經驗中的諸般紛擾,在團體對話中,暫時的停歇,使人得以重新觀看自身的經驗,深化生活與生命的內容。
體知學習
體知學習(embodied learning),重視教學情境中的身體感,主張學習是由身體的五感,以及心智直覺與周圍環境的相互作用。此學習不是僅以抽象思考與世界接觸,更以活生生的身體各種感官去感覺與觀察所處的世界,涉及體驗、體悟、體會、體察乃至體諒,並且源源不斷產生意義的「做中學」;不同於傳統教學中學習與生活經驗是兩條平行線的「聽中學」(杜維明,2002;范琪、高玥,2018;葉浩生,2015;Dixon & Senior, 2011; Skulmowski & Rey, 2018; Stolz, 2015)。
身體,不僅是生理的構造,也是對自我本身進行思考或展開自我與外界聯繫的起點(蔡璧名,2008);身體是肉身化的主體,不僅映照著我們存在的樣貌,也是知覺與學習的指揮者與執行者。以觀看、觀察、覺悟參與學習,有時是不具意圖的面對眼前的人物,不怕忘記,也不要求自己要記住的觀看(looking on);有時是有意圖的留意眼前的人物,盡可能找出其特質的觀察(observing);有時是當一個人出現時,感覺他似乎傳達什麼,但我說不出來,卻逐漸覺悟(becoming aware)其與我的關係。對我產生的意義,並不是他說的,而是我自己覺察的(Buber, 2002)。近年由於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的發現,了解這種由對外物的觀察而誘發的運動神經系統的激活,產生語言的理解、情感的感同身受等,以及在想像中模擬現實世界事件以促進學習的神經生物學基礎(葉浩生、肖珊珊,2017)。在專業問題研討課程,由參與觀察與對話的自我觀照,產生自在自得與人文關懷的生命轉化(第二章)。透過師生對話,共同探究存在與理解真實,不僅是學生的學習,也是教師的成長。
體知學習,除了促成聞見之知,更能發展德性之知。聞見之知,是通過感官而獲得有關外界的知識;德性之知,則有「體之於身」的實踐意義,是從事道德實踐必備的自我意識;聞見之知可真可假,德性之知是真知,但需要反躬修己的學思功夫(杜維明,2002)。身體與世界互動產生的情感,引導仁義禮智的行為;當欲望超出人之常情,則是人可以用功的地方,即由「喜怒哀懼愛惡欲」的情感身體經驗,檢視自己理知的欲望、價值觀,減少不合宜的行為舉止(第十六、十七章)。
培養學生德性之知的方式很多,其中最有效的是小團體對話(Maslow, 1993b)。在團體中,人可以暫時遠離身處的現實限制,善用五感以及直覺,透過團體的體驗與議題的引導,進行反思學習,由別人身上發現未被意識到的自己,形成融合多方投入的理解或行動模式。學習者不再是只依「聽講—記憶」的模式學習,而能由自己的實踐與反思獲取知識,並賦予知識意義,充實專業素養(蔣欣欣,2015)。擺脫「表面上看來謙遜有禮、內在卻是死寂的空虛。」的假我(false self),邁向能自發且自由地感覺,能夠創造、能夠與人靠近的真我(true self)(Winnicott, 1971),進而提升超越個人之靈性層次。在閱讀詩作的對話課程,經歷著認同、淨化、領悟,陶養其人性情懷(第六章)。在護理導論課程,學生由訪談護理人員、生病的人,以及小組討論,好奇地主動探索知識、經驗世界,最後發現自己生命中的重要價值(第五章),這種來自觀看、觀察、實作與覺悟的學習,將永遠長存於其肌理筋骨。
人本導向的小組教學
人本導向的小組教學,是源自尊重身體主體性的體知學習,以及關注學習氛圍的對話教育,經由對話省察彼此的學習或生活,改變對自己經驗的體認,提升自我意識。採用自由談的小組教學,是營造一個自然的學習氣氛,以整體性的身體感覺進入深度與廣度的生命空間,容易促成自我生命的醒覺與開展,陶養人性情懷,以及體認普遍人性而生成對他者的人文關懷。
學習,不僅是閱讀、觀看或聆聽,而需要透過自身與外在他者的對話,小組教學使人由客觀界、主觀界,進入超主客界,體認自身的存在處境,開發心靈境界(柯慶明,2000;唐君毅,1986)。
客觀界,指顯現的自身與外界事物。我們的人性,通常不在抽象的思維中反應,而總是在面對具體的生存情境之際才會自然流露與表現。「團體就是讓我們不斷的有機會說,與聽別人說。」在團體的聽與說之間,引動個人的情感(emotion),包括身體感受(feeling)與情緒經驗(mood)。「感受」是鮮明的、短暫的前景,「情緒」是模糊的、潛藏的背景,與情境及個人成長經驗有關的氛圍,最初是說不清楚。這些情感經驗,成了我們生命反應的某種表白,引發我們對情境狀況的覺知,由瑣碎浮表、片段雜亂的知覺,進入個人的意識層面,給予關注,並試圖找到統一它們的內在基點。
主觀界,是開始清楚而真切的反觀自身,認識到自己與情境之間深切的連結,覺察到自身的情感,包括具體的感受與理不清的情緒,有人形容「這團體就像是一次旅行,我們坐上一列火車,坐在靠窗的位置,放眼望去,許多景色映入眼簾,很多畫面會勾勒起從前很多回憶(人、事、物)。」此單純自明的純粹感受性,有時可以訴說;有時,只是「有所感」,卻說不清楚。經由對話,話語被喚出,說出那其實已經存在著想要表達的情緒。
超主客界,則是思緒跳脫原有的思維與情感,與原有現實功利的態度暫時隔絕,對生活取得美感的距離與觀照的高度,穿梭於不同時空的觀看,體驗到心靈的真正開展擴大,邁向一種生命智慧的體驗。「團體中的時空與感受是現在,記憶則可能推回從前,但這一切,竟會賦予當下的自己,有不太一樣的感受,但最重要的,是自己到底得到什麼,學到什麼。」新的感知,陶養著對人性的了悟,以及對情境的容納,此心靈境界的轉折是經由團體中語言與非語言的表達,及其深層意涵的流動。
自由談的對話團體
自由談的小組學習,如同日常幾個好友閒話家常,但卻將話語當成思考對象,並發覺其所蘊含的問題意識。形式上是教師帶領6至8位學生,以正向的互賴關係,面對面的互動。注重此時此刻(here and now)的經驗流動,以自由表達營造無害、去擾、包容、祥和之氣氛,引發主動及創意,得以共同探究生活世界。透過語言捕捉複雜的心靈活動,藉由內在深刻的人性,反映外在世界的廣大豐富。自由談對話,雖源自英國團體分析學派(蔣欣欣,2013a;Foulkes, 1991),但其注重取消主體有為的操控欲望,調整身體與他者(物)共在的柔和氣氛,一如莊子的物我相遊,讓人卸除對物的機心目的,彼此共在而相忘相遊(賴錫山,2015)。其討論方法是:
1. 學生彼此面對面圍坐一圈,沒有既定流程的團體。
2. 沒有預定的團體討論主題,是以學生當時所想要談的議題為主,讓團體自然進展。
3. 學生可以自由自在的表達自己想說的話,並且自然地注意其他人所說的。
這種團體重視自發性,需要運用身體的五感,保持身心放鬆以維護清明的知覺。特別是在團體的前十分鐘,鼓勵學生聆聽自己內在的感知而加以陳述,這時,不必對所聽到的話語做回應,只是專注地聽自己與說自己(第十一章)。這種自說自話,是引導其聆聽內在真誠的聲音,同時基於話語的不被預先設定,具有不可預期的開放性,以促發新經驗的產生。
團體是個有機體,自有其內在的動力。在團體互動中,人不是主體,話題才是主體,話題是藉著身體自我和情境的呼應、感應而生的。對話者無法預知他將會提出什麼問題,只能面對課題。等待問題降臨,再整理它、提出它(陳榮華,1998)。一位團體的觀察者,提到,由自身出發的自由談,先不對話,這段時間的「聆聽」很重要,聆聽自己、聆聽他人,然後再啟動「說」(宜芳,2021課堂觀察)。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小組對話:教學與研究的圖書 |
 |
小組對話:教學與研究 作者:蔣欣欣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1-10-10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25 |
二手中文書 |
$ 405 |
健康醫療 |
$ 418 |
中文書 |
$ 428 |
教育學群 |
$ 428 |
教育 |
$ 428 |
醫療保健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小組對話:教學與研究
本書介紹小組對話的教學實踐與研究案例,主要是以對話教育、體知學習,以及團體分析的自由談,營造教學對話的空間,藉著這些實作的教學研究案例,說明小組教學的各種形式、學習內容以及實踐智識。本書分為三個部分,包括教學篇、對話篇、體知篇,每篇各有6章,全書包括導言共計19章。
適用對象: 教師、健康照護專業人員、教育心理之教師與學生
作者簡介:
蔣欣欣
陽明大學臨床護理研究所教授,曾任陽明大學護理學院副院長、中華團體心理治療學會理事長,以及國際團體心理治療學會(IAGP)理事。擔任教職至今逾40年,致力於融合東西方哲學於臨床照護,並將團體心理治療的理論與實務,用於提升護理倫理教育之內涵,以促進人性化照護之實踐。已於國內外雜誌發表逾百篇相關論文,並編著《護理照護的倫理實踐》、《團體心理治療》、《質性研究》、《護理與社會》等書。
章節試閱
任何一個年代,教師們都肩負者生命價值傳承的使命。然而,如何傳承?
對人心靈的看法影響我們對教育的理念與作法,西方學者指出如果相信「人心為白紙」,白紙需要外力介入才能產生色彩,就會認為教學的任務是促進學生思維能力的發展和客觀知識的獲得,類似於計算機似的輸入、作用、輸出過程;如果相信「人心像是一顆種子」,而種子裡面蘊含它成長所需要的養分,則重視提供滋養的環境,讓人擁有於內心世界與自己相處、以及面對外在世界的生活能力。中華文化的道統裡,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認為人本身就具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
對人心靈的看法影響我們對教育的理念與作法,西方學者指出如果相信「人心為白紙」,白紙需要外力介入才能產生色彩,就會認為教學的任務是促進學生思維能力的發展和客觀知識的獲得,類似於計算機似的輸入、作用、輸出過程;如果相信「人心像是一顆種子」,而種子裡面蘊含它成長所需要的養分,則重視提供滋養的環境,讓人擁有於內心世界與自己相處、以及面對外在世界的生活能力。中華文化的道統裡,孟子主張人性本善,認為人本身就具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自序
服務教職四十餘年,深感小組教學實踐著「育才先育人」的信念,在每個教學現場,持續累積著生命交會的感動,化為篇篇的文字。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撐自己這樣的走下去?
服務生涯裡,經歷兩次臺灣護理教育的變革,第一次是1980年代於國防醫學院將分科護理課程的各科護理學,改為統合性課程的護理學I、II、III。第二次是2001年於陽明大學實施的問題導向小組教學,見證當前大學護理教育的發展脈絡。之後,擔任臺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科技部及教育部計畫的複審委員,了解臺灣醫護教育的研究取向。教學方面,除了參與學士、碩士及博士班心理...
服務教職四十餘年,深感小組教學實踐著「育才先育人」的信念,在每個教學現場,持續累積著生命交會的感動,化為篇篇的文字。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撐自己這樣的走下去?
服務生涯裡,經歷兩次臺灣護理教育的變革,第一次是1980年代於國防醫學院將分科護理課程的各科護理學,改為統合性課程的護理學I、II、III。第二次是2001年於陽明大學實施的問題導向小組教學,見證當前大學護理教育的發展脈絡。之後,擔任臺灣護理教育評鑑委員、科技部及教育部計畫的複審委員,了解臺灣醫護教育的研究取向。教學方面,除了參與學士、碩士及博士班心理...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目錄
自序
各章出處
第一章 導言
教學篇
第二章 生命的成長
第三章 小組教學的學習內容
第四章 對話與關懷
第五章 反思學習
第六章 閱讀療法
第七章 教學的反思實踐
對話篇
第八章 醫護教育的夥伴關係
第九章 小組教學的自由談
第十章 團體中的話語
第十一章 自由談的體驗與導引
第十二章 帶領者的教育訓練
第十三章 參與者的全人體驗
體知篇
第十四章 臨終照護的情緒工作
第十五章 人性化照護的感通
第十六章 照護行動的身體感
第十七...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