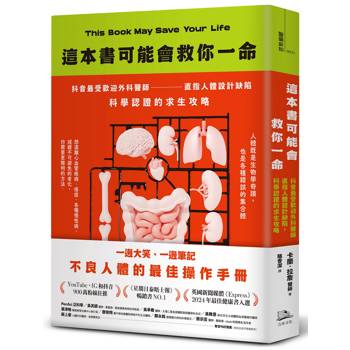在素有「詩國」美譽的中華文化國度裡,「詞」不啻為文學史上一顆耀眼的明珠。
隋唐以來,一種參雜胡樂的新興「燕樂」(宴樂)逐漸風靡;不同於廟享儀式中「雅樂」的典雅中正,是一種節奏多變、樂曲優美而富於新鮮感的新聲。漸漸的,中晚唐後,「由聲以定辭」、「依聲填字」的文學新體裁――詞,便以其宛轉合度的音樂性、錯綜美感的長短句以及細膩深曲的抒情特質而興盛,並在宋朝達到「凡有井水處即能歌」的盛況。至此,「宋詞」成為足與「漢賦」、「唐詩」相媲美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代表,並成就了韻文史上「詩、詞、曲」鼎立的不朽盛事。
本書依據詞的發展脈絡分章闡述,依序為:詞的整體觀,唐、五代篇,北宋篇,南宋篇,南宋遺民篇,餘響篇等。內容涵蓋:詞的起源、詞性、詞體發展、各時期傑出的詞人與詞作……不一而足。期待讀者翻開文學史扉頁時,在「詞」的這一章,能夠藉由本書窺得其中奧妙與菁華。讓這些悽惻怨悱、吞天洗月、落筆絕塵、相思無盡、山長水闊、一箭風快……的詞作,洗滌塵世紛擾,並從中得到處世智慧與蜿蜒無盡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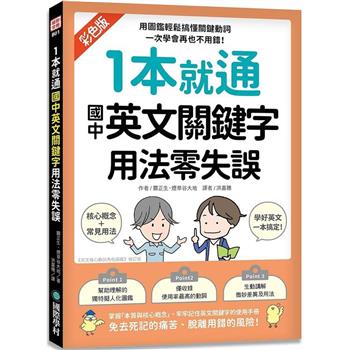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