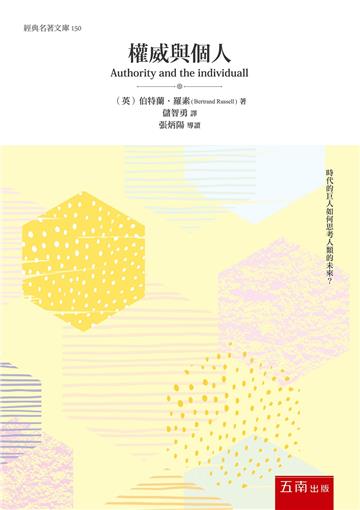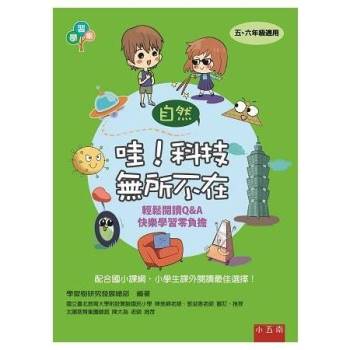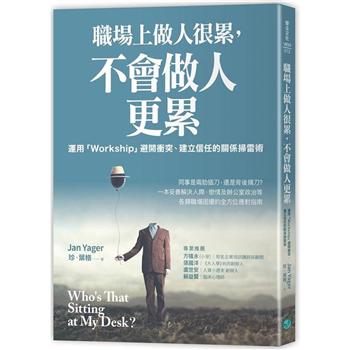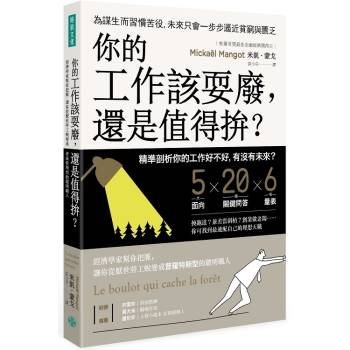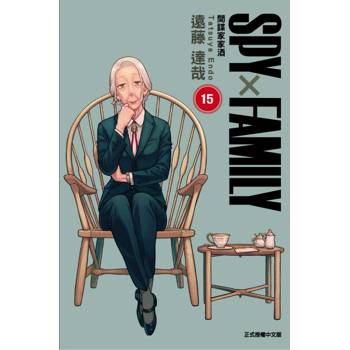時代的巨人如何思考人類的未來?
羅素的這本小書是他在1948年英國廣播公司六次演講的結集。發表於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末,肇因於羅素憂慮「個人自由往往隨著工業主義的增強而減少」,從而建議人們思考如下問題:「我們怎樣才能把進步所必須的個人首創精神的那種發揮程度與生存所必須的凝聚力的牢固程度結合起來。」主要為考察社會與個人創造性。內容包括:社會凝聚力與人性、社會凝聚力與政府、個性的作用、技術與人性的衝突、與主動性:它們各自的領域以及個人倫理與社會倫理。由於書中討論的主題本身對於人類社會具有恆久的性質,在今天仍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權威與個人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95 |
西方哲學 |
$ 195 |
哲學 |
$ 205 |
Books |
$ 234 |
英美哲學 |
$ 234 |
社會人文 |
$ 242 |
中文書 |
$ 242 |
Books |
$ 247 |
Books |
$ 247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權威與個人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二十世紀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歷史學家,無神論或者不可知論者。羅素被認為是與弗雷格、維根斯坦和懷特海一同創建了分析哲學。他與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對邏輯學、數學、集合論、語言學和分析哲學有著巨大影響。1950年,羅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多樣且重要的作品,持續不斷的追求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作品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學史》、《數學原理》、《物的分析》等。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二十世紀英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歷史學家,無神論或者不可知論者。羅素被認為是與弗雷格、維根斯坦和懷特海一同創建了分析哲學。他與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對邏輯學、數學、集合論、語言學和分析哲學有著巨大影響。1950年,羅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表彰其「多樣且重要的作品,持續不斷的追求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作品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學史》、《數學原理》、《物的分析》等。
目錄
導讀
調和權威與個人創立一個美好世界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退休教授 張炳陽
卷首語
導言
第一講 社會凝聚力與人性
第二講 社會凝聚力與政府
第三講 個性的作用
第四講 技術與人性的衝突
第五講 控制與主動性:它們各自的領域
第六講 個人倫理與社會倫理
譯後記
羅素作品譯名對照表
譯名索引
羅素年表
調和權威與個人創立一個美好世界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退休教授 張炳陽
卷首語
導言
第一講 社會凝聚力與人性
第二講 社會凝聚力與政府
第三講 個性的作用
第四講 技術與人性的衝突
第五講 控制與主動性:它們各自的領域
第六講 個人倫理與社會倫理
譯後記
羅素作品譯名對照表
譯名索引
羅素年表
序
序
在準備這些演講的過程中,不僅在細節方面,而且在總體的觀念以及把它們應用於當前的境況方面,我一直得到我的妻子派特麗夏·羅素的至關重要的幫助。權威與個人導言導言
在將近50年的歲月裡,這個導言寫於1995年,距裡斯講座開辦已近50年。——譯注裡斯講座在現代英國文化生活中一直享有獨特的地位。講座按照慣例在深秋和初冬時節舉辦,它們是向英國廣播公司的創始負責人約翰·裡斯約翰·裡斯(1889—1971),1922年任英國廣播公司經理,1927—1938年任董事長。——譯注表示敬意。裡斯傲慢、專橫、具有報復心,是一個專制的管理者和讓人畏懼的人物,他既極大地挫傷過下屬以及主管們的情感,又非常成功地創立了英國最令人讚賞和最持久的機構之一。裡斯堅持認為,英國廣播公司應讓它的聽眾享受到最傑出的演講者對最廣泛的主題所做的論述。裡斯講座忠實地貫徹執行了上述主張,其挑選演講者的標準始終是,他們興趣廣泛,精通自己講述的論題,以及能夠不費力氣地使困難的論題對廣大聽眾變得易於理解。因此,從1948年起,英國公眾得以受到人類學家和動物學家、天文學家和外交家、藝術史家和經濟學家、神學家和企業巨頭們的啟迪。
裡斯講座要成為一項非常持久的事業,這無疑是講座的創辦者英國廣播公司董事會的雄心所在——即便老實說,這並不是它的期望。對董事會來說,在戰後調整時期艱難的早期歲月裡,創辦這一講座並不僅僅是為了向裡斯致敬,更重要的,是為了促進對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的理解,這是一個由工黨政府和原子能、歐洲復興和超級大國競賽、帝國主義挑戰和經濟衰退構成的世界。他們雄心勃勃,確實想創辦一個一年舉辦一次的廣播版的吉福德講座吉福德講座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神學講座。——譯注——一個由英國最富原創性的思想家和最有創造力的研究者主持的、面向廣大聽眾的、通俗易懂的講座。為了進行首場該系列講座,並由此不但定下講座的調子,而且確立講座的信譽,董事會邀請了英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伯特蘭·羅素。
20世紀英國文化和思想精英所寵愛的這樣一種地位,既令羅素感到愉快,同時也使他感到新奇。在羅素特別漫長的一生中,其學術、政治和個人聲譽一直都(並且將繼續)劇烈起伏,而緊隨二戰結束之後的那個10年,是他具有公共威望的少有的時期。1872年,羅素生於一個非常顯赫而且穩定的英國輝格党貴族世家,在大戰爆發前的20年裡,他就已經獲得了思想上的聲望。在劍橋專門為他設立的邏輯學和數學哲學講席上,他有著20年不間斷的思想成就。其間羅素的著作包括《論幾何學基礎》(1897)、《對萊布尼茲哲學的批評性解釋》(1900)、《數學的原理》(1903)、《哲學問題》(1912)、《數學原理》(3卷本,1910—1913),以及超過30篇在英國、法國、義大利和美國刊物上發表的重要論文,他的名氣已經很大了,不僅是一位擁有罕見的複雜技術以及甚至更罕見的文體鑒賞力的令人肅然起敬的邏輯學家,而且是一項新的並且強有力的思想推理技術——分析哲學——的主要宣導者。一戰前夕,羅素確實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了英語世界中最著名也最有影響的哲學家。
然而,大戰的爆發改變了羅素的生活;如果說他的哲學著作給他帶來了名望的話,大戰則使他聲名狼藉。儘管羅素從來不是一個典型的遠離塵世的劍橋教書匠——他在1903年的關稅改革運動以及始於1907年的婦女選舉權運動中都很活躍,並且在1910年發起了一場不成功的議會競選運動——但羅素依然不是一個公共人物。然而隨著1914年夏英國不屈不撓地邁向戰爭,羅素首先投身于中立運動,隨後則致力於反戰運動——演講、寫作、組織協調和出謀劃策。羅素並不是和平主義者,但他堅信,這場戰爭——而不是所有的戰爭——是一個錯誤;確實,這場戰爭冒犯了他所有的政治直覺和道德原則。隨著戰爭深入,英國的參與擴展了,羅素的反對也加深了,他反對粗魯地對待有良知的反戰者,反對壓制公民的自由權,也反對英國指揮官的鋪張浪費。這一反對是尖銳的、不屈不撓的,也是非常不受歡迎的,這是羅素生命中獨特的經歷;不但各方面都情緒激憤,羅素因此而疏遠了朋友,惹惱了同盟者,也激怒了當局,而且他意識到,戰爭確實受到了他的絕大多數同胞的支持,這使他震驚並感到迷惑。解釋戰爭何以被接受——說明英國公眾的好戰和仇外,並探究他們為什麼容易受到新聞巨頭誇大宣傳的影響以及他們對於政府集權趨勢的漠不關心——在1918年以後的歲月裡成了羅素核心的思想和政治工作。
兩次大戰間的年月由此目睹了一個非常不同的羅素,他投身於一種非常不同的工作當中。由於自覺地決心成為20世紀的伏爾泰,羅素立刻——並且常常以一種很公開的方式——投身到範圍極其廣泛的各種論題的討論當中,努力重建社會和使個人重獲新生,以避免再一次的軍事災難。演講、寫作、教書、旅行,羅素所派出來參戰的並不是單個的探子,而是言語的大軍——涉及政治理論[《自由之路》(1918)和《權力論》(1938)全名為《權力:一個新的社會分析》(Power,a New Social Analysis)。——譯注],涉及經濟變遷[《工業文明的前景》(1923)],涉及歷史[《自由與組織1814—1914》(1934)],涉及亞洲的未來[《中國問題》(1922)],涉及俄國[《布林什維主義的實踐和理論》(1920)],涉及教育[《論教育》(1926)以及《教育和社會秩序》(1932)],涉及婚姻和性[《婚姻與道德》(1929)],涉及數學[《數學哲學導論》(1919)],涉及法西斯主義[《用什麼方法去爭取和平?》(1936)],涉及科學[《原子初步》(1923),《伊卡羅斯》(1924)全名為《伊卡羅斯或科學的未來》(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譯注以及《科學世界觀》(1931)],涉及大眾哲學[《心的分析》(1921)和《哲學概要》(1927)],以及涉及宗教[《我相信什麼?》(1925)]。儘管其中的很多著作和大多數作為補充的文章生命力並不長久,這些作品依然影響了廣泛的讀者,並且進一步加劇了羅素的惡名;確實,儘管他關於宗教、倫理和性的開明觀點吸引著年輕、獨立自主和自由思考的人,它們卻同時冒犯了閒適、因循和墨守成規的人。
二戰爆發之際,羅素正在美國教書。他渴望回到英國,並參與到對他廣受歡迎的作品的辯論之中,而當時的英國政府卻一直禁止他回國,政府實在太樂於記著他早期的反戰觀點和行為了,卻不相信他當前的——也是相當誠懇的——關於支持對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鬥爭的聲明。他由此在美國一直待到1944年夏天——寫作,演講,教書,並且為《西方哲學史》(1945)——這將成為他最廣為閱讀的作品——準備大量的手稿。
羅素後來不僅回到了英國,而且回到了劍橋,不僅回到了劍橋,而且回到了三一學院——19世紀90年代他曾是這裡的一名大學生,20世紀頭10年則是一名教師,1916年也正是在這裡,他被不能容忍他的反戰觀點的大學董事會所驅逐。受他原來的大學朋友而現在是三一學院院長的G.M.特裡維廉的邀請,羅素認可並且愉快地接受了提供給他的研究員職位,因為這是對先前那些不公正的一個糾正,也是對他持續作為20世紀一位傑出哲學家的一個證明。在盟軍入侵法國的直接餘波和打敗德國的最後階段回到英國,回到三一學院,回到牛頓所擁有的房間牛頓(1643—1727)1667年被選為劍橋三一學院的研究員。羅素回到三一學院後,一直住在牛頓住過的房子裡(參見[英]伯特蘭·羅素:《羅素自傳(第三卷)》,徐奕春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43拟44頁)。——譯注,對於羅素意味頗多,他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苦惱而悲觀地離開了英國——對英國外交和防禦政策的那些藉口滿懷憤怒,對國民政府在緩解彌漫性的社會和經濟苦難方面的無能和不爭充滿沮喪,並且對是否將他的孩子作為英國國民來撫養也猶豫不決。但是1944年,那一低迷、不真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緊接著的盟軍的凱旋、工党的勝利以及《西方哲學史》在出版上的成功都一道振奮了羅素的精神,並且使他天生的適應力和樂觀主義迅速成長起來。
在三一學院,羅素受到了老朋友們和那些少數未服兵役的學生們的熱烈歡迎。隨著戰爭的結束,以及緊接著的工党的勝利和《西方哲學史》的成功,羅素髮現自己已經被人們當成是名人。學院當局並不指望他去教書或者作演講,而羅素卻以一個72歲老人令人驚訝的活力和熱情投身到這兩項工作當中。讓他高興的是,他贏得了那些機敏而有悟性的聽眾。倫理學、認識論和哲學基礎等方面的導論性講座課程,使劍橋最大的報告廳爆滿。這些講座的要點出自他的《西方哲學史》(這本書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美國的講座的彙編)。羅素的講座是令人難忘的表演——深入淺出,機智詼諧,挖苦嘲諷,主題廣泛,插科打諢,充滿了活力,試圖立刻迷住聽眾,也試圖體現出哲學研究的道德嚴肅性和思想的高貴性。對他在劍橋的聽眾以及遍佈英語世界的讀者來說,羅素——約翰·羅素勳爵的孫子,以及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教子——看來不僅很快和英國政治與文化的偉大傳統建立了活生生的聯繫,而且也成為了戰勝法西斯惡魔並粉碎了納粹恐怖的西方文化的充分體現。羅素由此不被人們看作——他也不把自己看作——是一隻牛虻或者一個叛逆,反而被人們看作是為歡欣鼓舞的英國——她現在決心要在過去那些牢固而持久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增光添彩的人。
對羅素的獨特名望和他新的穩健風格的欣賞,很快就超越了劍橋,這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哲學史》不俗的銷售業績造成的——在經濟短缺的英國,它的銷量只是由於紙張的匱乏才受到了限制。羅素因此很快就發現自己成了英國議會以及外交部所鍾愛的一名演講者(這對任何一個生活在1916年的人來說都是不可想像的);接下來幾年,在它們的要求下,羅素遊歷了瑞士、挪威、德國和法國,以便就“文化與國家”以及“倫理和權力”這樣一些主題發表演講。
正是在恢復了名望的背景下,英國廣播公司發現了羅素。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社會絕對無法接受羅素,裡斯和他的繼任者也一直把羅素看作是一個充滿極端觀點的危險激進分子而加以回避。現在,羅素顯然更溫和也更值得信賴,於是1944年末,他受邀出現在大眾智囊節目英國廣播公司20世紀40年代播出的、邀請專家組成座談小組討論時事問題的一個節目。——譯注中。他的出場是如此成功,以至於他幾乎立刻被邀請就“文明的未來”這一論題發表廣播演講,並在隨後和J.B.S.霍爾丹、弗裡德里克·科普斯頓等一些知名人士展開辯論。讓英國廣播公司的策劃和導演高興的是,羅素被證明是一個近乎模範的廣播員——精確守時、見多識廣、生動活潑、富煽動性卻並不過激。到1946年底,英國廣播公司看來想要佔有他,1947年1月,羅素已抱怨操勞過度,“因為英國廣播公司極為喜歡我”。引自羅奈爾得·W.克拉克:《羅素傳》(倫敦, 1975年版),第496頁。——原注正是出於他的聲望——既包括演播室裡的聲望,也包括演播室外的聲望——他被邀請作為裡斯講座的開幕演講者。
在準備這些演講的過程中,不僅在細節方面,而且在總體的觀念以及把它們應用於當前的境況方面,我一直得到我的妻子派特麗夏·羅素的至關重要的幫助。權威與個人導言導言
在將近50年的歲月裡,這個導言寫於1995年,距裡斯講座開辦已近50年。——譯注裡斯講座在現代英國文化生活中一直享有獨特的地位。講座按照慣例在深秋和初冬時節舉辦,它們是向英國廣播公司的創始負責人約翰·裡斯約翰·裡斯(1889—1971),1922年任英國廣播公司經理,1927—1938年任董事長。——譯注表示敬意。裡斯傲慢、專橫、具有報復心,是一個專制的管理者和讓人畏懼的人物,他既極大地挫傷過下屬以及主管們的情感,又非常成功地創立了英國最令人讚賞和最持久的機構之一。裡斯堅持認為,英國廣播公司應讓它的聽眾享受到最傑出的演講者對最廣泛的主題所做的論述。裡斯講座忠實地貫徹執行了上述主張,其挑選演講者的標準始終是,他們興趣廣泛,精通自己講述的論題,以及能夠不費力氣地使困難的論題對廣大聽眾變得易於理解。因此,從1948年起,英國公眾得以受到人類學家和動物學家、天文學家和外交家、藝術史家和經濟學家、神學家和企業巨頭們的啟迪。
裡斯講座要成為一項非常持久的事業,這無疑是講座的創辦者英國廣播公司董事會的雄心所在——即便老實說,這並不是它的期望。對董事會來說,在戰後調整時期艱難的早期歲月裡,創辦這一講座並不僅僅是為了向裡斯致敬,更重要的,是為了促進對一個迥然不同的世界的理解,這是一個由工黨政府和原子能、歐洲復興和超級大國競賽、帝國主義挑戰和經濟衰退構成的世界。他們雄心勃勃,確實想創辦一個一年舉辦一次的廣播版的吉福德講座吉福德講座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自然神學講座。——譯注——一個由英國最富原創性的思想家和最有創造力的研究者主持的、面向廣大聽眾的、通俗易懂的講座。為了進行首場該系列講座,並由此不但定下講座的調子,而且確立講座的信譽,董事會邀請了英國最著名的公共知識份子——伯特蘭·羅素。
20世紀英國文化和思想精英所寵愛的這樣一種地位,既令羅素感到愉快,同時也使他感到新奇。在羅素特別漫長的一生中,其學術、政治和個人聲譽一直都(並且將繼續)劇烈起伏,而緊隨二戰結束之後的那個10年,是他具有公共威望的少有的時期。1872年,羅素生於一個非常顯赫而且穩定的英國輝格党貴族世家,在大戰爆發前的20年裡,他就已經獲得了思想上的聲望。在劍橋專門為他設立的邏輯學和數學哲學講席上,他有著20年不間斷的思想成就。其間羅素的著作包括《論幾何學基礎》(1897)、《對萊布尼茲哲學的批評性解釋》(1900)、《數學的原理》(1903)、《哲學問題》(1912)、《數學原理》(3卷本,1910—1913),以及超過30篇在英國、法國、義大利和美國刊物上發表的重要論文,他的名氣已經很大了,不僅是一位擁有罕見的複雜技術以及甚至更罕見的文體鑒賞力的令人肅然起敬的邏輯學家,而且是一項新的並且強有力的思想推理技術——分析哲學——的主要宣導者。一戰前夕,羅素確實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了英語世界中最著名也最有影響的哲學家。
然而,大戰的爆發改變了羅素的生活;如果說他的哲學著作給他帶來了名望的話,大戰則使他聲名狼藉。儘管羅素從來不是一個典型的遠離塵世的劍橋教書匠——他在1903年的關稅改革運動以及始於1907年的婦女選舉權運動中都很活躍,並且在1910年發起了一場不成功的議會競選運動——但羅素依然不是一個公共人物。然而隨著1914年夏英國不屈不撓地邁向戰爭,羅素首先投身于中立運動,隨後則致力於反戰運動——演講、寫作、組織協調和出謀劃策。羅素並不是和平主義者,但他堅信,這場戰爭——而不是所有的戰爭——是一個錯誤;確實,這場戰爭冒犯了他所有的政治直覺和道德原則。隨著戰爭深入,英國的參與擴展了,羅素的反對也加深了,他反對粗魯地對待有良知的反戰者,反對壓制公民的自由權,也反對英國指揮官的鋪張浪費。這一反對是尖銳的、不屈不撓的,也是非常不受歡迎的,這是羅素生命中獨特的經歷;不但各方面都情緒激憤,羅素因此而疏遠了朋友,惹惱了同盟者,也激怒了當局,而且他意識到,戰爭確實受到了他的絕大多數同胞的支持,這使他震驚並感到迷惑。解釋戰爭何以被接受——說明英國公眾的好戰和仇外,並探究他們為什麼容易受到新聞巨頭誇大宣傳的影響以及他們對於政府集權趨勢的漠不關心——在1918年以後的歲月裡成了羅素核心的思想和政治工作。
兩次大戰間的年月由此目睹了一個非常不同的羅素,他投身於一種非常不同的工作當中。由於自覺地決心成為20世紀的伏爾泰,羅素立刻——並且常常以一種很公開的方式——投身到範圍極其廣泛的各種論題的討論當中,努力重建社會和使個人重獲新生,以避免再一次的軍事災難。演講、寫作、教書、旅行,羅素所派出來參戰的並不是單個的探子,而是言語的大軍——涉及政治理論[《自由之路》(1918)和《權力論》(1938)全名為《權力:一個新的社會分析》(Power,a New Social Analysis)。——譯注],涉及經濟變遷[《工業文明的前景》(1923)],涉及歷史[《自由與組織1814—1914》(1934)],涉及亞洲的未來[《中國問題》(1922)],涉及俄國[《布林什維主義的實踐和理論》(1920)],涉及教育[《論教育》(1926)以及《教育和社會秩序》(1932)],涉及婚姻和性[《婚姻與道德》(1929)],涉及數學[《數學哲學導論》(1919)],涉及法西斯主義[《用什麼方法去爭取和平?》(1936)],涉及科學[《原子初步》(1923),《伊卡羅斯》(1924)全名為《伊卡羅斯或科學的未來》(Icarus or the Future of Science)。——譯注以及《科學世界觀》(1931)],涉及大眾哲學[《心的分析》(1921)和《哲學概要》(1927)],以及涉及宗教[《我相信什麼?》(1925)]。儘管其中的很多著作和大多數作為補充的文章生命力並不長久,這些作品依然影響了廣泛的讀者,並且進一步加劇了羅素的惡名;確實,儘管他關於宗教、倫理和性的開明觀點吸引著年輕、獨立自主和自由思考的人,它們卻同時冒犯了閒適、因循和墨守成規的人。
二戰爆發之際,羅素正在美國教書。他渴望回到英國,並參與到對他廣受歡迎的作品的辯論之中,而當時的英國政府卻一直禁止他回國,政府實在太樂於記著他早期的反戰觀點和行為了,卻不相信他當前的——也是相當誠懇的——關於支持對納粹德國和法西斯義大利鬥爭的聲明。他由此在美國一直待到1944年夏天——寫作,演講,教書,並且為《西方哲學史》(1945)——這將成為他最廣為閱讀的作品——準備大量的手稿。
羅素後來不僅回到了英國,而且回到了劍橋,不僅回到了劍橋,而且回到了三一學院——19世紀90年代他曾是這裡的一名大學生,20世紀頭10年則是一名教師,1916年也正是在這裡,他被不能容忍他的反戰觀點的大學董事會所驅逐。受他原來的大學朋友而現在是三一學院院長的G.M.特裡維廉的邀請,羅素認可並且愉快地接受了提供給他的研究員職位,因為這是對先前那些不公正的一個糾正,也是對他持續作為20世紀一位傑出哲學家的一個證明。在盟軍入侵法國的直接餘波和打敗德國的最後階段回到英國,回到三一學院,回到牛頓所擁有的房間牛頓(1643—1727)1667年被選為劍橋三一學院的研究員。羅素回到三一學院後,一直住在牛頓住過的房子裡(參見[英]伯特蘭·羅素:《羅素自傳(第三卷)》,徐奕春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43拟44頁)。——譯注,對於羅素意味頗多,他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苦惱而悲觀地離開了英國——對英國外交和防禦政策的那些藉口滿懷憤怒,對國民政府在緩解彌漫性的社會和經濟苦難方面的無能和不爭充滿沮喪,並且對是否將他的孩子作為英國國民來撫養也猶豫不決。但是1944年,那一低迷、不真誠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而緊接著的盟軍的凱旋、工党的勝利以及《西方哲學史》在出版上的成功都一道振奮了羅素的精神,並且使他天生的適應力和樂觀主義迅速成長起來。
在三一學院,羅素受到了老朋友們和那些少數未服兵役的學生們的熱烈歡迎。隨著戰爭的結束,以及緊接著的工党的勝利和《西方哲學史》的成功,羅素髮現自己已經被人們當成是名人。學院當局並不指望他去教書或者作演講,而羅素卻以一個72歲老人令人驚訝的活力和熱情投身到這兩項工作當中。讓他高興的是,他贏得了那些機敏而有悟性的聽眾。倫理學、認識論和哲學基礎等方面的導論性講座課程,使劍橋最大的報告廳爆滿。這些講座的要點出自他的《西方哲學史》(這本書本身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美國的講座的彙編)。羅素的講座是令人難忘的表演——深入淺出,機智詼諧,挖苦嘲諷,主題廣泛,插科打諢,充滿了活力,試圖立刻迷住聽眾,也試圖體現出哲學研究的道德嚴肅性和思想的高貴性。對他在劍橋的聽眾以及遍佈英語世界的讀者來說,羅素——約翰·羅素勳爵的孫子,以及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的教子——看來不僅很快和英國政治與文化的偉大傳統建立了活生生的聯繫,而且也成為了戰勝法西斯惡魔並粉碎了納粹恐怖的西方文化的充分體現。羅素由此不被人們看作——他也不把自己看作——是一隻牛虻或者一個叛逆,反而被人們看作是為歡欣鼓舞的英國——她現在決心要在過去那些牢固而持久的基礎上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增光添彩的人。
對羅素的獨特名望和他新的穩健風格的欣賞,很快就超越了劍橋,這很大程度上是由《西方哲學史》不俗的銷售業績造成的——在經濟短缺的英國,它的銷量只是由於紙張的匱乏才受到了限制。羅素因此很快就發現自己成了英國議會以及外交部所鍾愛的一名演講者(這對任何一個生活在1916年的人來說都是不可想像的);接下來幾年,在它們的要求下,羅素遊歷了瑞士、挪威、德國和法國,以便就“文化與國家”以及“倫理和權力”這樣一些主題發表演講。
正是在恢復了名望的背景下,英國廣播公司發現了羅素。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社會絕對無法接受羅素,裡斯和他的繼任者也一直把羅素看作是一個充滿極端觀點的危險激進分子而加以回避。現在,羅素顯然更溫和也更值得信賴,於是1944年末,他受邀出現在大眾智囊節目英國廣播公司20世紀40年代播出的、邀請專家組成座談小組討論時事問題的一個節目。——譯注中。他的出場是如此成功,以至於他幾乎立刻被邀請就“文明的未來”這一論題發表廣播演講,並在隨後和J.B.S.霍爾丹、弗裡德里克·科普斯頓等一些知名人士展開辯論。讓英國廣播公司的策劃和導演高興的是,羅素被證明是一個近乎模範的廣播員——精確守時、見多識廣、生動活潑、富煽動性卻並不過激。到1946年底,英國廣播公司看來想要佔有他,1947年1月,羅素已抱怨操勞過度,“因為英國廣播公司極為喜歡我”。引自羅奈爾得·W.克拉克:《羅素傳》(倫敦, 1975年版),第496頁。——原注正是出於他的聲望——既包括演播室裡的聲望,也包括演播室外的聲望——他被邀請作為裡斯講座的開幕演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