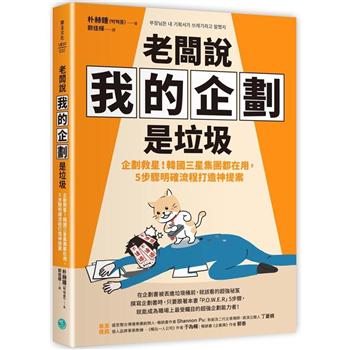★哲學是一個嚴肅工作的領域,哲學可以並且也必須在嚴格科學的精神中受到探討。
★哲學本質上是一門關於真正開端、關於起源、關於萬物之本的科學。
——胡塞爾
本書內容原是胡塞爾於1911年發表在德國哲學雜誌Logos上的長文,後由德國哲學家Wilhelm Szilasi於1965年編輯出版單行本,並給予高度評價:「這是一篇獨特的文獻,可以與笛卡兒的《談談方法》具有等同地位。」如今被視為是一份帶有胡塞爾簽名的「現象學宣言」。
德國哲學家Wolfgang Stegmüller也說:
「胡塞爾的研究對哲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於那些在原則上接受他的思想並將他的方法運用在其研究中的人來說,是一個無限廣闊的、新的工作領域的展現。對於對立陣營的哲學家來說,則形成了一種必然性,即:更清晰明白地闡明他們自己的立場,並使他們的論據的無懈可擊性與胡塞爾學說的高度科學水準相吻合。因此,像所有偉大的思想家一樣,胡塞爾對朋友和敵人都發揮了促使他們進行創造性活動的影響。」
胡塞爾在文中開宗明義寫道:「自最初的開端起,哲學便要求成為嚴格的科學」,但「哲學在其發展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能力滿足這個成為嚴格科學的要求」。基於此,胡塞爾意圖探究真正的科學意義,為哲學奠基。
胡塞爾努力在「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歷史科學)」之間找到哲學的位置。雖然在文中,現象學尚未帶有「先驗」現象學的標記(「先驗」一詞在這裡從未出現過),但胡塞爾的意圖在這裡已經十分清楚地揭露:透過對哲學的新論證,嚴格的哲學將以構造現象學的形態出現,它將為經驗的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奠定基礎,因為現象學探討的不僅是「意識構形的本質聯繫」(意識的「心理」方面),同時也探討「與它們相關的本質相屬的被意指性」(即被意識所構造出來的「物理」方面)。
此外,由於胡塞爾在文中公開揭露了他與狄爾泰思想的分歧,因而這篇文字對後人理解「現象學」與「解釋學」之間的關係也不無啟迪作用。
本書分為「自然主義哲學、歷史主義與世界觀哲學」兩部分,另附有「胡塞爾後來附加的邊注和補充、寫作背景、內容提要、內容分析、作者生平、相關文獻」提供讀者參考。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188 |
西方哲學 |
$ 198 |
德奧哲學 |
$ 198 |
📌哲學79折起 |
$ 208 |
Books |
$ 225 |
社會人文 |
$ 233 |
中文書 |
$ 233 |
Books |
$ 238 |
Books |
$ 23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4.8~1938.4.27)
出生於奧地利帝國摩拉維亞的普羅斯尼茲(今捷克普羅斯捷約夫),近代著名哲學家、現象學創始人,被譽為「現象學之父」。1883年獲維也納大學數學博士學位,後相繼任教於德國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及弗萊堡大學。
胡塞爾開創的「現象學」主張「回到事物本身」,以「意識」為思考特色,探討意識的本質及追問世界的本質,影響後世歐陸哲學走向深遠,開拓了新的哲學觀念——擺脫權威中介(以往的理論、前人的學說),直接、原本地把握真理自身。
主要著作有《邏輯研究》、《內時間意識現象學》、《現象學的觀念》、《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純粹現象學通論》等。
譯者簡介
倪梁康
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博士,國際著名現象學研究學者,曾任南京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人文學院院長、政治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現為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並任Husserl Studies期刊、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期刊編委及Max Scheler Gesellschaft諮議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方哲學,尤其是近現代哲學和現象學,近年亦涉及中西方意識哲學(包括心智哲學、心學、唯識學、心理哲學、心性論等)領域。
著有《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意識的向度》、《面對實事本身:現象學經典文選》、《自識與反思》等;譯有胡塞爾《邏輯研究》、《內時間意識現象學》、《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等。
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 1859.4.8~1938.4.27)
出生於奧地利帝國摩拉維亞的普羅斯尼茲(今捷克普羅斯捷約夫),近代著名哲學家、現象學創始人,被譽為「現象學之父」。1883年獲維也納大學數學博士學位,後相繼任教於德國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及弗萊堡大學。
胡塞爾開創的「現象學」主張「回到事物本身」,以「意識」為思考特色,探討意識的本質及追問世界的本質,影響後世歐陸哲學走向深遠,開拓了新的哲學觀念——擺脫權威中介(以往的理論、前人的學說),直接、原本地把握真理自身。
主要著作有《邏輯研究》、《內時間意識現象學》、《現象學的觀念》、《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純粹現象學通論》等。
譯者簡介
倪梁康
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博士,國際著名現象學研究學者,曾任南京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人文學院院長、政治大學哲學系客座教授,現為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並任Husserl Studies期刊、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期刊編委及Max Scheler Gesellschaft諮議委員。主要研究領域為西方哲學,尤其是近現代哲學和現象學,近年亦涉及中西方意識哲學(包括心智哲學、心學、唯識學、心理哲學、心性論等)領域。
著有《現象學及其效應——胡塞爾與當代德國哲學》、《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意識的向度》、《面對實事本身:現象學經典文選》、《自識與反思》等;譯有胡塞爾《邏輯研究》、《內時間意識現象學》、《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等。
目錄
導讀/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 倪梁康
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
自然主義哲學
歷史主義與世界觀哲學
附錄一 作者以後加入的邊注和補充
附錄二 全集本編者引論
附錄三 單行本編者內容提要
附錄四 單行本編者後記
附錄五 作者生平
附錄六 文獻選要
埃德蒙德‧胡塞爾年表
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
自然主義哲學
歷史主義與世界觀哲學
附錄一 作者以後加入的邊注和補充
附錄二 全集本編者引論
附錄三 單行本編者內容提要
附錄四 單行本編者後記
附錄五 作者生平
附錄六 文獻選要
埃德蒙德‧胡塞爾年表
序
序
〈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原是當代德國哲學家、現象學創始人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一八五九—一九三八年)於一九一一年發表在德國哲學雜誌《邏各斯》(第一期,第二八九—三四一頁)上的一篇長文(也被簡稱作「邏各斯文」)。這本中譯本是根據原文譯出,同時參照了之後收錄在由尼農(Thomas Nenon)和塞普(Hans Rainer Sepp)主編的《胡塞爾全集》第二十五卷:《文章與報告(一九一一 — 一九二一年)》(多德雷赫特等,一九八七年,第三—六二頁,以下簡稱「全集本」)中得到考證校定的同篇文字。胡塞爾之後在他的「邏各斯文」的私人自用本中還附加了一些評注性的文字,它們在全集本中作為「版本注」標出。這些評注性文字在中譯本中也一同被譯出,作為「作者後來加入的邊注和補充」附在正文的後面。同時一併譯出的還有《胡塞爾全集》第二十五卷編者所寫的與〈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文字產生背景有關的部分引論,題為「全集本編者引論」。
除此之外,中譯本還參照了威廉.斯基拉奇(Wilhelm Szilasi)於一九六五年所編的第一個單行本:《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法蘭克福/美茵,一九六五年,共一○七頁,以下簡稱「單行本」)。斯基拉奇為此單行本所撰寫的「內容分析」與「後記」也一同被譯出,以「單行本編者內容提要」和「單行本編者後記」(留有海德格痕跡的「後記」)為題附在正文後面。斯基拉奇還撰寫了「生平」和「文獻選要」附在單行本後,這後兩份文字雖然因為寫得時間比較早,不能反映當今胡塞爾研究的最新狀態,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尤其是作者本人在「生平」中加入了對胡塞爾的回憶,從而使之超出了單純資料的範圍,是故在此仍將它們譯出。
如此一來,書末的「附錄」便共有六篇,分別涉及:一、作者的修改意圖。二、文字的產生背景。三、內容提要。四、內容解釋。五、作者生平。六、有關文獻。
導讀
二十世紀初,胡塞爾《邏輯研究》兩卷本的發表(一九○○/○一年),使現象學得以突破並得以濫觴。這時胡塞爾在哲學界的聲譽斐然,他被看作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這從他的同時代人如狄爾泰(W. Dilthey)、那托普(P. Natorp)等,以及後一代人如海德格(M. Heidegger)、高達美(H.-G. Gadamer)等的評價與回憶中已可見一斑。現象學揭示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如列維納斯(E. Levinas)所說,這個領域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思辨目光所無法達及的。現象學的意向分析和描述方法幾乎使現象學成為一門與邏輯學或心理學相並列的特殊學科,甚至在今天通行的學科分類中還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影響的存在。
在《邏輯研究》發表的同一年,胡塞爾在一封信中預告說:「十年後再出一卷新的!」果然,在此後的十年裡,胡塞爾基本上是筆耕不輟。直到一九一一年,他才應里克特(H. Rickert)之約而拿出〈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我們在後面斯基拉奇所寫的胡塞爾「生平」中可以讀到:「在《邏輯研究》發表後處在顯赫聲譽之中的胡塞爾,沉默了十年之久,爾後才認為〈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值得發表,這個事實賦予了這篇論文無法充分估量的重要意義。」如今它基本上已被看作是一份帶有胡塞爾簽名的「現象學宣言」。
〈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在當時思想界所產生的影響至少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
從批判性的角度來看,在《邏輯研究》完成了對心理主義的有力抨擊之後,〈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仍然需要在兩條戰線上作戰:一方面是與自然主義,另一方面是與歷史主義。前者主要表現在當時盛行的實驗心理學的各種學說之中,後者則主要是指為狄爾泰等人所宣導的歷史學派。胡塞爾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邏輯研究》中對心理主義批判的延續,他仍然堅持不懈地揭示這些學說的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之最終結局。而這個結局對於當時的自然主義與歷史主義來說並非是不言自明的。對於胡塞爾在這方面的努力,非現象學哲學家科拉克夫斯基(L. Kolakowski)曾確切地評價說:「胡塞爾比任何一個人都更多地迫使我們認清知識的窘迫境況:要麼是澈底的經驗主義連同其相對主義、懷疑主義的結論,它被許多人看作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不能被接受的,並且事實上會給我們的文化帶來毀滅的立場;要麼就是先驗主義的獨斷論,它實際上無法論證自身,並且最終仍然是一個隨意性的決定。我不得不承認,儘管最終的確然性是一個在理性主義範圍之內無法達到的目標,但如果沒有那些不斷努力試圖達到這個目標的人們,我們的文化就將會是貧乏而可憐的。而且,如果我們的文化完全落入懷疑主義者們的手中,那麼它將幾乎無法繼續生存下去。我相信,人類的文化永遠不可能達到對它的各個繁雜而不統一的組成部分的完善綜合。然而,恰恰是它的各種成分的不統一性才有助於它的豐富多采,而使我們的文化得以保持其生命力,與其說是各種價值之間的和諧,不如說是各種價值之間的衝突。」實際上,許多當代人之所以能夠從容地遊弋於相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夾縫之間,既帶有懷疑主義的警覺,又仍抱有對健康的理性的最終信念,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胡塞爾的孜孜求索。
除此之外,由於胡塞爾在〈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中公開揭露了他與狄爾泰思想的分歧,因而這篇文字對後人理解現象學與解釋學之間的關係也不無啟迪作用。
從建構性的角度來看,可以籠統地說,在《邏輯研究》中,胡塞爾試圖將哲學定位於邏輯學和心理學之間,而在〈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中,他努力在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歷史科學)之間找到哲學的位置。雖然在這篇文章中,現象學尚未帶有「先驗」現象學的標記—「先驗」一詞在這裡從未出現過—,但胡塞爾的意圖在這裡已經十分清楚地揭露:透過對哲學的新論證,嚴格的哲學將以構造現象學的形態出現,它將為經驗的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奠定基礎,因為現象學所探討的不僅是「意識構形的本質聯繫」(意識的「心理」方面),同時也探討「與它們相關的本質相屬的被意指性」(即被意識所構造出來的「物理」方面);這兩個研究方向(所有的意識—被意指者)在他兩年後發表的《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第一卷中也被稱作「意向活動」(Noesis)和「意向對象」(Noema)。所以,〈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實際上已含有胡塞爾先驗構造現象學的第一次公開預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日後曾合理地指出,這篇文章「透過《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念》才獲得了對其綱領性論題的充分論證」。
值得一提的是:對胡塞爾在文章中所宣示出的這種努力趨向,海德格既表示贊同,也持有批評,他贊同胡塞爾所提出的「面對實事本身」的口號,贊同「研究的動力必定不是來自各種哲學,而是來自實事與問題」的主張,贊同現象學的直觀性原則與中立性原則。但他拒絕對「實事本身」作「意識的主體性」的理解,並且認為胡塞爾在此文中表現出向近代哲學,尤其是向康德主義的轉向,從而悖離了現象學的原則,放棄了對思的實事(原現象、原實事)的真正思考—對此,讀者可以對照胡塞爾的原文而得出自己的評價。
這裡無須再重構胡塞爾在上述兩個方面(批判性方面和建構性方面)的論述。讀者也許可以在正文中完整地讀到它們,或者可以在後面的「單行本編者內容提要」以及「單行本編者後記」等附錄中獲得對它們的大致了解。
需要強調的是胡塞爾的哲學觀。根據胡塞爾本人的回憶,他首先是在布倫塔諾(F. Brentano)的講座中獲得一個堅定的信念,這個信念使他有勇氣將哲學選擇為終生的職業:「哲學也是一個嚴肅工作的領域,哲學也可以並且也必須在嚴格科學的精神中受到探討。」這個信念不僅時常在他的研究手稿中出現:「哲學就是指向絕對認識的意向」,而且也在〈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中得到第一次公開的展示:「哲學本質上是一門關於真正開端、關於起源、關於萬物之本的科學」。可說胡塞爾這一生從未放棄過這個哲學觀。
將這個哲學觀加以展開,便意味著:一方面,向最終論證、最終奠基的回溯被理解為向認識主體的「意義給予」之成就的回溯,這種回溯是直接進行的,是自身負責的,任何間接的中介都必須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在獲得了經過最終論證的真理之後,哲學的任務還在於,將這種真理付諸實踐並且根據這種真理而承擔起主體性的責任與義務,這也是一門哲學倫理學和價值論的中心任務。在對哲學的這一理解中無疑包含著胡塞爾對理論與實踐的奠基關係的理解。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凡略曉當今世界「哲學行情」的人都會認為這種哲學觀已經屬於過去,當代人會樂於坦然地面對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指責。雖然各種不同派別的哲學思潮如今還在「理性」或「合理性」的整體標題下進行著各種獨白或對話,但「告別原理」,亦即告別邏輯中心主義意義上的理性,已經成為或多或少可以被一致接受的口號,世界不再被視作一個可以根據某個或幾個公理而推導出來的統一而有序的系統。笛卡兒曾在他的時代以「有序的」哲思者作為其沉思對話的基本前提對象,時至今日,「有序」已經不再成為哲學思考的公認標準。「有序」連同「無序」一起,被一些哲學家視為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兩大危險。胡塞爾所做的那些對心理主義、自然主義、歷史主義等各種形式的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的批判,已經明顯與流行意識相悖,而他對確然性之苦苦追求,更是被視為不明生活形式和價值系統之繁雜與間斷的真諦。
然而,就像蘇格拉底或康德至今對當代人所留下來的影響一樣,今天仍然有人——譯者也算是其中之一 ——不懈地在胡塞爾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寶庫中尋找精神生活的動力或支點,究其原因至少可以找到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雖然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仍然還是一個「無限遙遠的點」,胡塞爾的哲思方法卻仍然直接而具體地向我們指示著嚴格性的實例。就面前的《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而言,儘管它在胡塞爾的現有文獻中屬於綱領性的方法論述,本書單行本的編者斯基拉奇因而將它比作笛卡兒的《談談方法》,但即使在這裡也可以處處感受到胡塞爾現象學論述和操作的嚴格性。另一位非現象學的哲學家施泰格繆勒(W. Stegmüller)也曾公正地承認:「胡塞爾的研究對哲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於那些在原則上接受他的思想並將他的方法運用在其研究中的人來說,是一個無限廣闊的、新的工作領域的展現。對於對立陣營的哲學家來說則形成了一種必然性,即:更清晰明白地闡明他們自己的立場,並使他們的論據的無懈可擊性與胡塞爾學說的高度科學水準相吻合。因此,像所有偉大的思想家一樣,胡塞爾對朋友和敵人都發揮了促使他們進行創造性活動的影響。」對於施泰格繆勒所做的這個特徵描述,讀者可以從〈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一文的字裡行間獲得直接的感受。
但比他的嚴格方法影響更為深遠的,或許是胡塞爾在理論研究方面的執著精神。斯基拉奇認為,「胡塞爾的偉大從根本上帶有這樣一種特徵:他能夠長達數十年地以一種頑強的精神,並且在一種寧靜退隱的狀態下,一再地奉獻於新的問題。」這種甘於寂寞的個性,恐怕是每一個「理論人」都應具備的一個基本素質前提。理論研究者應當可以看到:他們的宿命就在於追求獨立的思想而避開流行的時尚。胡塞爾在世紀初所呼籲的「我們切不可為了時代而放棄永恆」,與王元化在二十世紀末一再宣導的「為學不做媚時語」,實際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過強的功利目的和實用心態或許是中國近現代學術困境的一個主要根源,正如文德爾班(W. Windelband)所說:「知識的金果只有在不被尋求的地方才能成熟。」從近年來學術研究的整個趨勢來看,胡塞爾在這篇文章中所做的警告在今天仍然有效:「正是在一個實踐動機超強地上升的時代裡,一種理論的本性也可能會比它的理論職業所允許的更為強烈地屈從於這些實踐動機的力量。但在這裡,尤其是對我們時代的哲學而言,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危險。」就此而論,《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可能會給我們的學術研究帶來一定的啟發與教益。
〈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原是當代德國哲學家、現象學創始人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一八五九—一九三八年)於一九一一年發表在德國哲學雜誌《邏各斯》(第一期,第二八九—三四一頁)上的一篇長文(也被簡稱作「邏各斯文」)。這本中譯本是根據原文譯出,同時參照了之後收錄在由尼農(Thomas Nenon)和塞普(Hans Rainer Sepp)主編的《胡塞爾全集》第二十五卷:《文章與報告(一九一一 — 一九二一年)》(多德雷赫特等,一九八七年,第三—六二頁,以下簡稱「全集本」)中得到考證校定的同篇文字。胡塞爾之後在他的「邏各斯文」的私人自用本中還附加了一些評注性的文字,它們在全集本中作為「版本注」標出。這些評注性文字在中譯本中也一同被譯出,作為「作者後來加入的邊注和補充」附在正文的後面。同時一併譯出的還有《胡塞爾全集》第二十五卷編者所寫的與〈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文字產生背景有關的部分引論,題為「全集本編者引論」。
除此之外,中譯本還參照了威廉.斯基拉奇(Wilhelm Szilasi)於一九六五年所編的第一個單行本:《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法蘭克福/美茵,一九六五年,共一○七頁,以下簡稱「單行本」)。斯基拉奇為此單行本所撰寫的「內容分析」與「後記」也一同被譯出,以「單行本編者內容提要」和「單行本編者後記」(留有海德格痕跡的「後記」)為題附在正文後面。斯基拉奇還撰寫了「生平」和「文獻選要」附在單行本後,這後兩份文字雖然因為寫得時間比較早,不能反映當今胡塞爾研究的最新狀態,但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尤其是作者本人在「生平」中加入了對胡塞爾的回憶,從而使之超出了單純資料的範圍,是故在此仍將它們譯出。
如此一來,書末的「附錄」便共有六篇,分別涉及:一、作者的修改意圖。二、文字的產生背景。三、內容提要。四、內容解釋。五、作者生平。六、有關文獻。
導讀
二十世紀初,胡塞爾《邏輯研究》兩卷本的發表(一九○○/○一年),使現象學得以突破並得以濫觴。這時胡塞爾在哲學界的聲譽斐然,他被看作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這從他的同時代人如狄爾泰(W. Dilthey)、那托普(P. Natorp)等,以及後一代人如海德格(M. Heidegger)、高達美(H.-G. Gadamer)等的評價與回憶中已可見一斑。現象學揭示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如列維納斯(E. Levinas)所說,這個領域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思辨目光所無法達及的。現象學的意向分析和描述方法幾乎使現象學成為一門與邏輯學或心理學相並列的特殊學科,甚至在今天通行的學科分類中還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影響的存在。
在《邏輯研究》發表的同一年,胡塞爾在一封信中預告說:「十年後再出一卷新的!」果然,在此後的十年裡,胡塞爾基本上是筆耕不輟。直到一九一一年,他才應里克特(H. Rickert)之約而拿出〈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我們在後面斯基拉奇所寫的胡塞爾「生平」中可以讀到:「在《邏輯研究》發表後處在顯赫聲譽之中的胡塞爾,沉默了十年之久,爾後才認為〈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值得發表,這個事實賦予了這篇論文無法充分估量的重要意義。」如今它基本上已被看作是一份帶有胡塞爾簽名的「現象學宣言」。
〈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在當時思想界所產生的影響至少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
從批判性的角度來看,在《邏輯研究》完成了對心理主義的有力抨擊之後,〈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仍然需要在兩條戰線上作戰:一方面是與自然主義,另一方面是與歷史主義。前者主要表現在當時盛行的實驗心理學的各種學說之中,後者則主要是指為狄爾泰等人所宣導的歷史學派。胡塞爾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邏輯研究》中對心理主義批判的延續,他仍然堅持不懈地揭示這些學說的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之最終結局。而這個結局對於當時的自然主義與歷史主義來說並非是不言自明的。對於胡塞爾在這方面的努力,非現象學哲學家科拉克夫斯基(L. Kolakowski)曾確切地評價說:「胡塞爾比任何一個人都更多地迫使我們認清知識的窘迫境況:要麼是澈底的經驗主義連同其相對主義、懷疑主義的結論,它被許多人看作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不能被接受的,並且事實上會給我們的文化帶來毀滅的立場;要麼就是先驗主義的獨斷論,它實際上無法論證自身,並且最終仍然是一個隨意性的決定。我不得不承認,儘管最終的確然性是一個在理性主義範圍之內無法達到的目標,但如果沒有那些不斷努力試圖達到這個目標的人們,我們的文化就將會是貧乏而可憐的。而且,如果我們的文化完全落入懷疑主義者們的手中,那麼它將幾乎無法繼續生存下去。我相信,人類的文化永遠不可能達到對它的各個繁雜而不統一的組成部分的完善綜合。然而,恰恰是它的各種成分的不統一性才有助於它的豐富多采,而使我們的文化得以保持其生命力,與其說是各種價值之間的和諧,不如說是各種價值之間的衝突。」實際上,許多當代人之所以能夠從容地遊弋於相對主義和絕對主義的夾縫之間,既帶有懷疑主義的警覺,又仍抱有對健康的理性的最終信念,恐怕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胡塞爾的孜孜求索。
除此之外,由於胡塞爾在〈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中公開揭露了他與狄爾泰思想的分歧,因而這篇文字對後人理解現象學與解釋學之間的關係也不無啟迪作用。
從建構性的角度來看,可以籠統地說,在《邏輯研究》中,胡塞爾試圖將哲學定位於邏輯學和心理學之間,而在〈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中,他努力在自然科學與精神科學(歷史科學)之間找到哲學的位置。雖然在這篇文章中,現象學尚未帶有「先驗」現象學的標記—「先驗」一詞在這裡從未出現過—,但胡塞爾的意圖在這裡已經十分清楚地揭露:透過對哲學的新論證,嚴格的哲學將以構造現象學的形態出現,它將為經驗的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奠定基礎,因為現象學所探討的不僅是「意識構形的本質聯繫」(意識的「心理」方面),同時也探討「與它們相關的本質相屬的被意指性」(即被意識所構造出來的「物理」方面);這兩個研究方向(所有的意識—被意指者)在他兩年後發表的《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第一卷中也被稱作「意向活動」(Noesis)和「意向對象」(Noema)。所以,〈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實際上已含有胡塞爾先驗構造現象學的第一次公開預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日後曾合理地指出,這篇文章「透過《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念》才獲得了對其綱領性論題的充分論證」。
值得一提的是:對胡塞爾在文章中所宣示出的這種努力趨向,海德格既表示贊同,也持有批評,他贊同胡塞爾所提出的「面對實事本身」的口號,贊同「研究的動力必定不是來自各種哲學,而是來自實事與問題」的主張,贊同現象學的直觀性原則與中立性原則。但他拒絕對「實事本身」作「意識的主體性」的理解,並且認為胡塞爾在此文中表現出向近代哲學,尤其是向康德主義的轉向,從而悖離了現象學的原則,放棄了對思的實事(原現象、原實事)的真正思考—對此,讀者可以對照胡塞爾的原文而得出自己的評價。
這裡無須再重構胡塞爾在上述兩個方面(批判性方面和建構性方面)的論述。讀者也許可以在正文中完整地讀到它們,或者可以在後面的「單行本編者內容提要」以及「單行本編者後記」等附錄中獲得對它們的大致了解。
需要強調的是胡塞爾的哲學觀。根據胡塞爾本人的回憶,他首先是在布倫塔諾(F. Brentano)的講座中獲得一個堅定的信念,這個信念使他有勇氣將哲學選擇為終生的職業:「哲學也是一個嚴肅工作的領域,哲學也可以並且也必須在嚴格科學的精神中受到探討。」這個信念不僅時常在他的研究手稿中出現:「哲學就是指向絕對認識的意向」,而且也在〈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中得到第一次公開的展示:「哲學本質上是一門關於真正開端、關於起源、關於萬物之本的科學」。可說胡塞爾這一生從未放棄過這個哲學觀。
將這個哲學觀加以展開,便意味著:一方面,向最終論證、最終奠基的回溯被理解為向認識主體的「意義給予」之成就的回溯,這種回溯是直接進行的,是自身負責的,任何間接的中介都必須被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在獲得了經過最終論證的真理之後,哲學的任務還在於,將這種真理付諸實踐並且根據這種真理而承擔起主體性的責任與義務,這也是一門哲學倫理學和價值論的中心任務。在對哲學的這一理解中無疑包含著胡塞爾對理論與實踐的奠基關係的理解。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凡略曉當今世界「哲學行情」的人都會認為這種哲學觀已經屬於過去,當代人會樂於坦然地面對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的指責。雖然各種不同派別的哲學思潮如今還在「理性」或「合理性」的整體標題下進行著各種獨白或對話,但「告別原理」,亦即告別邏輯中心主義意義上的理性,已經成為或多或少可以被一致接受的口號,世界不再被視作一個可以根據某個或幾個公理而推導出來的統一而有序的系統。笛卡兒曾在他的時代以「有序的」哲思者作為其沉思對話的基本前提對象,時至今日,「有序」已經不再成為哲學思考的公認標準。「有序」連同「無序」一起,被一些哲學家視為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兩大危險。胡塞爾所做的那些對心理主義、自然主義、歷史主義等各種形式的相對主義和懷疑主義的批判,已經明顯與流行意識相悖,而他對確然性之苦苦追求,更是被視為不明生活形式和價值系統之繁雜與間斷的真諦。
然而,就像蘇格拉底或康德至今對當代人所留下來的影響一樣,今天仍然有人——譯者也算是其中之一 ——不懈地在胡塞爾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寶庫中尋找精神生活的動力或支點,究其原因至少可以找到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雖然作為嚴格科學的哲學仍然還是一個「無限遙遠的點」,胡塞爾的哲思方法卻仍然直接而具體地向我們指示著嚴格性的實例。就面前的《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而言,儘管它在胡塞爾的現有文獻中屬於綱領性的方法論述,本書單行本的編者斯基拉奇因而將它比作笛卡兒的《談談方法》,但即使在這裡也可以處處感受到胡塞爾現象學論述和操作的嚴格性。另一位非現象學的哲學家施泰格繆勒(W. Stegmüller)也曾公正地承認:「胡塞爾的研究對哲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對於那些在原則上接受他的思想並將他的方法運用在其研究中的人來說,是一個無限廣闊的、新的工作領域的展現。對於對立陣營的哲學家來說則形成了一種必然性,即:更清晰明白地闡明他們自己的立場,並使他們的論據的無懈可擊性與胡塞爾學說的高度科學水準相吻合。因此,像所有偉大的思想家一樣,胡塞爾對朋友和敵人都發揮了促使他們進行創造性活動的影響。」對於施泰格繆勒所做的這個特徵描述,讀者可以從〈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一文的字裡行間獲得直接的感受。
但比他的嚴格方法影響更為深遠的,或許是胡塞爾在理論研究方面的執著精神。斯基拉奇認為,「胡塞爾的偉大從根本上帶有這樣一種特徵:他能夠長達數十年地以一種頑強的精神,並且在一種寧靜退隱的狀態下,一再地奉獻於新的問題。」這種甘於寂寞的個性,恐怕是每一個「理論人」都應具備的一個基本素質前提。理論研究者應當可以看到:他們的宿命就在於追求獨立的思想而避開流行的時尚。胡塞爾在世紀初所呼籲的「我們切不可為了時代而放棄永恆」,與王元化在二十世紀末一再宣導的「為學不做媚時語」,實際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過強的功利目的和實用心態或許是中國近現代學術困境的一個主要根源,正如文德爾班(W. Windelband)所說:「知識的金果只有在不被尋求的地方才能成熟。」從近年來學術研究的整個趨勢來看,胡塞爾在這篇文章中所做的警告在今天仍然有效:「正是在一個實踐動機超強地上升的時代裡,一種理論的本性也可能會比它的理論職業所允許的更為強烈地屈從於這些實踐動機的力量。但在這裡,尤其是對我們時代的哲學而言,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危險。」就此而論,《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可能會給我們的學術研究帶來一定的啟發與教益。
浙江大學哲學系教授 倪梁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