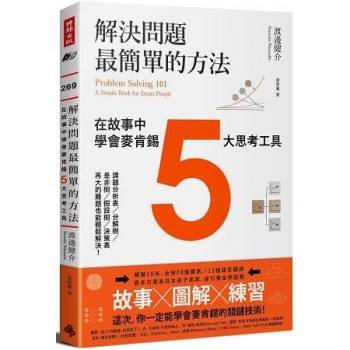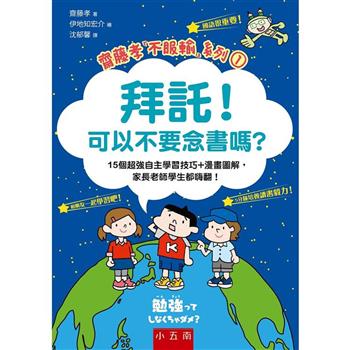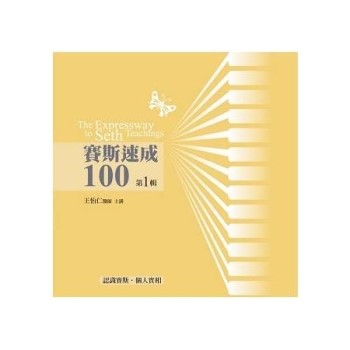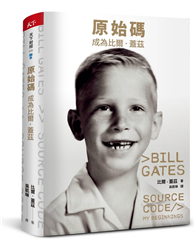小.言
散步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行動,它的弱點是沒有計畫,沒有系統。看重邏輯統一性的人會輕視它,討厭它,但是西方建立邏輯學的大師亞里斯多德的學派卻喚做「散步學派」,可見散步和邏輯並不是絕對不相容的。中國古代一位影響不小的哲學家——莊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裡散步,觀看著鵬鳥、小蟲、蝴蝶、遊魚,又在人間世裡凝視一些奇形怪狀的人:駝背、跛腳、四肢不全、心靈不正常的人,很像義大利文藝復興時大天才達·芬奇在米蘭街頭散步時速寫下來的一些「戲畫」,現在竟成為「畫院的奇葩」。莊子文章裡所寫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後來唐、宋畫家畫羅漢時心目中的範本。
散步的時候可以偶爾在路旁折到一枝鮮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別人棄之不顧而自己感到興趣的燕石。無論鮮花或燕石,不必珍視,也不必丟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後的回念。
詩(文學)和畫的分界
蘇東坡論唐朝大詩人兼畫家王維(摩詰)的〈藍田煙雨圖〉說:
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詩曰:「藍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山路元無雨,空翠溼衣。」此摩詰之詩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補摩詰之遺。」
以上是東坡的話,所引的那首詩,不論它是不是好事者所補,把它放到王維和裴迪所唱和的輞川絕句裡去是可以亂真的。這確是一首「詩中有畫」的詩。「藍溪白石出,玉山紅葉稀」,可以畫出來成為一幅清奇冷豔的畫,但是
「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二句,卻是不能在畫面上直接畫出來的。假使刻舟求劍似地畫出一個人穿了一件溼衣服,即使不難看,也不能把這種意味和感覺像這兩句詩那樣完全傳達出來。好畫家可以設法暗示這種意味和感覺,卻不能直接畫出來。這位補詩的人也正是從王維這幅畫裡體會到這種意味和感覺,所以用「山路元無雨,空翠溼人衣」這兩句詩來補足它。這幅畫上可能並不曾畫有人物,那會更好的暗示這感覺和意味。而另一位詩人可能體會不同而寫出別的詩句來。畫和詩畢竟是兩回事。詩中可以有畫,像頭兩句裡所寫的,但詩不全是畫。而那不能直接畫出來的後兩句恰正是「詩中之詩」,正是構成這首詩是詩而不是畫的精要部分。然而那幅畫裡若不能暗示或啟發人寫出這詩句來,它可能是一張很好的寫實照片,卻又不能成為真正的藝術品——畫,更不是大詩畫家王維的畫了。這「詩」和「畫」的微妙的辯證關係不是值得我們深思探索的嗎?
宋朝文人晁以道有詩雲:「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意,貴有畫中態。」這也是論詩畫的離合異同。畫外意,待詩來傳,才能圓滿,詩裡具有畫所寫的形態,才能形象化、具體化,不至於太抽象。
但是王安石《明妃曲》詩雲:「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他是個喜歡做翻案文章的人,然而他的話是有道理的。美人的意態確是難畫出的,東施以活人來效顰西施尚且失敗,何況是畫家調脂弄粉。那畫不出的「巧笑倩兮,美目盻兮」,古代詩人隨手拈來的這兩句詩,卻使孔子以前的中國美人如同在我們眼面前。達·芬奇用了四年工夫畫出蒙娜麗莎的美目巧笑,在該畫初完成時,當也能給予我們同樣新鮮生動的感受。現在我卻覺得我們古人這兩句詩仍是千古如新,而油畫受了時間的侵蝕,後人的補修,已只能令人在想像裡追尋舊影了。我曾經坐在原畫前默默領略了一小時,口裡念著我們古人的詩句,覺得詩啟發了畫中意態,畫給予詩以具體形象,詩畫交輝,意境豐滿,各不相下,各有千秋。
達·芬奇在這畫像裡突破了畫和詩的界限,使畫成了詩。謎樣的微笑,勾引起後來無數詩人心魂震盪,感覺這雙妙目巧笑,深遠如海,味之不盡,天才真是無所不可。但是畫和詩的分界仍是不能泯滅的,也是不應該泯滅的,各有各的特殊表現力和表現領域。探索這微妙的分界,正是近代美學開創時為自己提出了的任務。
十八世紀德國思想家萊辛開始提出這個問題,發表他的美學名著《拉奧孔或論畫和詩的分界》。但《拉奧孔》卻是主要地分析著希臘晚期一座雕像群,拿它代替了對畫的分析,雕像同畫同是空間裡的造型藝術,本可相通。而萊辛所說的詩也是指的戲劇和史詩,這是我們要記住的。因為我們談到詩往往是偏重抒情詩。固然這也是相通的,同是屬於在時間裡表現其境界與行動的文學。
拉奧孔(Laokoon )是希臘古代傳說裡特羅亞城一個祭師,他對他的人民警告了希臘軍用木馬偷運兵士進城的詭計,因而觸怒了袒護希臘人的阿波羅神。當他在海濱祭祀時,他和他的兩個兒子被兩條從海邊遊來的大蛇捆繞著他們三人的身軀,拉奧孔被蛇咬著,環視兩子正在垂死掙扎,他的精神和肉體都陷入莫大的悲憤痛苦之中。拉丁詩人維琪爾曾在史詩中詠述此景,說拉奧孔痛極狂吼,聲震數裡,但是發掘出來的希臘晚期雕像群著名的拉奧孔(現存羅馬梵蒂岡博物院),卻表現著拉奧孔的嘴僅微微啟開呻吟著,並不是狂吼,全部雕像給人的印象是在極大的悲劇的苦痛裡保持著鎮定、靜穆。
德國的古代藝術
古希臘雕塑.拉奧孔
古希臘雕塑.拉奧孔面部
史學者溫克爾曼對這雕像群寫了一段影響深遠的描述,影響著歌德及德國許多古典作家和美學家,掀起了紛紛的討論。現在我先將他這段描寫介紹出來,然後再談萊辛由此所發揮的畫和詩的分界。
溫克爾曼(Winckelmann,1717—1768 年)在他的早期著作《關於在繪畫和雕刻藝術裡模仿希臘作品的一些意見》裡曾有下列一段論希臘雕刻的名句:
希臘傑作的一般主要的特徵是一種高貴的單純和一種靜穆的偉大,既在姿態上,也在表情裡。
就像海的深處永遠停留在靜寂裡,不管它的表面多麼狂濤洶湧,在希臘人的造像裡那表情展示一個偉大的沉靜的靈魂,儘管是處在一切激情裡面。
在極端強烈的痛苦裡,這種心靈描繪在拉奧孔的臉上,並且不單是在臉上。在一切肌肉和筋絡所展現的痛苦,不用向臉上和其他部分去看,僅僅看到那因痛苦而向內裡收縮著的下半身,我們幾乎會在自己身上感覺著。然而這痛苦,我說,並不曾在臉上和姿態上用憤激表示出來。他沒有像維琪爾在他拉奧孔(詩)裡所歌詠的那樣喊出可怕的悲吼,因嘴的孔穴不允許這樣做(白華按:這是指雕像的臉上張開了大嘴,顯示一個黑洞,很難看,破壞了美),這裡只是一聲畏怯的斂住氣的歎息,像沙多勒所描寫的。
身體的痛苦和心靈的偉大是經由形體全部結構用同等的強度分布著,並且平衡著。拉奧孔忍受著,像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菲諾克太特(Philoctet):他的困苦感動到我們的深心裡,但是我們願望也能夠像這個偉大人格那樣忍耐困苦。一個這樣偉大心靈的表情遠遠超越了美麗自然的構造物。藝術家必須先在自己內心裡感覺到他要印入他的大理石裡的那精神的強度。希臘具有集合藝術家與聖哲於一身的人物,並且不止一個梅特羅多。智慧伸手給藝術而將超俗的心靈吹進藝術的形象。
萊辛認為溫克爾曼所指出的拉奧孔臉上並沒有表示人所期待的那強烈苦痛的瘋狂表情,是正確的。但是溫克爾曼把理由放在希臘人的智慧克制著內心感情的過分表現上,這是他所不能同意的。肉體遭受劇烈痛苦時大聲喊叫以減輕痛苦,是合乎人情的,也是很自然的現象。希臘人的史詩裡毫不諱言神們的這種人情味。維納斯(美麗的愛神)玉體被刺痛時,不禁狂叫,沒有時間照顧到臉相的難看了。荷馬史詩裡戰士受傷倒地時常常大聲叫痛。照他們的事業和行動來看,他們是超凡的英雄;照他們的感覺情緒來看,他們仍是真實的人。所以拉奧孔在希臘雕像上那樣微呻不是由於希臘人的品德如此,而應當到各種藝術的材料的不同,表現可能性的不同和它們的限制裡去找它的理由。萊辛在他的《拉奧孔》裡說:
有一些激情和某種程度的激情,它們經由極醜的變形表現出來,以至於將整個身體陷入那樣勉強的姿態裡,使他在靜息狀態裡具有的一切美麗線條都喪失掉了。因此古代藝術家完全避免這個,或是把它的程度降低下來,使它能夠保持某種程度的美。
把這思想運用到拉奧孔上,我所追尋的原因就顯露出來了。那位巨匠是在所假定的肉體的巨大痛苦情況下企圖實現最高的美。在那醜化著一切的強烈情感裡,這痛苦是不能和美相結合的。巨匠必須把痛苦降低些;他必須把狂吼軟化為歎息;並不是因為狂吼暗示著一個不高貴的靈魂,而是因為它把臉相在一難堪的樣式裡醜化了。人們只要設想拉奧孔的嘴大大張開著而評判一下。人們讓他狂吼著再看看……。
萊辛的意思是:並不是道德上的考慮使拉奧孔雕像不像在史詩裡那樣痛極大吼,而是雕刻的物質的表現條件在直接觀照裡顯得不美(在史詩裡無此情況),因而雕刻家(畫家也一樣)須將表現的內容改動一下,以配合造型藝術由於物質表現方式所規定的條件。這是各種藝術的特殊的內在規律,藝術家若不注意它,遵守它,就不能實現美,而美是藝術的特殊目的。若放棄了美,藝術可以供給知識,宣揚道德,服務於實際的某一目的,但不是藝術了。藝術須能表現人生的有價值的內容,這是無疑的。但藝術作為藝術而不是文化的其他部門,它就必須同時表現美,把生活內容提高、集中、精粹化,這是它的任務。根據這個任務各種藝術因物質條件不同就具有了各種不同的內在規律。拉奧孔在史詩裡可以痛極大吼,聲聞數裡,而在雕像裡卻變成小口微呻了。
萊辛這個創造性的分析啟發了以後藝術研究的深入,奠定了藝術科學的方向,雖然他自己的研究仍是有侷限性的。造型藝術和文學的界限並不如他所說的那樣窄狹、嚴格,藝術天才往往突破規律而有所成就,開闢新領域、新境界。羅丹就曾創造了瘋狂大吼、軀體扭曲、失了一切美的線紋的人物,而仍不失為藝術傑作,創造了一種新的美。但萊辛提出問題是好的,是需要進一步作科學的探討的,這是構成美學的一個重要部分。所以近代美學家頗有用《新拉奧孔》標名他的著作的。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美學散步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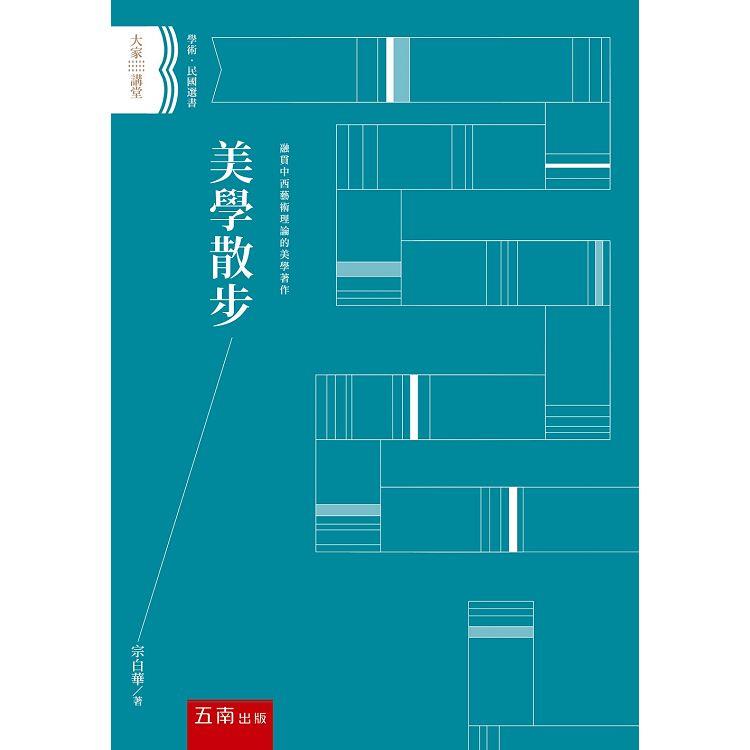 |
美學散步【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作者:宗白華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3-28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87 |
藝術總論 |
$ 387 |
美術 |
$ 387 |
社會人文 |
$ 399 |
中文書 |
$ 400 |
藝術總論 |
$ 400 |
Books |
$ 409 |
藝術理論 |
$ 409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美學散步
融貫中西藝術理論的美學著作
《美學散步》是作者的美學論集,主要內容包括繪畫,詩歌,書法的批評與對比。共22篇。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美學和文藝一般原理。第二部分,中國美學史和中國藝術論;第三部分,西方美學史和西方藝術的論述;第四部分,詩論。
作者憑著深厚的中國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良好素養,以比較的眼光,特別是中國繪畫為主,並以詩歌、書法為主要研究對象,中西比較賞析,對中國古典美學思想的幾個重要範疇加以闡釋,引領讀者領會中國和西方藝術家的意境。
作者簡介:
宗白華(1897-1986)
生於安徽安慶。哲學家、美學家、詩人。1920年赴德國留學。1925年回國,任東南大學、中央大學哲學系教授。1952年起,擔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等。宗白華先生被譽為「融貫中西藝術理論的一代美學大師」。主要著作有:《美學與意境》、《美學散步》、《歌德研究》、《論中西書法之淵源與基礎》、《宗白華全集》、《宗白華美學文學譯文選》等。
《美學散步》是作者的美學論集,這些文章的寫成年代為1920年至1979年。1981年6月首次出版。
章節試閱
小.言
散步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行動,它的弱點是沒有計畫,沒有系統。看重邏輯統一性的人會輕視它,討厭它,但是西方建立邏輯學的大師亞里斯多德的學派卻喚做「散步學派」,可見散步和邏輯並不是絕對不相容的。中國古代一位影響不小的哲學家——莊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裡散步,觀看著鵬鳥、小蟲、蝴蝶、遊魚,又在人間世裡凝視一些奇形怪狀的人:駝背、跛腳、四肢不全、心靈不正常的人,很像義大利文藝復興時大天才達·芬奇在米蘭街頭散步時速寫下來的一些「戲畫」,現在竟成為「畫院的奇葩」。莊子文章裡所寫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
散步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行動,它的弱點是沒有計畫,沒有系統。看重邏輯統一性的人會輕視它,討厭它,但是西方建立邏輯學的大師亞里斯多德的學派卻喚做「散步學派」,可見散步和邏輯並不是絕對不相容的。中國古代一位影響不小的哲學家——莊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裡散步,觀看著鵬鳥、小蟲、蝴蝶、遊魚,又在人間世裡凝視一些奇形怪狀的人:駝背、跛腳、四肢不全、心靈不正常的人,很像義大利文藝復興時大天才達·芬奇在米蘭街頭散步時速寫下來的一些「戲畫」,現在竟成為「畫院的奇葩」。莊子文章裡所寫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美學散步
小言
詩(文學)和畫的分界
美從何處尋?
論文藝的空靈與充實
一、空靈
二、充實
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
一、引言——中國美學史的特點和學習方法
二、先秦工藝美術和古代哲學文學中所表現的美學思想
三、中國古代的繪畫美學思想
四、中國古代的音樂美學思想
五、中國園林建築藝術所表現的美學思想
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
引言
一、意境的意義
二、意境與山水
三、意境創造與人格涵養
四、禪境的表現
五、道、舞、空白:中國藝術意境結構的特點
中國藝術表現裡的虛和實
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
...
小言
詩(文學)和畫的分界
美從何處尋?
論文藝的空靈與充實
一、空靈
二、充實
中國美學史中重要問題的初步探索
一、引言——中國美學史的特點和學習方法
二、先秦工藝美術和古代哲學文學中所表現的美學思想
三、中國古代的繪畫美學思想
四、中國古代的音樂美學思想
五、中國園林建築藝術所表現的美學思想
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
引言
一、意境的意義
二、意境與山水
三、意境創造與人格涵養
四、禪境的表現
五、道、舞、空白:中國藝術意境結構的特點
中國藝術表現裡的虛和實
中國詩畫中所表現的空間意識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