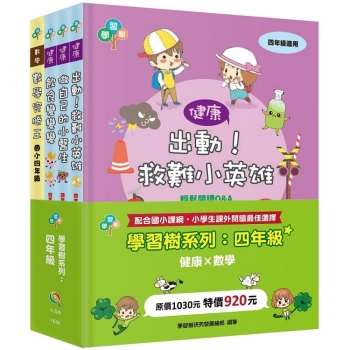第一篇 儒家學派的源流與思想內涵
第一章 儒家哲學的前沿——魯國與宗周文化
儒家和道家是中國文化長期以來的主流思想,其中孔子是儒家的開創者。孔子集夏、商、周三代思想與文化的精華,不但繼承了他之前約三千年的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傳統,也開出後續性的、迄今仍不息滅的儒家哲學與文化之慧命。孔子以禮、樂、射、御、書、術為教育弟子的教材,以《詩》、《書》、《禮》、《樂》、《易》等代表先聖先賢的歷史、思想與文化的業績為儒學典籍。戰國時代已有將代表儒學內容的這六部典籍稱為「六經」。《莊子‧天運》載:「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今觀《禮記》中有〈經解〉篇,《呂氏春秋》引用《孝經》,反映了儒家所言的「經」係指儒家經典。就史脈而言,「經」係由「書」到「典」的歷程再發展而成的。「書」的本義是「著」、「記」和「寫」。《後漢書‧許慎說文解字序》對「文」、「字」和「書」做了一區分,謂:「黃帝之史倉頡,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書,如也。」換言之,「書」指書寫出來的文字。因此,作為「六經」之一的「書」,其始原義是「記載」而不是「書籍」。例如:《尚書》中所含的〈虞書〉、〈夏書〉、〈商書〉和〈周書〉等所用的「書」字,當指「記載」義。「經」字的原意為絲織的縱絲,後來引申為常理、常道、常則,與「典」的引申義接近。儒學予「六經」賦予了這些含義。例如:《荀子‧儒效》曰:「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也。」《禮記‧經解》點出儒家六經之旨要,及其施教的重點,所謂:「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荀子指出了六經中五經的人文教育價值,且視為全人教育之總綱所在。《荀子‧勸學》說:「《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可見儒家「六經」為儒學的核心文本所在。由於《樂》經已早佚,因此,本篇以《樂》經之外的其他五經為論述先秦儒學的骨幹,同時,也將分別代表孔子、孟子、荀子三人思想的《論語》、《孟子》、《荀子》列為儒學三大家的論述依據。此外,近世出土文獻中,郭店儒簡證成了孔子與孟子間的子思、曾子學派,因此,本篇得列《中庸》、《大學》為先秦儒家思孟學派的典籍,以及其他相關的重要儒學思想文獻,如:上博簡的〈性情說〉(與郭店竹簡中的〈性自命出〉簡文字內容幾乎相同)、郭店楚儒簡〈五行〉篇、二○○一年上海博物館公布的〈孔子詩論〉、〈緇衣〉,郭店儒簡中的〈窮達以時〉、〈唐虞之道〉,和馬王堆帛書《易傳》之孔門易學。
中國哲學離不開中國文化的醞釀,哲學也離不開脫胎於宗教的發展過程。因此,本篇特別先論及孕育儒家思想的宗周文化及周公受封於魯的方國地域文化,尤其是山東古老的東夷文化,這些對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注入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和元素。
第一節 魯國與宗周的文化因緣
魯國是形成西周宗教文化與東夷區域文化融合的儒學故鄉。因此,對先秦儒家思想的探索,當溯源於魯國的都邑文化之內涵和傳統。金文「都」字、《詩經》中「國」字常被稱為邑或邦。《廣雅‧釋詁》:「都,國也。」《釋名‧釋州國》:「國城曰都。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都」之本義或國、邑沒有分別,周公將其長子伯禽派去受封地魯,其作用在於安置周室東方的前哨。由於周公的關係,魯國受賜豐厚,得享天子之禮樂,地位特殊。宗國保留殷禮,魯國則保存典型的周禮。《左傳‧襄公十年》謂:「周禮盡在魯也。」魯國為東方的宗周模式,因此,周公治國的敬天保民思想、明德慎罰、勤政任賢等政治哲學要旨為魯國政治理念所本。周公對「殷民六族」採懷柔政策,仍任其保留三年之喪的舊禮制和其他的氏族文化。魯國採周公所樹立的「尊,而親之」之治國策略,進一步的健全宗法制。魯國係一典型的宗法農業社會兼具周人重農及重禮兩大文化風格,尊祖和敬宗是維繫宗法制度的兩條紐帶,再配合重土輕遷的農業社會文化,於是依宗法制度的嫡庶、親疏、長幼等關係所確立貴族之間的貴賤、尊卑、長幼、上下之人倫身分和森嚴有序的道德規範。周人在宗族情感的凝聚上,則不斷的祖述先王之訓和周公之禮。中國古代政治體制有貴族君主制和專制君子制兩種基本類型。後者是戰國以後宗法制度解體後才真正出現。前者的君權分授封土予有血緣關係或姻親關係的貴族群體,王國維《殷周制度論》認定周人實行的是「立子立嫡制度」。
《左傳‧襄公十四年》載晉國師曠之言: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
這段話可剖析出孕育了孔子與儒家的魯國文化特性,是客觀切實地研究孔子與儒
家思想的必要途徑。
第二節 祭天祀祖的精神傳統
魯國的祭祀制度以尊德重民的周禮為中心,祖先崇拜為其特點,兼及天神、地祇,其所祭祀的神靈大多由周人的祖先充任,是祭祀祖先的一種變形。天神指對上帝(天)及日、月、星辰等天體的崇拜與祭祀。周人對上帝的祭祀,主要是在「禘」與「郊」祭中舉行。禘祭是宗廟之祭的一種,屬祭祖時兼及「上帝」。「郊」祭主要是祭稷神,是祭穀物之神兼及「上帝」。據《左傳》記載,魯國對日、月、星辰有時也祭祀。因此,日、月、星辰的異常象徵著天災人禍的即將降臨。按周禮,若有日食發生,則意味著君主有災禍降臨,國中要舉行一系列的禳禱活動。地祇以社、稷、山、川之神為主,社祭是指對土地之神的祭祀,《論語‧八佾》載魯哀公問社,宰我對曰:「社,夏後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社祭本是祭土地神,是為乞求農業豐收而設立的。一般多在春耕前舉行。春秋時期社稷已成為國家的象徵,地位同於宗廟,重要性超過君王、郊祭。漢儒多認為這是祭天之禮,由較原始的文獻觀之,「郊」是以祭穀物之神(農神)為主的一種大型祭祀活動,自新春開始,乞求全年豐收的大型祭祀,所祭神靈甚多,《荀子‧禮論》曰:「郊者,並兼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此外,「灶」,即火神爺,《論語‧八佾》云:「與其媚於奧,寧媚於,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行」,即祭路神,「蜡」為年終大祭百神之禮。魯國平時飲食享宴之前也要先祭神靈,宗廟是國家的象徵,國君即位、授爵、冊封、授兵、朝聘、會盟等重大活動皆在宗廟中舉行。所祭神主以始封祖及近世祖先為主。禘祭是祭祖禮中最為隆重的一種,常與郊祭並舉。
禮樂在周初具有調整人際關係及規範人之行為的功能。魯國是姬姓「宗邦」,諸侯望國,《左傳紀事本末》卷一《王朝交魯》高士奇說:「周之最親莫如魯,而魯所宜翼戴者莫如周。」西周之前,禮樂尚帶有明顯的巫術性質。分而言之,禮與樂有別,若統而言之,則樂和狹義的禮是廣義的禮的組成內容。禮之起源,《說文》釋禮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禮記‧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原始的信仰在經歷了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後,過渡到祖先崇拜階段。在當時的信仰中,「人統」與「神統」統合在一整體中,定期地對祖先施行祭祀,或通過一定的音樂舞蹈或致其虔敬於鬼神。「夏道尊命,事鬼敬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將禮樂性質的人文化轉變是周人的功勞,他們將歷來習俗制度化,形成周人的禮樂文化。
對魯國及日後儒家影響深遠的《周禮》之內容可概括為三層面:
(一)禮義:《禮記‧禮器》:「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大學〉十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二)禮儀或禮節:禮樂制度大體可分為吉、凶、軍、賓、嘉五大方面。細分之,有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謂「繁文縟節」。
(三)禮俗:社會風俗與民眾的道德習慣。
魯國由於其封國的特殊性質及所處的地理環境而成了宗周禮樂文明的嫡傳,全盤繼承了周人的文化傳統,周王室為昭周公之明德,賜魯國予受封他國所沒有之天子器物、服飾;魯人既有此尊業與特權,自不能忘記祖述先人之訓,追憶周公之禮,乃以傳播宗周文化為歷史使命,周初實行分封的目標旨在「以藩屏周」。魯為姬姓,齊為姜姓,後來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周禮在魯遂為禮文化中心,在推行周代禮樂制度時,有望國地位。
《論語‧八佾》載述:杞、宋兩國分別為夏、殷後代的封國,在周人「興滅國,繼絕祀」的傳統下,得以享國並祭祀其失祖,但所保存之夏、殷之禮,仍令孔子有「文獻不足」之憾。但是春秋末期,魯國的古典樂舞,仍令吳公子季札觀賞後嘆為「觀止」。晉范宣子讚嘆魯國典冊之富,說「周禮盡在魯」時,已到了春秋末年魯昭公時期,當年魯國濃郁的禮樂文化氣氛,或許很難產生像孔子這樣一位禮樂大師。在魯國之初,周公所制定的禮是人們行為的準則,上自魯公,下至卿士,皆循禮而動,一切按照「以次世;長幼,而等胄之親疏」的昭穆制度。一般而言,各諸侯國對周禮各取所需,因地制宜,唯有魯國始終不忘「法則周公」,祖述先王之訓。周禮本身是「損益」前代夏、商之禮而來。
魯國建國之初,魯人的「親親」觀念便逐漸深入人心,相信「非吾族類,其心必異」,於是,異姓家族均被排斥在外。當權派的卿族一直限定在「伯禽之後」,與魯國不同的是,姜姓齊國「舉賢而上功」為治國方針之一,異姓的管仲甚至輔佐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魯國不同於齊國處在於注重血親關係,旨在保存卿族宗祀的觀念,魯人在行為上重義輕利,經濟上重農輕商意識,社會意識有重男女之別,為儒家所繼承。
《淮南子‧要略》曰:「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說苑‧政理》云:「孔子以為『聖人之舉業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遂可施於百姓。』」意指周公之德義對魯國風俗之影響以及伯禽對魯地原有「禮」、「俗」的變革,卓有成效。因自然條件不同而形成的習尚叫「風」,由於環境不同而造就的習尚謂「俗」。魯與他國習俗的差別,主要表現在「男女有別」和「夫婦有別」的倫序上,《禮記‧王制》曰:「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這一倫理習俗尖銳的反映出魯文化的禮樂傳統在「化民成俗」上之效應。
周人有鑒於殷商迷信昏亂、丟國喪家之事實,周初「重人輕天」思想於是萌芽,春秋以來「重人輕天」及輕視鬼神的思想逐漸衍生,鄭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傳‧桓公六年》曰:「夫民,神之主也成。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已充分認識到只靠神靈很難得福佑,從而認識到「民」的重要性。因此。春秋時期對於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已不如西周時期那樣盛行與隆重。
春秋中期以前,學術本為官有,除國學外,魯太廟是魯國講習禮樂的重要場所。〈八佾〉:「子入太廟,每事問。」學琴於師襄,訪樂於萇弘。孔子所學以禮、樂為主,他的一家之學便是在此基礎上,統攝西周以來之文籍及典章制度、倫理道德而形成的。西周所建制的「禮」是以血緣為基礎,以等級為特徵的宗法氏族統治體系,西漢「中興之主」宣帝曾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漢書‧宣帝紀》)漢代的禮法可說是統一了魯國的禮教和秦國的法律。
第三節 禮樂文化中「親親上恩」的核心價值
先秦的「禮」,廣義而言指包括節文儀式、倫理道德規範和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等所構成的一整套規範體系,狹義而言則指儀式層面的禮儀。五禮中的吉禮(主要為祭祀)、凶禮(主要指喪葬)形成在相應的原始宗教觀念上。古代的古、凶、賓、軍、嘉「五禮」,早在東夷文化中已略具輪廓。儀式、禮典是帶有象徵性或表演性的模式化行為,其所內具的無形價值觀念體系,具有啟引靈魂、主導的作用。蓋禮儀、禮義和禮制(社會政治等級)相互關聯形成三代上層社會結構和其社會文化之意識形態。宗法貴族的統治手段主要是「禮治」,就歷史而言,東夷文化中的禮制萌芽和禮觀念的雛形,是三代禮制的重要淵源之一,魯國儒家禮學和齊國管晏學派的禮學則構成齊魯文化的一項特色。
此外,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東夷文化在原始宗教、禮儀、曆法和文字等方面所獲致的成就,對西周以後的齊魯文化產生許多具體影響。另方面,夏朝的建立,標誌著一種對眾多文化區域產生及影響力的全國性文化中心。《詩》、《書》、《左傳》等先秦文獻將夏、商、周三代視為前後連貫、具天下共主之政治身分的政權。西周齊、魯兩國是分別建立在兩個商朝故地上,即蒲姑國的臨淄以及奄國的曲阜。齊魯文化係以周文化為主導,又融攝了夏商文化因素和東夷文化的集大成性質文化。其中齊國文化環境較為開放、寬鬆,較注重功利,工商業和軍事比較發達,戰國時代成為百家爭鳴的中心。魯國基於宗族文化傳統,較重視維持宗周文化的特質,強調道德名節、宗法倫理及固有傳統文獻之研究。齊、魯文化在崇尚禮制、重視學術方面有一致性,形成有別於南方楚文化、吳越文化,北方燕文化,西方秦文化,中原晉鄭文化之區域文化特色。
春秋時期的魯國是周王室以外,保存禮樂制度最多的文化中心,儒家在這一文化土壤上誕生,以弘揚禮樂制度及德治思想為核心價值。在戰國以前,宗法貴族掌政的時代,各國皆以「親親上恩」為通行的政治原則。「親親」原則旨在強化宗族成員間血緣認同,增進其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上恩」強調血緣情感,用感恩的力量來凝聚宗族成員的向心力,處處以宗族利害的大局為考量。《呂氏春秋》將「親親上恩」與「尊賢上功」視為區別魯文化與齊文化的判準。周公長子伯禽率領原在陝、甘一帶的姬姓宗族,繼周公東征之後,二度大規模入山東地區,其治魯的人脈主要靠宗族組織和姬姓族人的團結合作。先秦時期的貴族文化係依附在宗族組織下,伯禽治魯旨在移植周文化和改造異族文化,因此,「親親上恩」原則可鞏固姬姓貴族在魯國的政治和文化特權,這一原則將魯國引領至重倫理親情、禮儀形式、道德規範和德化人格的文化路向上。「親親上恩」這項原則特別體現在家庭倫理方面,逐漸形成一成熟的學說,為儒家預先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與文化資源。相較於「尊賢尚功」的齊文化,不可諱言的,魯文化呈現出相對的較為保守、偏狹、輕忽功利以及陳義過高而不切實際的局限性。
第四節 儒家之源流與特色
「儒」字首見於《論語‧雍也》載孔子對子夏說:「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反映出儒者之間個別差異很大,品第不一。然而皆被稱為「儒」,則有其基本的一致性。今觀《說文》的解釋為:「儒,柔也,術士之稱。」清朝段氏之《解字》敷衍其說曰:「以疊韻為訓,鄭錄目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當代文字學家戴君仁先生從另一側重面解釋說:「案說文『儒,柔也。』一語,只是一個聲訓,⋯⋯聲訓的辦法,只取訓字與被訓字某一點相合,而不必全部相同。所以儒有柔的一部分性質,而不是全體徹內徹外,表裡俱是一致的。⋯⋯所以『柔也』二字,不是儒字的正式訓詁,正式訓詁,是『術士之稱』四個字。」
然而,何謂「術士」呢?就中國哲學史而言,將「術」字作怪迂、方士的方術、法術解,係流行於漢代之後,在漢代「術士」一詞幾乎成了「方士」的專稱。在春秋戰國之地,「術」係一切學問技能的通稱,例如:管子、墨子和韓非子皆稱賢良者乃有道術之士。莊子在〈天下〉將「方術」、「道術」互文。因此,在先秦「術」字古義當係方法與學問之泛稱,所看重的是治國的道術或方術。「術士」可被了解成一切有學術技能的人,亦即「道術之士」。此外,「術」與「藝」在古義是相通的,例如:《列子》中〈周穆王〉謂:「魯之君子多術藝」,《史記》中〈儒林傳〉載:「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禮記》中〈鄉飲酒義〉:「古之學術道者」注云「術猶藝也。」民國初年的國學家劉師培解釋說:「古代術士之學蓋明習六藝以俟進用。」
至於儒者修習的「六藝」之內容為何?當代國學大師錢穆先生的解釋:
周禮地官司徒保氏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六儀。六藝者,一曰五禮,二曰六藝,三曰五射,四曰五卿,五曰六書,六曰九數。禮樂射御書數六者,乃貴族之學,亦儒生進身的貴族之學也。習禮樂所以為相,習射御所以為將,習書數所以為宰。故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又曰:「學也祿在其中矣。」蓋其先儒士之習六藝,皆所以進身於貴族而得穀祿也。其後又迻以稱經籍。……昔之儒者身習禮、樂、射、御、書、數之六藝,至漢既不得傳,乃以儒者所傳古經籍足其數,以附會於六藝焉。
依錢先生的看法,六藝係禮、樂、射、御、書、數等六種技藝,而非六部經書。「藝」字原意為種植,引申為才能、文德義或「常也,準也」。綜括上述,我們可把「儒」理解為有道術或道藝之士,猶如今所稱的學者或知識分子,他們如做例行的園藝工作般地天天修習諸般才能、文德,以之為日常生活的準則。他們進德修業,誠於衷形於外,涵養成舉止文雅,優柔不迫之儀態,期能成為文質彬彬的君子。彼時,他們的服飾或有異於常人,言貌冠服形成一特殊風格。由孔子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或可理解為君子儒係具備才藝的知識分子,以傳授知識,柔化性情的教育工作為職志。小人儒則以相人治喪為其謀生之職業。蓋中國古代文化以禮樂為其具體表現,尤以喪葬儀文特別講究,以致鋪設得繁複精微。一般人若非專習其事者,實不易全懂,流勢所趨,日久則自然發展成一種專業化的術士。
「儒」之得名、內容及所賦予的特定意義,最初典籍之記載可追溯至《周禮》中〈天宮太宰〉有「以九兩繫邦國民」之一條,有所謂「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鄭康成注曰:「師有德行以教民者,儒通道藝以教民者。」在上古,師儒乃代司徒敷五教的一種職務,尚不得謂為一家之學。俟周衰,王官之學失其所守,遂分裂為私家之學。孔子開私人講學授徒之風。孔子逝世後,其弟子繼承其業,各以其心得傳授他人,《韓非子‧顯學》謂: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晉‧陶潛於其《群輔錄》云:
夫子沒後,教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蓽門圭竇,甕牖繩樞,併口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諷諫之儒。孟子傳《書》為道,為疏道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
孔門四教為文、行、忠、信。其教科則為《易》、《書》、《詩》、《禮》、《樂》、《春秋》等六經。孔子之教科與《周官》之儒的職掌一致。等到墨家興起且與孔門之學風相對,楊氏為我學說繼起突出與儒門對峙。逐漸地,《漢書‧藝文志》所謂九流者叢生而錯出。於是,後人遂以儒之名稱冠於孔門學徒,以為甄別之標幟。吾人由學術史考察《詩》、《書》、《禮》、《樂》等書,原本未加「經」之稱號。在儒家典籍中,最早冠以「經」字者雖為《孝經》,然而《孝經》係原來既與的書名,非後加「經」字以為尊號。在儒家的人物中,首先將典籍稱做「經」者,係始於荀子。六經的名稱首見於道家的典籍中。12值得吾人注意者,荀子所列舉的經書中獨不見《易經》,可推知後人所謂「六經」當非孔子時所能有。
再者,觀《論語》中〈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復審視先秦有關孔子的文獻,孔子除了詩書禮樂之外,似無其他教材。且這四種教材裡,樂是沒有書籍的,禮雖有書,似乎亦不過只是輯錄一些人與人相與的行為之節目儀注類的典籍,並無專書的形態。「詩」是周王朝的雅言,係由王室裡的樂官蒐輯而成。「詩」在彼時的主要功用有三:(一)在修身處事時用為格言;(二)用於外交應對的修辭及達意之資具;(三)應用於各種宴會場合中的演奏,或助於儀禮,或助於餘興。「書」乃藏諸王府的政府檔案之類,大部分為誥命等公文,現存二十九篇。《詩》、《書》是後人藉以了解周代歷史的重要文獻。當時的貴族教育中,皆須誦習《詩》、《書》以便隨時引證和應對。吾人由《左傳》、《國語》中可獲知孔子前盟宴賦詩的風氣很流行。《詩》、《書》是傳統的經典,在春秋至戰國初期被視為傳統文化,非特別歸屬於某一家一派。
因此,孔子採用詩、書、禮、樂來教導弟子,可謂是繼承了文化傳統,將傳統上屬於貴族知識階級的典冊作為其「有教無類」的教材。由於歷史的變遷,原來貴族知識分子的學問逐漸荒疏。相對的,新的「士」階層逐漸興發,其聚徒講學的發展結果,不但繼承了原來貴族知識分子之學問,亦承襲了他們的稱號,如是而成為社會上一種新的平民知識階級。換言之,貴族因忙於作戰與治賦,無暇於講究「儒」之修養,而孔子及其門弟子以高度修養的「士君子」人格為基本目標,以仁人、聖賢之堯舜為理想境域。因此,這些由平民中興起之有理想抱負,有實踐毅力之「君子儒」取代了原來的「貴族儒」,而成為「儒」的正宗。「儒」至此,乃由泛稱一般知識分子的廣義含義,轉變成專指孔門弟子的狹義含義。
後來,由於禮崩樂壞,儒家原來「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的治術,無助於現實政冶。於是儒者的主要進身之階,不是從政,而是教學和相禮。趨勢所向,後期儒家只留心政教制度,基於職業需要,特別提倡學制和禮制。換言之,彼時儒家者流在逐漸忽略其他技藝後,「儒」由專指孔門弟子的術士義再轉變成專事有裝飾和教育之價值的「禮」、「文」者,亦即專詩、禮的「文學」者。原來的射、御、書、數等,至此已非孔門之專長。文學之儒亦轉稱六藝為六種經書,以取代那些不再為他們所精熟的射、御、書、數等技藝。
《韓非子》中〈五蠹〉篇謂「儒」之含義為:
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仁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奠榮;此匹夫之美也。
《史記》中〈太公自序〉述司馬談之言云: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由「六藝經傳以千萬數」一語,可知其所謂「六藝」乃指六經。此後,儒家的六經與六藝便成了同義字。《漢書》中〈儒林傳〉載:「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顏師古注曰:「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王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詩、書、易、禮、樂、春秋的六藝與周禮保氏六藝,已普遍地為後人所接受。因此,我們由戰國晚年至秦漢這段時期觀之,「儒」這一詞語已漸由「嫻習六藝」的儒士轉化成專治「王教之典籍、先王之成法」的文學儒了。這是「儒」字含義的第三次嬗變。再由荀子不稱《易經》這點來看,六經非孔子時代既已完成。及漢代,儒者轉折到「師儒」這地步外,似無他路可走。師儒所承傳的以六經為內容之文學,成為漢儒之代名詞。因此,以六經來解釋六藝,是漢儒的流風。而「儒家」一詞亦創用於漢代。再者,不論六藝或六經,皆可看出儒家是肯定和承傳歷史文化的業績為自身的工作。同時,儒家是以人文教養來完滿化文質彬彬的人格生命,作為對己修身,對世教化的目標。吾人或可說儒家是以德性人格的「仁」為體,以構成歷史文化內涵之六經或六藝為用。其目的一方面在成聖成賢,一方面在以人文化成天下,體現歷史文化的價值理想。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先秦哲學史的圖書 |
 |
先秦哲學史 作者:曾春海 出版社: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4-10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585 |
哲學 |
$ 585 |
社會人文 |
$ 605 |
中文書 |
$ 605 |
中國哲學 |
$ 605 |
Others |
$ 611 |
Books |
$ 618 |
文史哲學群 |
$ 618 |
哲學 |
$ 618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先秦哲學史
★增訂新版!
★針對「儒、道」兩家,以宏觀性視域、「比較哲學」的方法,增補「儒、道」具差異性特色,及其共同關注之人類精神文明問題、可資互補處。
本書是作者累積四十多年在「先秦哲學」研究、教學經驗而撰成。全書依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之學派分類,分為六篇,詳述各學派內涵與特色。
本書特色為:
一、將近世出土文獻的主要哲學論題脈絡性地概括於書中。
二、掌握原典蘊含之哲學性問題,如:本體論、宇宙論、天人關係、心性論、認識論、人生境界的功夫實踐、倫理學、政治哲學等。
三、重視原典、基本概念的精確分析、論述脈絡的清晰性、理論結構的系統性及文字表述的可讀性。
四、兼重文化史和思想史,資料詳備,務求對「先秦哲學」內涵有情境性、脈絡化的理解。
五、強化對名家、墨家及荀子邏輯和知識理論之紹述。
作者簡介:
曾春海
✦輔仁大學哲學博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後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
現 任
中國文化大學哲學所兼任教授
學術專長
先秦儒家哲學、魏晉哲學、宋明理學、易經
著 作
《先秦哲學史》、《兩漢魏晉哲學史》、《竹林七賢的玄理與生命情調》、《中國近當代哲學史》、《中國哲學史綱》、《朱熹哲學論叢》、《朱熹易學析論》、《易經的哲學原理》、《儒家的淑世哲學──治道與治術》、主編《中國哲學概論》、合著《中華文化人文精神教材》等
章節試閱
第一篇 儒家學派的源流與思想內涵
第一章 儒家哲學的前沿——魯國與宗周文化
儒家和道家是中國文化長期以來的主流思想,其中孔子是儒家的開創者。孔子集夏、商、周三代思想與文化的精華,不但繼承了他之前約三千年的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傳統,也開出後續性的、迄今仍不息滅的儒家哲學與文化之慧命。孔子以禮、樂、射、御、書、術為教育弟子的教材,以《詩》、《書》、《禮》、《樂》、《易》等代表先聖先賢的歷史、思想與文化的業績為儒學典籍。戰國時代已有將代表儒學內容的這六部典籍稱為「六經」。《莊子‧天運》載:「孔子謂老聃曰...
第一章 儒家哲學的前沿——魯國與宗周文化
儒家和道家是中國文化長期以來的主流思想,其中孔子是儒家的開創者。孔子集夏、商、周三代思想與文化的精華,不但繼承了他之前約三千年的中國歷史文化的精神傳統,也開出後續性的、迄今仍不息滅的儒家哲學與文化之慧命。孔子以禮、樂、射、御、書、術為教育弟子的教材,以《詩》、《書》、《禮》、《樂》、《易》等代表先聖先賢的歷史、思想與文化的業績為儒學典籍。戰國時代已有將代表儒學內容的這六部典籍稱為「六經」。《莊子‧天運》載:「孔子謂老聃曰...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二版序
本書自二○一○年十月初版以來,已歷三刷,在即將第四刷之際,本人除了將全書校正錯別字之外,亦增加了新的內容。有鑒於先秦哲學的「六家」是中華民族遠古先聖先賢們的共同智慧,不同學派既有縱向的發展,亦有橫向的聯繫,非各自獨立而可切割的六學派。其中儒、道兩家的原創性智慧對中華民族精神文明的凝聚和發展,有源遠流長的影響,可謂中華文化精神文明的兩大本根。雖然儒家由於許多因素而形塑了其構成中華文化主流的地位,但是道家的形上智慧和人生智慧也是安身立命的不朽經典。質言之,儒家和道家是各有獨特性,也可互鑒交...
本書自二○一○年十月初版以來,已歷三刷,在即將第四刷之際,本人除了將全書校正錯別字之外,亦增加了新的內容。有鑒於先秦哲學的「六家」是中華民族遠古先聖先賢們的共同智慧,不同學派既有縱向的發展,亦有橫向的聯繫,非各自獨立而可切割的六學派。其中儒、道兩家的原創性智慧對中華民族精神文明的凝聚和發展,有源遠流長的影響,可謂中華文化精神文明的兩大本根。雖然儒家由於許多因素而形塑了其構成中華文化主流的地位,但是道家的形上智慧和人生智慧也是安身立命的不朽經典。質言之,儒家和道家是各有獨特性,也可互鑒交...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自序
二版序
第一篇 儒家學派的源流與思想內涵
第一章 儒家哲的前沿——魯國與西周文化
第一節 魯國與宗周的文化因緣
第二節 祭天祀祖的精神傳統
第三節 禮樂文化中「親親上恩」的核心價值
第四節 儒家之源流與特色
第二章 《周易》原經《尚書》及《詩經》所呈現的西周哲學與文化
第一節 西周《周易》原經的天人思想
第二節 《尚書》以德配天的天命觀和以德治國論
第三節 《尚書》對殷商思想之述要
第四節 《尚書.周書》的主要篇章要旨
第五節 《詩經》的天論及詩教的人文價值
第三章 春秋時代的儒家思...
二版序
第一篇 儒家學派的源流與思想內涵
第一章 儒家哲的前沿——魯國與西周文化
第一節 魯國與宗周的文化因緣
第二節 祭天祀祖的精神傳統
第三節 禮樂文化中「親親上恩」的核心價值
第四節 儒家之源流與特色
第二章 《周易》原經《尚書》及《詩經》所呈現的西周哲學與文化
第一節 西周《周易》原經的天人思想
第二節 《尚書》以德配天的天命觀和以德治國論
第三節 《尚書》對殷商思想之述要
第四節 《尚書.周書》的主要篇章要旨
第五節 《詩經》的天論及詩教的人文價值
第三章 春秋時代的儒家思...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