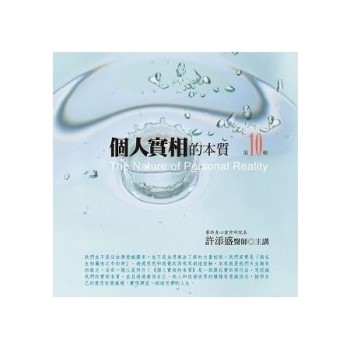隔離的歷史,就是一部公衛發展史
也是一部關於恐懼、濫權與獵巫的歷史
隔離從來不曾消失,未來更將成為常態
你我隨時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歧視的「帶原者」
後疫情時代必備讀物
結合田野調查、公衛、歷史與社會學,全面理解隔離的社會心理與意義!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詹長權、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左宜恩
好評推薦
結合田野調查、公衛、歷史與社會學,全面理解隔離的社會心理與意義!
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詹長權、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左宜恩
好評推薦
「隔離」(Quarantine)源自義大利文「quarantena」,意思是「四十天」。人類對抗瘟疫最古老的回應,就是把「可能染疫」的人和「健康的人」隔開。隔離是人類面對未知的本能反應,卻也涉及監控、收容和控制,成為剝奪人權的手段。
本書的基本假設是:因為人類是混亂的、有缺陷的、自私自利的存在,隔離過去一直存在我們的歷史裡,也會是我們未來的一部分。有效管理人口的隔離措施,被證明是控制新的疾病、降低死亡率,以及避免經濟和社會崩潰的最好方法,雖然至今仍然有人心存懷疑。
本書起源於調查歷史上的檢疫與隔離措施,直到Covid-19爆發,這段歷史瞬間成為現在式。作者以歷史寫作和田野調查的方法,採訪各地醫院和城市,並且回顧歷史遺址,細述瘟疫和隔離或封城的種種問題和面向。從1377年黑死病爆發,在杜布洛夫尼克(Dubrovnik)的第一次封城,一路談到今日的方艙醫院、炭疽郵件與太空污染。並指出:從古到今隔離的失敗,都是來自人們對於隔離本身的恐懼。
後疫情時代,隔離已經成為常態。在危急狀態下如何管控人口、個人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都是必須面對的議題。本書的翔實調查與分析,能夠帶給社會一個指引。
各界讚譽
「人類的歷史是一部不斷與疾病對抗的奮鬥史詩,隔離與檢疫雖為對抗重大傳染病的良方,但在疫情結束的曙光乍現前,強迫性的隔離、監控與歧視卻也撕裂了社會。閱讀此書使我們從經驗中學習成長,建立更具災害韌性的社會。」
——左宜恩,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兩位作者為這個主題帶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廣泛涉獵,不僅涉及傳染病,在他們雄心勃勃而又無縫的敘述中,更涵蓋了政治、農業、監視甚至外太空。」
——Jennifer Szalai,《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本書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為他們的研究深度,以及堅信隔離是一種強大而危險的武器,必須在未來更明智地使用……作者的文筆引人入勝,除了來源註釋之外幾乎沒有學術賣弄,這是一本異常強大的書。」
——Roger Ekirch,《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閱讀這本嚴謹周密的書,可帶給我們一些與直覺相反的安慰,它將過去18個月的與世隔絕和不確定性賦予了脈絡……令人無法放下的書。」
——安娜・奎因,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讀一本關於「隔離」的書,這可能是你今年最不想做的事情……但這本書卻讓我深深沉迷。它挖掘這個看似理所當然的概念背後的漫長歷史,是一本完美的大流行後讀物。以一種富想像力、深入淺出的方式來理解我們剛剛經歷的災難。」
——亞蕊安娜・雷博里尼,BUZZFEED
「對人類如何保護自己進行了引人入勝且及時的研究……馬納夫和特莉將他們的研究整理成一系列簡明而合乎邏輯的未來公共衛生危機建議,其基礎是對隔離如何影響人類的深刻理解。」
——《出版人週刊》Publishers Weekly(星級評論)
「嘆為觀止.....將這個當下主題的全球視野與生動詳細的敘述融為一體......但這本書更大的魅力,在於他們能夠將可能枯燥的話題帶入生活......對於該如何努力控制潛在的傳染危機,給出了具說服力的論述。」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星級評論)
「本書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論據,指出我們必須繼續改進檢疫與隔離措施,在公共衛生與人權之間取得平衡」。
——《紐約客》The New Yor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