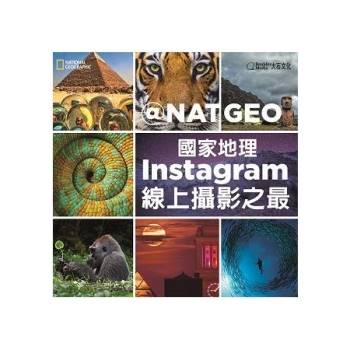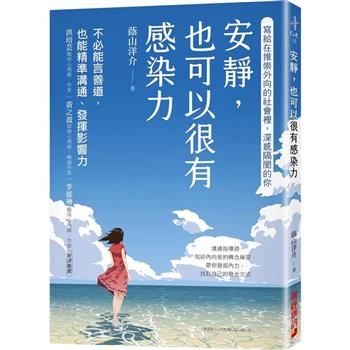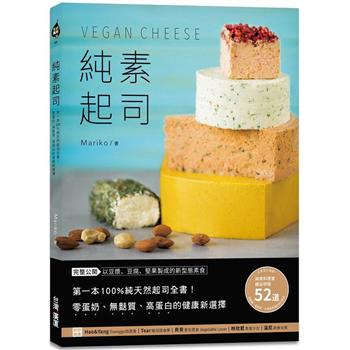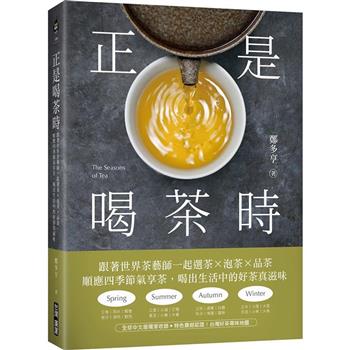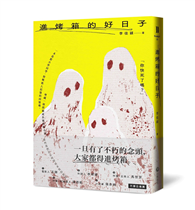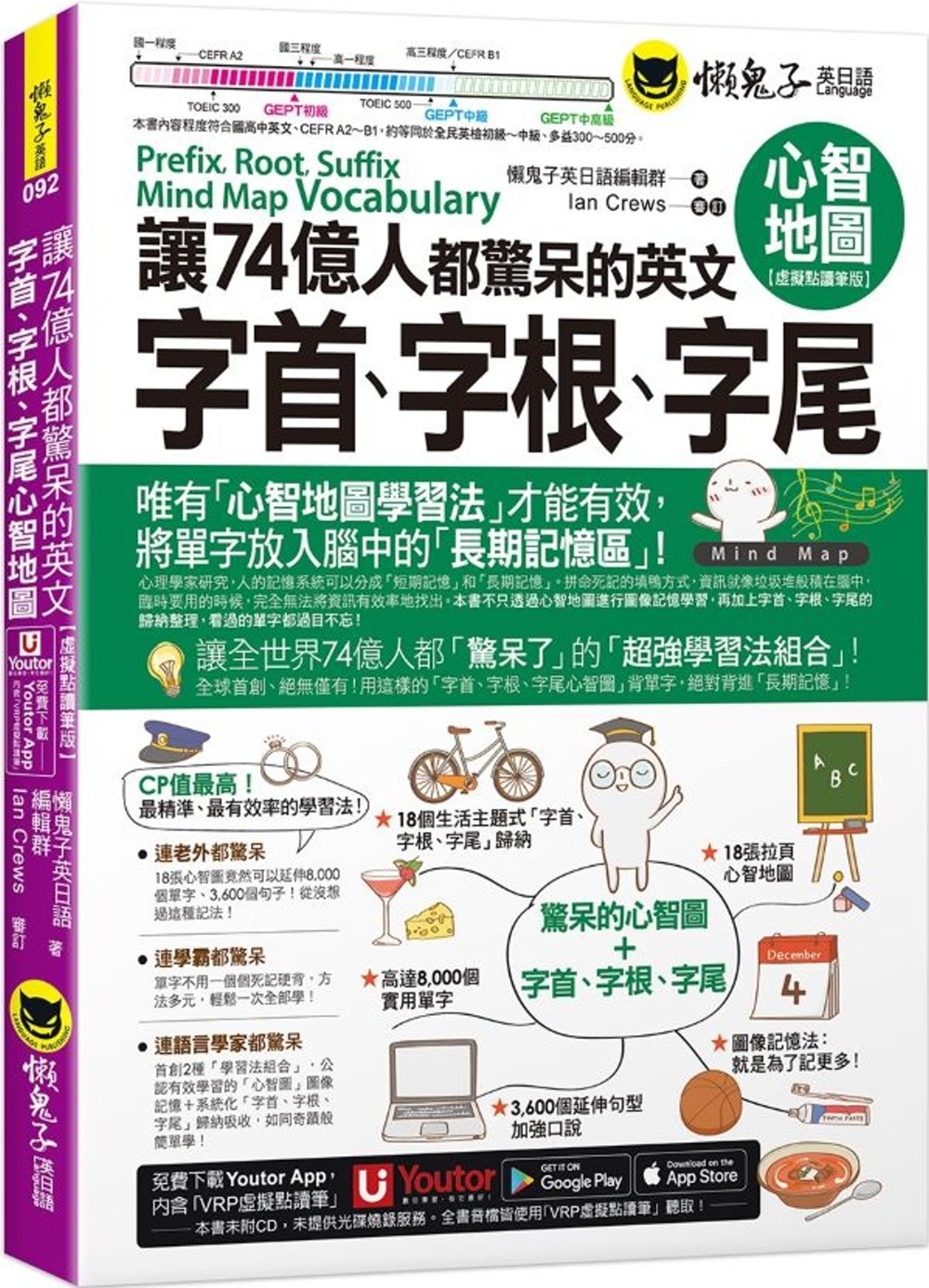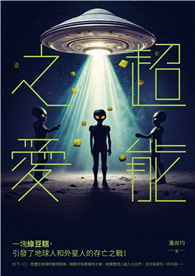《雖然不相見》摘文
PART ONE☉親愛的大人
親愛的大人,
請照顧好住在你身體裡的那個小孩。
親愛的你:
也不知道是什麼因緣,讓你讀到了這一本書。
它是一本書信集,而書信總是帶著私人的性質,尤其這書裡的每一封信,都是我過去真實信件的整理。
不過你完全不必覺得,買下這本書反映了你潛意識裡的偷窺欲,出版這一本書,也絕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壓抑已久的暴露癖。這一次書信的集結出版是因為,其實書信才是我寫作的主要方式,每一篇或長或短的文字,無論以什麼文體出現,當初都是為了傾訴而來。在有書案的對面,我總是假設,有一個他日會在文字中相遇的你,或者有一個始終都在的神明。
而真正的書信便是最直接的傾訴了,因為彼此相識的親密,加上無法相見的距離,從而有了一個坦誠自然又深入細緻的訴說空間,這裡有著面對陌生人時難以敞開的心意,也有面對面交談時無法保持的專心一致,而更多的還是一種交付。雖然你不在這裡,此時此刻的我,此時此刻的心情,還是要交由你來見證。
所以當你讀到了這本書,你便無端地有了一份見證者的責任了。
你呀,多麼無辜的你。
我呀,多麼幸運的我。
祝你,閱讀快樂!
多多
二○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於北京
我們的爛尾青春
在這陽光燦爛的日子,我的心仍奇怪地漆黑一片,
但是還能感覺到油頭粉面的你。
Dear Helping:
今天是週末,有點熱,有點懶的週末,正所謂「在這陽光燦爛的日子,我的心仍奇怪地漆黑一片,但是還能感覺到油頭粉面的你」,還記得這我們一起看過的電影裡的台詞嗎?所以我決定給你寫一封信。
你知道嗎?從我家的落地窗望出去,是兩棟爛尾樓,我現在的辦公室的落地窗外,也是兩棟爛尾樓,這番光景讓我不禁想寫一寫我們倆的爛尾青春。對啊,我們在熱情即將被燃燒的歲月裡分開,於是青春就那樣被生生地擱置,永遠沒辦法完成,卻也不可能推倒重建,誰能給青春一個說法呢?那些又寂寞又美好的青春。
首先我要向你坦白,決定要學小提琴,只是因為我覺得周華健的《不願孤單一個人》間奏部分用小提琴拉一定很棒,常常孤單一個人,在房間裡想像那個美好的情形。後來跑去跟我媽說,學音樂能夠提高智商、陶冶情操云云。我媽對我的智商和情操一向沒有信心,所以很快就同意了。教琴的老師說要兩個人一起學,我需要先找一個和我同樣有追求的人,第一個就想起了你。我忘了當時究竟是怎麼說服你的,更加不知道你對自己的情操到底有著怎樣的抱負,只是記得你爸給你買的那一把琴比我的高檔很多。那一天我開始懷疑,父母對我的人生到底有多重視,我認為自己的前途一下子渺茫了起來。多年之後,當在電影裡看到麥兜向麥太要一台電腦,麥太卻給他帶回來一個電飯煲時,我深深理解麥兜的悵然憂傷。
但是,仍然要感謝我們的父母沒有去揭穿那個,我們故意忽略的重要事實——從十五歲才開始吊兒郎當地學小提琴,其實已經晚了十二年。於是後來的那三年,從人民南到青泰里,才有了那兩個孤單又驕傲的身影,影影綽綽,驕傲得有點荒唐。
最荒唐的還莫過於那個每次經過都要上前來搭訕的陌生小子,他總是故作熟悉地上前,然後滿面堆笑地向我們打招呼:「嗨!又去彈小提琴啊?貝多芬哦!」你為什麼不告訴他,小提琴是用「拉」的,而貝多芬是彈鋼琴的呢?也許那時候,我們都只忙著驕傲了。
直到今天,我身上還有這種青春後遺症——越寂寞越驕傲。不同的只是,那時候為了滿足驕傲,選擇孤單,選擇不與任何人類比;而現在,開始能夠為發現「終其一生,不過都是一條孤獨的路徑」而感到驕傲。那時候再孤單,也還有你來見證,而現在,再驕傲也沒有誰能欣賞了。多麼殘忍的人生。
這些年近鄉總是情怯,尤其當你不在的時候。如果你在,你一定會明白那種無言,因為一切都已經改變,而人們卻仍然把記憶停留在你離開之前,你沒有辦法將離開後的歲月一一鋪陳,也懶得一再把離開前的日子綿綿複述,最後只能無言。如果你在,你一定不會追問,我也不必搪塞,我們只需要坐二十分鐘的船回到「松濤」,在那個幽暗破敗的咖啡廳,喝上一杯劣質的即溶咖啡,一切一切就都氤氳成了雲煙。
忘了是哪一年開始的,我們每一年春節都會來到這間冷冷清清的咖啡廳。是十三歲吧,那個青春痘加青春肥的年紀,那時候還沒有「小資」這個詞。而當時代終於趕上了我們的步伐,我們就顯得惡俗了。在二十二年前,我們可以放心地喝著咖啡,放心地做著幻夢,我們總是說:「等我長大了,我要……」忽然之間,我們就長大了,還來不及好好暢想一番。
記得那時候我們說,如果有一天,我們有了兩千塊錢,就要從肇慶打出租車到廣州買一包廣州臘腸回來。那是我們能想到的最肆意、無聊的花錢方法,最奢華的幸福。後來的人們更有想法,他們說有了錢買豆漿要一次買兩碗,喝一碗,倒一碗。
最後真的有了錢,你結婚,買房子,賣房子,又買第二套房子,你還救濟沒有錢的我。你結婚,離婚,又重婚,還一直照顧依然單身的我……我們卻都知道,沒有哪一輛出租車,能夠載我們回到咖啡廳的那個角落了。當你偶爾覺得不夠幸福時,希望能夠想起,我們那包幸福的臘腸。
最後,送你半闋詞,順便告訴你,我愛你如昔:
二十年江湖常為客,
都付與風吹夢杳,
雨荒雲隔。
昨夜重逢深院裡,
一種溫存由昔,
添多少周旋形跡。
祝好!
談笑
二○○六年四月七日於北京
PART TWO☉親愛的小孩
親愛的小孩,
請原諒那些,還沒來得及想好就長大的大人們。
親愛的你:
謝謝你的耐心,一直看到這本書的這一頁。
親愛的,我必須向你坦白,你前面看到的所有內容,其實都不是我出版這一本書的本意。這一本書,其實是為了你接下來即將讀到的二十三封給孩子的信而出版的。
在過去的兩年多裡,我一直在為一本兒童雜誌寫作,不定期地為那些給雜誌寫信的孩子們回信。我一直想將這些真實的來信與回信集結出版,但又擔心一本以兒童為主題的書,不足以引起你的注意,所以才增加了前面的一章,給大人的信。
我知道,這些孩子的來信裡所表達的問題,可能對你來說太幼稚,太可笑了;我知道,這些我給孩子們的回信,也可能對你來說太淺顯太囉唆了。但我還是那麼想要將其集結出版,因為,第一,我希望父母們能夠借此知道,孩子們原來需要獨自面對那麼多困惑,而這些困惑他們往往不會向父母傾訴;第二,我更希望的是,每一個大人都能藉由閱讀這些信件而重新觀照自己的內在孩童,重新回到那個當年,告訴曾經困惑的自己,一個足以療癒的答案。
相信我,哪怕事隔經年,你仍然有機會與那個小孩對話,你的苦,你的痛,你心中的那個受傷的小孩,需要你,你還有機會擁抱他,他的痊癒才是你真正的成長。
你要相信我,親愛的,因為就是在那些給孩子們回信的當下,我與我的內在小孩,第一次相擁而笑。
祝你讀後也微笑。
多多
二○一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於印度菩提迦耶
願你不失單純,不落世故
年少時愛意萌動,往往寄情於人,暮年後多淡泊透徹,則寄情於山水,
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對現實的一種跳脫,對美好的一種描摹。
多多姊姊:
最近有個問題一直困擾我。我是一名初中女生,我在看一本歷史書的時候發現了一張貴族的照片,其中有一個男子氣質非常吸引我,然後我每天就想去看那本書上的照片。漸漸地我發現我好像喜歡上了他,每次一停下來就會想著他的樣子和氣質,這樣做事就不專心了。但他是一戰以前的人啊,我也見不到他,一想到這個我就很難受,我不知道時間久了能不能忘掉,可我不想讓這件事影響我的生活,我該怎麼辦呢?
請您幫幫我!
啊呀呀
親愛的啊呀呀小姐:
你好!大約十幾、二十年前,還是高中女生的我,偶然間看到半闋詞「心灰盡,有髮未全僧。風雨消磨生死別,似曾相識只孤檠,情在不能醒。」竟愛上了這一份堅執的迷情,人生都似乎還沒開始的我,竟也有了一種奇怪的「曾經滄海」、「千帆過盡」的喟嘆。因此,我也愛上了這首詞的作者——清代詞人納蘭性德。
那時候納蘭性德並不是中學生所熟悉的詞人,他的作品或許因為多為個人情感的表達,又充滿了對隱士的豔羨,對佛老的熱愛和淡泊功名富貴的思想,大概並不適合鼓勵年輕人心懷家國的中學教科書,而互聯網在那個時候是沒有的。所以當我與同桌說起納蘭性德的時候,她只茫然地回答我:「什麼?誰?我只知道阿蘭•德龍。」可我就是這樣默默地愛上了一位古人。
你說,那時候的我是不是很傻呀,但是這份傻氣,並不是什麼罪過,更談不上影響生活了。寄情,只不過是一種在現實之外的別處安放情感與熱愛的抒發方式罷了。年少時愛意萌動,往往寄情於人,暮年後多淡泊透徹,則寄情於山水,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對現實的一種跳脫,對美好的一種描摹。唯一的「不應當」,只是「沉湎」而不是「幻想」本身——沉湎於幻想,和沉湎於現實,都是一種深陷和不可自拔,都同樣失去了自由,失去了生命中更多的可能性,那才是真正的影響生活呢!
親愛的啊呀呀小姐,也許當你長大後,你會發現人們淪陷於現實生活,失去了對美好的想像,但願你還能夠想起,你曾經那麼真摯地愛過一個從未謀面的貴族男子,但願你不失單純,不落世故。
對了,十幾年之後,我才再次找到納蘭性德的另外半闋詞,我把它用自己的方式演繹成了一首現代詩,權當是對我的「初戀」的一種祭奠吧,分享於你——
心灰盡,有髮未全僧。風雨消磨生死別,似曾相識只孤檠,情在不能醒。
搖落後,清吹那堪聽。淅瀝暗飄金井葉,乍聞風定又鐘聲,薄福薦傾城。
——納蘭性德
連嘆息都只得輕輕
怕吹落心尖的塵埃啊
怕塵埃蒙住了疏落的白髮
風雨未能沾染的灰藍袈裟
今夜被一缽不期而至的思念淋透
我以為我早已經醒來的
原來不曾
聽不得風的肆意
因為像極了我的任性
像極了你的無所用情
也許正因為如此
我們才是最契合的一雙?
你的撤退成全了我的追趕
但風終於還是讓滿樹的期許零落了
零落在我為你一次次放空的那口小小的井
怎麼忘了
即便空空如此
還是無法承載你
如同深海的寂靜
是我福薄
寫於二○○九年八月三日深夜的北京
祝福你親愛的啊呀呀!
扎西拉姆•多多
二○一四年一月七日於北京
|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雖然不相見(遠距相見版)的圖書 |
| |
雖然不相見【遠距相見版】【金石堂、博客來熱銷】 出版日期:2022-01-06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0 |
Books |
$ 300 |
Books |
$ 300 |
中文現代文學 |
$ 334 |
中文書 |
$ 334 |
小說 |
$ 342 |
現代小說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雖然不相見(遠距相見版)
而現在,我們需要不斷地彼此鼓勵,
才能不讓世界改變自己。
無論你多愛、多依賴一個人,請一定要保有你自己的人生:
你的朋友,你的愛好,你的技能,
甚至你的軟弱與你的愚笨也要好好惠存。
★馮小剛電影《非誠勿擾2》片尾獨白的作者
扎西拉姆‧多多 最美、最真的告白
透過文字與你相遇 與你一同回歸純真 療癒自心
◎不相見的時代,與你遠距相見◎
★這本書是寫給大人跟小孩看的——
如果你是大人,請照顧好住在你身體裡的那個小孩。
如果你是小孩,請原諒那些,還沒來得及想好就長大的大人們。
人與人之間,雖然不相見,但只要有了心靈交流的管道,就像相見了。因為彼此相識的親密,加上無法相見的距離,從而有了一個坦誠自然又深入細緻的訴說空間。
其實書信才是作者寫作的主要方式,以書信的方式呈現,是為了傾訴。書信裡有著面對陌生人時難以敞開的心意,也有面對面交談時無法保持的專心一致,而更多的還是一種交付。誠如作者說:「雖然你不在這裡,此時此刻的我,此時此刻的心情,還是要交由你來見證。」
本書有:作者給大人的信、作者回覆小孩的信,以及作者給自己的信。
第一部分「親愛的大人」是寫給大人的信。作者對大人們說,「請照顧好住在你身體裡的那個小孩」,希望大人們在成熟中也能不失真性情,你可以從這些書信中,見證了作者的心情,同時見證了自己的心靈。
第二部分「親愛的小孩」則是給孩子的回信。從孩子遇到的困擾與問題中,作者對現在以及曾經是孩子的每個人說,「請原諒那些,還沒來得及想好就長大的大人們」,希望大人都能藉由閱讀這些信件,而重新觀照自己的內在孩童,重新回到那個當年,給曾經困惑的自己一個足以療癒的答案。
穿插的部分是作者「給自己的信」,短短的、如詩的信,搭配作者行腳途中的攝影作品,給你沉澱下來、回歸內心的空間。
真誠感人的文字心靈與深具意境的攝影畫面,在你閱讀時,會交織成此刻你生命中,可以好好惠存的風景。
作者簡介:
扎西拉姆‧多多
本名談笑靖,女,漢族人,生於1978年。著有《當你途經我的盛放》、《喃喃》、《以何之名》。
FB:扎西拉姆‧多多(台灣交流平台)
微博:www.weibo.com/dorophy101
博客:blog.sina.com.cn/dorophy101
章節試閱
《雖然不相見》摘文
PART ONE☉親愛的大人
親愛的大人,
請照顧好住在你身體裡的那個小孩。
親愛的你:
也不知道是什麼因緣,讓你讀到了這一本書。
它是一本書信集,而書信總是帶著私人的性質,尤其這書裡的每一封信,都是我過去真實信件的整理。
不過你完全不必覺得,買下這本書反映了你潛意識裡的偷窺欲,出版這一本書,也絕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壓抑已久的暴露癖。這一次書信的集結出版是因為,其實書信才是我寫作的主要方式,每一篇或長或短的文字,無論以什麼文體出現,當初都是為了傾訴而來。在有書案的對面,我總是假...
PART ONE☉親愛的大人
親愛的大人,
請照顧好住在你身體裡的那個小孩。
親愛的你:
也不知道是什麼因緣,讓你讀到了這一本書。
它是一本書信集,而書信總是帶著私人的性質,尤其這書裡的每一封信,都是我過去真實信件的整理。
不過你完全不必覺得,買下這本書反映了你潛意識裡的偷窺欲,出版這一本書,也絕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壓抑已久的暴露癖。這一次書信的集結出版是因為,其實書信才是我寫作的主要方式,每一篇或長或短的文字,無論以什麼文體出現,當初都是為了傾訴而來。在有書案的對面,我總是假...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PART ONE 親愛的大人
我們爛尾的青春
小指輕挑之微薄
只有你知道我的裝瘋賣傻
不問前程的心之所向
那觸手可及的幸福
人有人的天命,神有神的慈恩
走向自己的深處
人山人海,相見離開
原鄉與邊疆
語句及辭章,其實都是屍骸
一切人始終會走向同一個方向
做一個精神病康復者
這裡還有我們
那個大齡失業女青年
我們都要好好的
這是一個充滿懷疑的時代
兩條腿
做個有錢人
繼續做就是了
我知道,我懂的
一件正確的事
PART TWO 親愛的小孩
大米小姐的小世界
少女的皮鞋
當你傻傻地站著
告訴他們你是誰
我很在乎
...
我們爛尾的青春
小指輕挑之微薄
只有你知道我的裝瘋賣傻
不問前程的心之所向
那觸手可及的幸福
人有人的天命,神有神的慈恩
走向自己的深處
人山人海,相見離開
原鄉與邊疆
語句及辭章,其實都是屍骸
一切人始終會走向同一個方向
做一個精神病康復者
這裡還有我們
那個大齡失業女青年
我們都要好好的
這是一個充滿懷疑的時代
兩條腿
做個有錢人
繼續做就是了
我知道,我懂的
一件正確的事
PART TWO 親愛的小孩
大米小姐的小世界
少女的皮鞋
當你傻傻地站著
告訴他們你是誰
我很在乎
...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