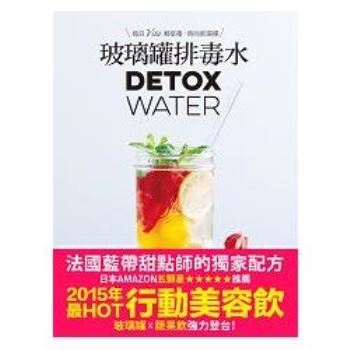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7 項符合
溫州街的新疆大院子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303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315 |
散文 |
$ 355 |
中文書 |
$ 355 |
社會人文 |
$ 356 |
現代散文 |
$ 356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396 |
現代散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溫州街的新疆大院子
哈登旦 歐德勒瑰 哈德勒雅尬 奇奇 哈德勒雅尬 歐尼格森貝 歐……
鄉音爆發在氈帳裡
淚流在族人的親情中
十七世紀傳唱在土爾扈特汗國草原上的歌,經數百年的顛沛流離,在台北溫州街的新疆大院子裡重新響起……
席慕蓉 專文推薦
作者簡介
海中雄
1956年生於台北市溫州街的新疆大院子裡,祖籍蒙古土爾扈特部,祖先世居游牧於天山、阿爾泰山。十六世紀末,土爾扈特人由新疆移居至蒙古欽察汗國所屬、裏海北岸的伏爾加河大草原;直到十八世紀,一方面迫於俄國凱薩琳女王的欺壓,一方面清廷剛平定「準噶爾之亂」,強人已除,族人也不禁興起「逐鹿」故土的雄心。1771年1月5日,由喇嘛占卜選定的東歸「吉時」已到。無奈上蒼作弄,那年冬天伏爾加河竟沒有凍結,西岸族人無法渡河相會,東岸的族人卻已殺官造反,不得不走。在兵源減半的情況下,這群扶老攜幼、帶著金銀細軟、趕著數十萬牲口的隊伍,哪裡躲得過沿途俄軍的追擊,以及剽悍的哥薩克等草原民族的劫掠呢?八個月後,族人終於抵達伊犁,十六萬餘人僅存六萬多人,其中就包括了其先祖王津家族,這就是歷史所說的「最悲慘的遷徙」。原本的爭雄野心成了「歸順」,乾隆皇帝還喜孜孜立碑,題為「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1920年代,祖父海穆從阿爾泰山的科布多移居新疆。1949年,父親海玉祥翻過帕米爾高原,經過巴基斯坦再從印度轉來台灣,定居在溫州街的新疆大院子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