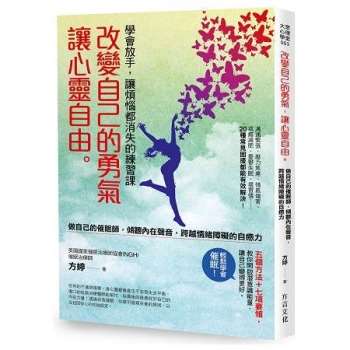前言
你可以擁有一定程度的戶外覺察,也就是偵測和判讀自然界線索的本能能力,雖然這種能力在以前很普遍,但現在卻很罕見,許多人甚至將之稱為「第六感」。透過演練建立聯繫的能力,我們可以透過感官察覺到的所有徵兆,幾乎不假思索就推斷出結論。在本書中,我將告訴你如何從星星和植物看出方位,從林地的聲音預測天氣,並從動物的身體語言立即預知牠們的下一個動作。
對這類思考方式不熟悉的人,可能要等到我特別指出來,才會知道自己「遺漏」的步驟。我們變得如此疏離這種感受周遭環境的方式,導致難以相信我們能在戶外辦到,不過在較熟悉的環境中似乎就不那麼奇怪了。
你曾經感覺到有人在看你,之後發現你的感覺是對的,但卻無法解釋自己當時為什麼知道嗎?
想像你坐在咖啡店裡,背對窗戶。你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有人在你身後看你。你的感覺可能是對的。如果你朋友開車慢慢經過時,想從車窗裡叫你,這個舉動可能會顯示在咖啡店裡其他人的臉上或身體語言中——也許服務生幫你倒咖啡時抬頭了。當天稍晚,你朋友會打電話給你,證實你被他看著。
心理學家已經證實,我們接起電話聽到另一頭的人開口說的第一個字時,就能相當精準判定對方的情緒狀況。我們用耳朵聽,但我們的大腦會迅速調出人生經歷、我們對通話者個性和狀況的瞭解、通話時間處於晝夜,以及其他無數提示,在「你好」這個詞之上推論出更全面性的結論。不分晝夜,戶外都有無數對我們充滿具有更深層意義的低語。只是我們聽出弦外之音的技巧有點生疏了。
第六感並非神祕莫測;那是一種專業直覺,一種經過磨練的能力,可以把我們感官所提供的線索串連在一起,對環境有更完整的見解。而外在的線索比我們所意識到的還多。過去一秒內,你的感官已經接收到一千一百萬筆資訊。要有意識地分析所有資訊需花上好幾年,所以幾乎所有資訊都被我們的大腦無聲無息地過濾了。但是如果你的大腦接收到任何奇怪、美好或有威脅性的資訊,你會發覺有些事情值得你多加留意。
最近的研究與暢銷書讓許多人相信我們能憑直覺判定當今的情況。
看著附圖,想像自己穿越馬路。你會看到三輛車,其中一輛比較靠近你,可是你需要注意最遠的那輛。但在現實生活中,你會憑直覺做出這個決定,不需要任何計算或測量。
沒人想過我們在大自然中依然有這樣的能耐。說來諷刺,因為憑直覺判定情勢的能力源自我們在更野蠻的環境中存活的需求。在人類歷史上的大部分的時間裡,我們都曾用這種思維經歷野外生活,而演化論證實,若少了這項能力,我們便不復存在。在早期,若有人需要仰賴費力思考來弄清楚周圍發生的事情,便會明顯輸給那些能察覺到附近有敵人、身後有危險的掠食者(predator)或前方可能有一頓大餐的人。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電視劇組曾帶我一同前往地底深處。我們一路蜷伏,穿過黑暗又曲折的隧道,進入威爾斯(Wales)北部一處板岩礦場。四周溼冷,沒有任何線索可以讓劇組一眼辨識,可能這使得他們詢問我能否分辨現在面對的方向,以試探我的能耐。
我看著潮溼的石頭,僅憑著頭燈照射出的燈光,回答他們「東方」。
對那個礦區非常熟悉的安全顧問確認了我的答案是正確的,但是他也承認他跟其他人一樣,對這個「第六感」感到困惑。過了愉快的幾分鐘後,我告訴他們,我注意到板岩的紋理,即地質學家所謂的「傾角」(dip)。所有沉積岩一開始都是水平沉積的,可是經歷數百萬年之後,地質力量會將它彎曲、傾斜;許多岩石最後會出現明顯的角度,並有其趨勢。我在威爾斯谷看到我們周圍的板岩向南方朝上傾斜,因此找到我們在地底深處的方向。
在那個情況下,我有意識地使用「線索」回答一個簡單的問題。幾十年來,我在職業上仰賴這個方法,我大部分的著作都著重在這種邏輯性的推理思考上。不過,當大腦採用這個程序並走捷徑時,可能會發生一些更有趣的事。當我們離開礦場時,大家都能立刻察覺到方向;從板岩上看得一清二楚。認為我們可能做不到的想法近乎可笑。
以最基本的程度而言,我們還沒完全喪失這些技能。想像一下,由於窗簾厚重,你在一間全黑的房間醒來,然後你聽到外面的公雞啼叫。也許不用花太多力氣思考,就能知道外面天色已經愈來愈亮。狗吠聲在尋常時間如常出現,告訴我們郵差已經到門口了。
可是相較於我們在戶外時的頭腦能耐,這些範例顯得很孩子氣。本書與我們在此領域的非凡能力有關,而這項能力在我們允許之下萎縮了,幾乎被現代的生活型態所遺忘和碾壓。
可是我們怎麼知道它還能恢復呢?
因為有少數人還堅持著這項技能,他們主要是出於需要或期望,沉浸在鑽研特定生物或某些景色。世界各地的原住民部落、專業獵人以及漁民常保有卓越的能力,舉起火炬提醒我們仍可運用這項能力。
我曾與婆羅洲(Borneo)的達雅(Dayak)族人席地而坐,他們向我解釋將有一隻鹿會出現在山頂,不久之後,當我在預測的地點與山羌四目相接,我感到驚訝無比。仔細討論後我才明白,顯然達雅族人下意識注意到石頭上的鹽、蜜蜂、水源、一天中的時間,以及森林中空地之間的關聯性,以上都顯示鹿會在那個時間現身來舔鹽。
剛果民主共和國(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的俾格米人(Pygmy)習慣聆聽蜂蜜。他們知道,當有蜂蜜時,有一種與變色龍有關的動物,其聲音會略有變化;他們也能察覺到花豹在注視他們。有形的線索就在地面的足跡上,可是若缺乏想像力來調查,便難以將它們連結到森林裡的掠食者。相反地,他們學會將某些痕跡連結到花豹可能的休憩地點。在典型的花豹休憩地點附近若出現新痕跡將帶來危險。而他們察覺到自己被注視時,通常都是對的。
因紐特(Inuit)獵人有一個詞,quinuituq,意思是等待某事物出現時所需的深厚耐心。透過這份耐心,他們與土地發展出一種超越概略分析的關係。北極專家貝瑞.洛佩茲(Barry Lopez)稱因紐特獵人不只是聆聽動物或觀察牠們的蹄印。他們把眼前的景色像衣服一樣「穿在」身上,並與之進行「無言的對話」。我得強調這是科學而非神祕主義。那是一項古老的技能,不是新時代運動(New Age),是我們生來便實踐的。即便沒有天氣預報,很多人也知道什麼時候開始下起陣雨或較久的暴雨。他們也許很難解釋原因,可是我們愈來愈習慣天空出現代表將落下陣雨或其他雨勢的變化。我們的祖先不只能看出地景的大致變化,還瞭解更細膩的部分,像是酢漿草葉在快下雨時捲起的方式。
一名漁夫或許能預測鱒魚跳出水面的確切位置,但一開始很難說明原因。事後回想,她理解到她的眼睛和大腦一起合作,注意到有一片雲擋住陽光。黑蚋(black gnat)因陽光不足而從天而降,鱒魚就浮至水面覓食。但垂釣者已經察覺到鱒魚會跳出水面的位置。
重要的不是位置,而是沉浸感。最近我跟大衛‧巴斯克特(David Baskett)共處了幾個小時,他是英格蘭東部海岸保護區的一名嚮導。我們沿著歐洲最長的卵石岬(shingle spit,一種突出的鵝卵石灘)頂端步行,當時水面上有一對黑影吸引了我們的目光。灰海豹在一條延伸入水的突堤(groin,一種保護海岸的海堤)盡頭附近玩了一分鐘;接著大衛說:「牠們現在會上岸。」
海豹花了一點時間,不過很快就不雅地跟鵝卵石纏鬥在一起,拖著身體往岸上移動。
「你怎麼知道牠們會爬出來?」
大衛一臉困惑。
我又再問了一次:「你怎麼知道牠們會選在這時候,在這個位置爬出水面?那是每天的習慣嗎?」
「嗯……不是。」大衛看著自己的腳。「嗯…其實我不知道,真的。」
十分鐘後,我們聊起鳥類與交通工具的關係。汽車、貨車,甚至公車都不會驅散保護區的鳥兒,但是車門打開的那一瞬間,牠們就四處飛散了。當我們俯瞰一池泥塘(Scrape,充滿淤泥與淺水的區域),我再次問了他海豹的事。
「我想是狗的關係。」大衛說。
「那裡有狗嗎?」我試著回想,「可是狗不會把牠們嚇跑嗎?」
「你以為會,但其實海豹喜歡爬上岸觀察牠們。我想我們到那裡時,那隻狗就已經在了。或許我因此認為海豹會出現那樣的行為,我不確定。」
這項能力仍有一部分保留在我們與家畜之間的關係中。當你在都市裡的公園溜狗時,很容易能從狗轉彎的方式看出從後方靠近的人有沒有牽狗。花點時間以這種方式享受戶外經歷,可以幫助我們開始重建我們失去的第六感。若我們把這當作戶外經歷的例行環節,我們很快就會發現我們的大腦開始掌管一切,打造出捷徑,讓我們無需有意識地思考就能推斷出結論。我們不再需要思索每個步驟,因為我們的大腦已經代勞了。我們察覺到身後有一隻狗,我們感覺明天的天氣會很好。其實只差一步,這樣的程度就能變成察覺我們會在附近發現什麼,或動物接下來會有什麼行為。
本書囊括我過去的經歷,不過主要目標是讓讀者知道如何自己發展這種覺察。中心主旨是「鑰匙」(keys),也就是自然界中值得我們注意的一系列模式和事件。為了讓這些事件更好記,我賦予它們各自的名稱——例如「剪切」(The Shear)。全書會由淺入深,逐步介紹從簡單到較進階的能力。自然界中的這些鑰匙將引領你提升覺察能力,找回我們失去的感覺。
在這本書中,我將畢生對戶外覺察能力的追求帶到頂峰,這一直是博物學家的目標。那門科學一直在探索自然界的意義,我對這項悠久的傳統心懷感激。十九世紀的自然作家理查德‧傑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相信雀蛋上的棕色、綠色和紅色斑點帶有訊息,他發現這個字母表與「亞述(Assyria)的奇怪碑文」一樣迷人又令人費解。所有博物學家都未能攀上最高峰,但我們還是啟程,希望帶著謙遜,雖然謙遜永遠不夠,站上某個未知的高原一睹大自然。在星空之下,穿越海洋、森林和沙漠的旅程,引領我接受終極挑戰:深度、直觀地瞭解切身的環境,那才是真正的地方感。
我們周遭環境中的事物很少是隨意分布,只要稍微練習,我們就能學會察覺到可能使我們感到吃驚的事情。釐清這種情況發生的原因,會開起一種既新穎同時又非常古老的體驗環境方式。這比幾世紀以來常見的戶外體驗還要更激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