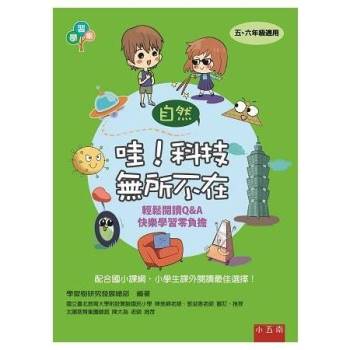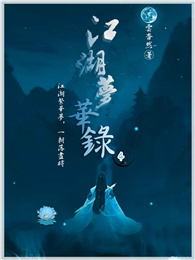mamazangljan王國子孫分家的衝擊,讓部落的天空充滿不祥的耳語,vuvu樂歌安族老不以傳統方式分家後一病不起,轉眼很快過世。排灣族古葬禮當下,鷹族一隻接著一隻出現上空環繞,象徵祖靈護送樂歌安回到大武山。年輕的孫女魯真倉促繼承族長,但族裡因為外教的影響,Pulingav女巫繼承之路早已斷裂,傳統的安靈儀式只能拜託隔壁部落分支的女巫召喚祖靈與樂歌安亡靈到來。
在樂歌安的遺物中,魯真發現一柄古老木雕梳子與簪子,她問到ina吾艾——樂歌安從小一起長大的鄰居友伴,牽動一世紀的部落三代原住民女性們強韌的生命史就此打開……
本書特色
以母系認同為核心,由個人女性生命經驗出發,連結家族史、部落史的女性經驗與處境,提出對臺灣殖民歷史、族群與父權體制的深刻反思與觀照的小說創作。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女族記事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308 |
中文現代文學 |
$ 343 |
中文書 |
$ 343 |
小說 |
$ 351 |
中文現代文學 |
$ 351 |
現代小說 |
$ 351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女族記事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利格拉樂.阿[女烏] (Liglav A-wu)
漢名高振蕙,既是排灣族也是外省二代,數十年來始終在身分認同的河流裡跌跌撞撞,流離在父系與母系的家族故事中,著有《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紅嘴巴的vuvu》、《穆莉淡Mulidan:部落手札》、《祖靈遺忘的孩子》等散文集,以及《故事地圖》兒童繪本,編有《1997原住民文化手曆》。近年來投入「原住民族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述歷史影像紀錄計畫」的拍攝工作,完成共15位原住民族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實紀錄片。另外也開始著手小說創作,2024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女族記事》(晨星)。
利格拉樂.阿[女烏] (Liglav A-wu)
漢名高振蕙,既是排灣族也是外省二代,數十年來始終在身分認同的河流裡跌跌撞撞,流離在父系與母系的家族故事中,著有《誰來穿我織的美麗衣裳》、《紅嘴巴的vuvu》、《穆莉淡Mulidan:部落手札》、《祖靈遺忘的孩子》等散文集,以及《故事地圖》兒童繪本,編有《1997原住民文化手曆》。近年來投入「原住民族政治受難者暨相關人士口述歷史影像紀錄計畫」的拍攝工作,完成共15位原住民族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紀實紀錄片。另外也開始著手小說創作,2024年出版首部長篇小說《女族記事》(晨星)。
目錄
〔推薦序〕穿越煙霧,向光前行 楊翠(現任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楊逵文教協會理事長)
〔自序〕從散文到小說的爬行之路
〔導讀〕想對自己說的故事 瓦歷斯.諾幹
一、樂歌安
檳榔
外省人
死亡
夢境
召喚
二、阿露伊
工地
戀情
女人之間
三、魯真
界線
禮物
秘密
四、爾仍
戰爭
紋手
重逢
〔自序〕從散文到小說的爬行之路
〔導讀〕想對自己說的故事 瓦歷斯.諾幹
一、樂歌安
檳榔
外省人
死亡
夢境
召喚
二、阿露伊
工地
戀情
女人之間
三、魯真
界線
禮物
秘密
四、爾仍
戰爭
紋手
重逢
序
作者序
從散文到小說的爬行之路
其實這篇小說一開始,長得並不是小說的樣子,過去長期書寫的文類,大多以散文或報導文學為主,因此當累積的材料和口述愈來愈多的時候,我的散文也就愈寫愈長,最長的篇幅高達四萬多字,事後在閱讀時,自己都覺得困惑不已,不知道該如何定位這些文章。又因為覺得不曾嘗試寫過小說,不懂得小說技巧,因此限縮自己的書寫在「真實的散文」中,始終沒能寫出更具有想像空間的作品。
此種類型的作品大約有近十篇,短則兩、三萬字,長則四、五萬字,每每沉浸在田野的口述中欲罷不能,又觀照自身的成長經驗,逐漸長出了一部家族史的樣貌,只是單純的家族史又顯得故事薄弱,於是這些稿子在約十年前獲得國藝會補助創作之後,就此被收入抽屜深處不見天日。
後來有機會重新進入校園讀書,在東華大學華文所學習時期,修習了小說課的相關課程,也因此對於小說的樣貌有了更清楚的理解,於是,重新翻出這些沉埋已久的「長篇散文」,試圖以小說的思維將這些文章改寫。改寫的工程是龐大的過程,何況又是十年前的語境,因此在改寫過程中多次想放棄,幸好在女兒麗度兒作為第一讀者的鼓勵下,終於慢慢尋回當初書寫的意境,再參照多年來不斷蒐集的田野資料,轉寫完成這一部小說。
故事的原型來自我的母族部落,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口述,當然也摻雜了鄰近幾個部落的歷史,每當回想起口述的內容,我總慶幸自己還有機會,聽見那些溘然長逝的vuvu 們說故事,若是再晚個幾年,這些綿長的記憶,大概也就隨著祂們入土長埋了。
我聽過許多不同的部落遷移版本,有來自本家部落,有來自其他部落,各自的觀點略有不同,但是期間總是存在著幾位重要的人物,那些人物往往是某個mamazangiljan的族老,或是部落裡的pulingav,在外來殖民政權的非常時期,做出了相對應的非常決策,而這些決定也直接影響了現在的部落樣貌與構成。
我想像著那樣的年代裡,那些擁有決策權力的vuvu們,在面對時代劇烈變化時,心裡的掙扎與無奈。當初的他們必然無法想像吧?!當那些美麗的神話變成失落的遺珠,嚴謹的信仰與傳統成為學術上的詞彙,舌尖上吐語如珠的優美音韻被另一種通用語言取代,部落似乎仍然是部落,但部落也已然不再是部落。
我在每一年返回部落時,總是會挑選一個傍晚,循著樂歌安的步履,睜大已然退化的雙眼,試圖一步步地踩著她遺留的足跡,彷如她巡視傳統領域一般地踱步,試想歷經日領時期、國民政權來到西元2000 左右的現代,如何運用她所有承襲的知識系統,思考現代化下的各種疑難雜症,例如遺產的爭議。那是這篇小說的起始,也是我第一次透過外婆得知,其中竟有如此巨大的文化脈絡與邏輯。
我甚至起心動念前去詢問母親,在自己雙手上紋手的可能性,母親睜著愈來愈排灣化的熠熠大眼,一臉不可思議地尖聲回答:「妳沒有資格,妳的身分不允許,何況,現在部落裡已經沒有人會紋手了!」我悵然若失卻沒有捨棄的繼續追問:「那⋯⋯如果我去找會紋手的部落,或是⋯⋯拿圖案去刺青呢?」母親波浪鼓似地搖著頭,一臉緊張的警告我:「絕對不行,妳是平民家族,就算有人會,那也是傳統不允許的,妳可別給我作亂,這會受到祖靈懲罰的。」最後一句話,徹底粉碎了我的奢念。
現實無法達成的奢望,於是只能在小說裡完成了。我開始翻閱文獻,找尋各時期被記錄下來的紋手圖案,細細描繪在筆記本裡,註記上研究者透過口訪得來的解釋,逐一去理解每個圖紋的代表和意義。並在A4大小的純白紙張上,描繪自己的左右手,像玩樂高積木似地,繪出一張張不同圖紋組合的紙上紋手,以滿足自身對傳統的嚮往。
卻也在這一張張圖描中,感受到愈來愈多的回應,在敲打鍵盤的時候,飛快地從手下呈現出一幕幕場景。
於是口訪、文獻和想像就一起在小說裡盡情徜徉了,無論是檳榔不離身的吾艾、身分尊貴的樂歌安、或是現代繼承人魯真,又或者是威嚴的爾仍,與流浪在都市、眷村之間的阿露依,各自鮮活而立體的活出自己的樣子。我穿梭在時光隧道之中觀看,試圖在這將近一百年的空間裡,為她們也為自己撐出一個敘事的空間,努力展現不同世代之間的樣貌。
支撐出一百年的小說空間,之於我一個小說新手而言,無疑是困難的,我不斷揣摩與推論已然失去的時代,又必須理解活在傳統裡人物的思維,也幸好有許許多多的人物原型,不斷供給我養分和能量,才得以讓這個故事能夠生存下來。於是,我更加好奇部落裡那些年逾九十歲以上的耆老們,他們的腦海裡留存著的部落,究竟長得是什麼樣子?那些他們念念不忘的人物與事件,還能以何種記憶模式繼續留存下來。
小說之路既已開啟,便使人念念不忘。完成這一部小說之後,我才發現仍有許許多多的故事等待書寫,期待這本小說面世的同時,我已然開啟了第二本小說的序幕,站在散文與小說的中線上,期待自己既能掌握小故事為散文所用,又盼望能因此展開敘事的小說長河,源源不絕地在書寫世界裡,既是累積又是創造的完成自我追尋,以及一直以來的創傷療癒,以字字句句縫合人生的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