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風乃啊,妳知道『人魚傳說』嗎?」
小學四年級暑假,我坐在緣廊邊吃西瓜。奶奶就坐在我身邊,一道蚊香燃起的白煙,就在我們之間朝湛藍的天空飄去。
「不知道。」
如果是人魚我還知道,人魚傳說是什麼啊?
專心啃西瓜的我停下手,抬頭看奶奶。奶奶面帶溫和表情,慢慢舉起手捏掉沾在我頰邊的西瓜籽,輕聲說:「這樣啊。」
奶奶視線看著正面的庭院,瞇成一線的眼睛前方,好幾株朱槿綻放朱紅色的花瓣,正在做日光浴。
「這是石垣島流傳的古老傳說──」
石垣島距這個小島約一小時船程,雖然同為沖繩縣離島,石垣島遠比這個沒有超商也沒有燈號的島更繁華。
「很久很久以前,有個漁夫到外海去。那天很不可思議地大豐收,聽說捕到教人痛快的大量漁獲。」
奶奶沉穩的音調自然地流入耳中。父母和學校老師說的話,不管多麼想要專心好好聽都聽不進去,但奶奶說出的每句話都會自然地滲透身心。
「所以他忘了時間,非常專注捕魚。接著,感覺漁網出現了從未出現過的手感。漁夫想著捕到大獵物了,相當興奮地把漁網拉起來。接著發現漁網裡是個上半身是美女,下半身是魚尾的人魚。據說人魚不停哭泣。」
腦海中想像被魚網困住而哭泣的人魚,讓我也跟著難過起來。我把吃到一半的西瓜放回盤子上,身體轉向奶奶。
「因為她以為自己一定會被吃掉,人魚好可憐喔。」
「人魚當然拜託漁夫放過她,但漁夫也是第一次看見如此罕見的生物,他說著可以大賺一筆,不聽人魚的哀求。」
「好過分。」
「所以人魚說了:『如果你放過我,我就告訴你大海的祕密。如果不知道這件事,你們會遇到大麻煩。』漁夫很煩惱,但他又很在意是什麼事,只好放過人魚。」
「啊,太好了。」人魚得救了,可以回家了。
「回到大海的人魚相當開心,在漁船旁游了幾圈之後這樣說:『明天日出後,會出現把整個小島吞沒的海嘯。』說完後就回去大海了。」
「海嘯是那個海嘯嗎?不久前電視上一直報的那個。」
去年三月發生的東北大地震。我回想起新聞報導時絕對會播放的海嘯畫面,滔天巨浪吞沒建築物的光景讓人震撼。我每次看見畫面都想著,無法置信這彷彿電影場面的事情就發生在日本國內。
我吞吞口水,繃起身體。奶奶低頭看著我繼續說下去:
「漁夫慌慌張張回村莊,帶所有村民到山頂避難。他也很好心地告訴鄰村的人,但鄰村的人說怎麼可能會有人魚,根本不相信漁夫。」
「什麼,還特地去告訴他們耶。」
「隔天早晨,去避難的村民們從山上俯視大海,發現海水全部不見了。平常看慣的海岸邊,變成一望無際的沙漠。」
「海岸變成沙漠?」
「因為海水完全退潮了。看見這一幕的村民們一陣騷動,接著伴隨著地鳴聲,沙漠那一頭,從視線的這頭到那頭,幾乎遮掩整片天空的大海嘯『轟!』聲而來……」
奶奶舉高雙手,做出海嘯襲來的動作。奶奶瞪大眼睛,兩顆眼珠簡直要飛出來了,這份恐怖讓我全身顫抖往後方倒下。
「正如人魚所言,日出同時出現大海嘯,吞沒了村莊原本所在的位置。漁夫的村莊奇蹟似地幾乎全村平安,而不相信人魚之說的鄰村整村滅亡了。」
「怎麼這樣……要是他們相信就得救了耶。」
「所以啊,這個故事在石垣島上主要和三個教誨一起口傳下來。要好好重視人類以外的生物,要相信他人所說的話,以及天災相當恐怖的這三點。」
奶奶豎起三根手指說著,這彷彿學校老師教訓學生的口吻,讓我鬆了一口氣。
「什麼啊,原來不是真的故事,而是桃太郎、浦島太郎那類的民間故事啊。」
肯定是童謠那類的東西,全怪奶奶流暢的敘事口吻,讓我完全相信是真的了。
但奶奶面無表情地慢慢搖頭。
「不,是真實故事。那是『明和大海嘯』,明和就是當時的年號,和平成、昭和相同。是距今大約兩百五十年前的時代。」
我之後才知道。在明和時代,日本史上最大,浪高超過八十公尺的大海嘯,襲擊了以石垣島為中心的八重山諸島全區,這個事實也有留下正式紀錄。除此之外也有村莊明明靠海卻不自然地完全沒出現受害者,以及另一個村莊九成八的人口,大約一千五百人死亡的紀錄。
但就算不知道這些紀錄,奶奶的表情和聲音已經有十足的說服力了。
「去避難的漁夫村莊,和不相信的鄰村是真實存在。」
晴朗無雲的天空出現灰色雲朵,陽光因而被遮蔽,感覺空氣稍微變得冰冷。
「怎麼這樣……不是虛構的故事嗎?真的有人魚嗎?」
我無意識地把變得冰冷的雙手拇指折進掌心中緊緊握拳。比電視畫面上更巨大的海嘯襲擊就近在旁邊的石垣島,還奪走了許多人的生命,簡直無法置信。
我低下頭,奶奶溫柔地摸摸我的頭。
「風乃很害怕嗎?對不起喔,但這個故事還有後續。」
我抬頭一看,奶奶的表情一變,露出在她臉上刻畫出深深皺紋的微笑。這個表情讓我心情平靜下來,也不在意陰暗的天空和冰冷的空氣了。
「後續?」
「特別是風乃,妳得好好記住才可以。這是因為,妳有個重要的使命。那就是……」
我好喜歡奶奶。她說了許多故事給我聽,教會我很多事情。而在之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這個人魚傳說。
每到夏日,我就會回想起這個島民人人皆知的故事。
@一、複雜更甚燈黑
我名叫高木海斗。過去曾被譽為神童,現為某升學高中的高三生。
「明明從明天開始放暑假耶,還要每天去補習班參加暑期講座,真討厭。」
放學鐘聲響起,教室瞬間變得吵鬧。同學們紛紛開始準備回家,坐我隔壁的隆也垂下肩膀嘆氣。他嘴上說著「真討厭」但他的音色中沒有絲毫焦急。高中最後一個暑假開始,感覺他也有點雀躍。
「就快大考了,這也沒辦法啊。」
我邊回以敷衍微笑,從抽屜拿出課本塞進書包裡。我想快點回家,我不太喜歡學校。
「你成績很好但沒補習對吧,想要推薦入學嗎?」
「就是那種感覺。」
「真好──平常就乖乖念書的人真輕鬆。」
隆也雙手交握擺在後腦勺,身體往後仰。我邊陪笑邊站起身。
「我只有考前念書,每次只是剛好考到我臨時抱佛腳的範圍啦。」
「聽你在說。」
「真的啦。」
隨意應和後,想要快點離開教室。如果不趕快離開,就會發展成「暑假找個時間大家一起聚一聚吧」的狀況。真心希望放過我。雖然不討厭隆也,但我不想把難得的假期浪費在人際往來上。
明明這樣想,沒想到講台上的老師突然喊我:
「高木,美術老師找你,要你放學後到美術教室一趟。聽說你想要考美術大學啊。你成績這麼好,我覺得有點可惜……但人生就是要挑戰,老師會替你加油喔。」
老師用力握緊右拳,露出相當誠摯的微笑。完美表現把學生的事情當自己的事,為學生著想的老師形象。對渡過叛逆期,且因近在眼前的大考而不安的高三學生來說,是令人放心的存在。
但我只覺得厭煩。只要把我平時的成績照實寫在成績單上就好,我不期待他做出這以上的事情。
「好,謝謝老師。」
我努力忍下想咋舌的心情,點頭致意。我這才想起來,這麼說來,前陣子交出去的畢業出路調查表上,我才第一次寫上這個。在這之前,我都隨意寫上符合自己成績的文科大學。
隆也似乎也聽到老師說的話,他睜大眼睛看著我像有話要說。我眼角感受著他的視線,迅速離開教室。
一抵達美術教室,教室裡有三個女學生圍著石膏像擺好畫架,正在畫紙上素描。肯定是美術社成員吧,三人的畫紙都佈滿鉛黑,已經進入收尾階段了。
我在離她們一段距離的教室角落坐下,女性美術老師接著走出準備室,在桌子另一端坐下,互相打招呼之後,她開口說:
「高木同學,你藝術選修也不是選擇美術對吧。你要考美術大學,具體來說已經決定要考哪間大學了嗎?」
聽見鉛筆規則刷過畫紙的沙沙聲,這個聲音讓我感到很舒服。至少比老師講大考的話題舒服上好幾倍。
「是的,我的第一志願是東京美術大學的油畫學系。」
聽見我的答案,老師食指搔搔臉頰苦笑:
「東美大……那可是私立美術大學數一數二難考的學校耶。我聽說你的成績很優秀,你不是為了考普通大學而唸書的嗎?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打算呢?那邊的學費相當貴,你有跟父母商量過嗎?」
老師連珠炮似地不停提問,她似乎相當困惑。這也是難怪,至今完全沒展現任何跡象的學生,突然在高三暑假前夕說這種事情嘛。
「我從國中開始到繪畫教室學畫畫,那位老師的母校是東京美術大學。老師強烈推薦我去那裡,我的父母也同意了。」
「這樣啊,那你為什麼沒有選修美術呢?」
這間高中有藝術選修科目,得從美術、音樂、書法中選擇一個科目上來上。大多數的學生都選擇功課輕鬆的音樂,把時間花在準備大考上。順帶一提,我選修書法。因為音樂課太多認識的人讓我覺得很煩,不選美術是因為我不想在學校裡畫畫。
「這個嘛……我在繪畫教室已經畫很多了,所以在學校裡不想要思考畫畫的事情。」
「你那麼常去嗎?」
「是的,從國二開始每天去,平日四小時,假日八小時左右。」
說完後,老師驚訝大喊「什麼」,正在畫素描的學生們對此反應轉過頭來看。老師要她們別在意繼續畫畫後,端正姿勢清清喉嚨。
「……你花這麼多時間啊,那也是在那邊準備考試對吧。你可以早點告訴我啊,我或許也能幫上你的忙。」
「是的,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恭敬低頭,還以為這樣就結束了,但老師大嘆一口氣後又繼續問:
「你有參加過比賽嗎?」
我對「比賽」這個單字起反應,心口旁的肌肉繃起來。
「這個……」
「如果你很尊敬繪畫教室的老師,讓那位老師仔細指導你也很好,但偶爾接受不同人的評論對你的進步也是必要……」
「我沒有打算參加比賽。」
我打斷老師的話,自己也知道手心開始出汗。
她手肘撐在桌面,上半身往前傾。
「如果你不介意,下次可以拿來給我看嗎?素描畫或其他什麼都可以,我們的美術社也會舉辦作品評論會,偶爾讓其他人看看比較好喔。可以得到不同角度的建議,現在正在素描的那些學生也是要考美術大學。同為學校裡想考美術大學的人,或許可以得到不同的激勵。」
「不,不用了,我不喜歡和其他人比較。」
我明確拒絕後,老師驚訝地揚眉。我有點不安是否讓老師不開心了。這個人明明是好意邀請我,我卻不小心強硬拒絕了。
「……非常感謝您邀請我,但我有在準備考試,所以沒有問題。我暑假也預定要密集訓練了。」
我揚起嘴角,意識提高音調盡量圓滑一點說話,老師似乎有話要說,但我在她開口前先離開美術教室。
只要一提到比賽,我就會不小心感情用事。
我不想被外人干涉。
因此,我不可以太過社交,也不能太過內向。不被喜歡也不被討厭,這就是遠離所有人的祕訣。
走著走著,上衣口袋中的手機震動。是隆也傳來的訊息。
『我都不知道你想要考美大耶』、『你平常連塗鴉也不畫啊』、『你也說一聲嘛』
畫面迅速顯示簡短句子,我邊感到麻煩也還是打上回應。
「對不起」、「我找不到機會」、「而且很害臊啊」
『你將來要當畫家?』、『替我簽名』
「美術大學不等於畫家啦」
『原來不是啊』、『但畫家也給人一種不是怪人就沒辦法當的感覺』
「我不是怪人?」
『海斗是THE有常識的人』、『下次替我畫肖像畫吧』、『我會拿來當頭貼』
我不知道該如何拒絕這個要求,原本一句接一句有來有往的對話也出現了空白。
老實說,我絕對不想畫肖像畫。好不容易在高中沒有讓朋友看過我的畫過到今天耶。
幾秒後,原本在半空中徘徊的手指落在液晶螢幕上。
「下次有機會吧」
我沒有看回應,把手機收回口袋中。
所有事情都讓我感到厭煩。
如果要我替現在的心情加上顏色畫在畫布上,我會選擇什麼顏色呢?
大概是稍微帶著藍色的燈黑色吧。不,肯定更加複雜。或許更接近群青與凡戴克棕混合出的顏色。如果是小學時的我,肯定可以創造出無人能超越的完美顏色。
讓我再重申一次,我過去曾被譽為神童。
第一次握畫筆是我小學一年級,在美勞課上繪製的「刷牙運動推廣海報」獲得了市的最優秀獎。
身為富裕家庭獨生子而備受寵愛的我,人生第一次得獎獲得父母盛大慶祝。我還清楚記得父母興奮說著我以後要當畫家的開心表情。在那之後,只要與繪畫相關,不管多任性的要求父母都會答應我。
但那絕非我的父母誇張寵小孩,當時我的畫和身邊的小朋友相比明顯鶴立雞群,會如此認為也是沒有辦法的。
大膽的構圖,用色,選定題材的觀察能力。更重要的是,我相當執著畫下每個細節,也有確實完成畫作的耐力。
雖然不是很多人知道,在小學生的繪畫比賽中擔任評審的,不是畫家或美術相關人士,而是從地區的小學裡選出的老師們。要獲得他們的好評相當簡單。技巧高低根本不是太大的問題,只要擁有孩童獨特的觀點,努力作畫就好了。當然,當時的我根本沒思考過那種事情,只是無意識地具體呈現出來。
很不可思議的,只要獲得身邊人的好評就會認真起來。得到他人「這孩子很會畫畫」印象的我,休息時間和放學後都把時間花在畫畫上,也因此練就出技巧。
擁有高超技巧與卓越品味的我,在小六之前橫掃大大小小比賽的我,在升上國中的同時進入繪畫教室,也在那遇到出乎意料外的事情,並立刻離開那個繪畫教室。
自那之後我不再參加任何比賽,也開始向同齡朋友隱瞞我在畫畫的事情。
我離開美術教室離開學校,轉乘電車抵達從國二開始學畫到現在的「秋山繪畫教室」。
和第一間馬上就離開的教室不同,我在這第二間教室持續學畫學了四年半,幾乎每天都泡在這裡。站在靜靜佇立於都內喧囂中的古舊大樓內的一室前,從書包中拿出備份鑰匙開鎖。一打開門,油彩臭氣竄進鼻腔,悶熱感纏繞肌膚。我畫的好幾幅風景畫、寫實畫就立在玄關、走廊、畫室等室內的各個角落。
我一如往常準備好畫布,在椅子上坐下。抓起構圖用的鉛筆,眼前既沒有當主題的東西,也完全沒有構想。只是呆呆舉起右手看著全白的畫面。
以前只要這樣做,我想畫的東西就會一個接一個冒出來,右手也會自己動起來。畫過在宇宙彼方綻放的櫻花,也畫過幾百頭羊在空中奔馳的景色。但不知何時開始,我變得只能畫出親眼所見的東西。
過了幾十分鐘,我的腦海中仍然沒浮現任何東西。反正今天也會和平常一樣,隨意畫個靜物素描後結束這一天吧。
「『認為自己能做到的人就一定能做到,認為自己做不到的人就一定做不到,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法則。』這是畢卡索說過的話。」
這聲音嚇得我身體一跳,一轉過頭,秋山老師雙手環胸才剛嘆完一口氣。別說腳步聲,我連他開門的聲音也沒發現。
「今天又是連一條線也畫不出來嗎?」
所有毛髮長度皆相同的天然捲,只看剪影就像爆炸頭。一臉鬍渣,身穿皺巴巴白色襯衫的樣子,完全就是對自己儀容打扮漫不經心的中年人。
「秋山老師,不好意思。」
「我不是想聽你道歉。」
「你今天不是要工作嗎?」
「我在這裡會打擾你嗎?」
秋山老師露出詫異的表情。
「沒有那種事。」
他是這間繪畫教室的講師,順帶一提,學生只有我一個。他的本業是販售畫作給有錢人,也就是所謂的畫商,趁閒暇經營這個繪畫教室。他一週頂多只會露面一、兩次,這裡已經變成我專屬的畫室了。四十歲單身,常有引用畫家名言的習慣。
「要參加大賽的作品,你再不畫就來不及了喔。」
「報名截止日是八月底吧,今天開始放暑假,趕得及的。最糟拿之前畫的風景畫也行。」
「你以為那個風景畫有辦法在天下的『丸之內創世紀藝術大賽』中獲勝?連佳作都辦不到吧。」
「是嗎?我覺得我畫得還挺不錯的耶。」
「只是不錯而已吧。只是比例完美,每片拼圖正確,花時間仔細畫出來的東西而已。」
「你這是在誇獎我吧。」
「並沒有誇獎你。」
秋山老師皺起眉頭。
一般來說,正確和仔細都是誇獎人的用語。但在藝術的世界中,這無法成為武器。
更別說在丸之內創世紀藝術大賽,通稱「大賽」這個不問專業非專業,十六歲到三十歲的所有人都能報名參加,是能讓年輕人鯉躍龍門的二次元藝術大賽了。
「總之,如果你的作品無法得到佳作,那肯定沒辦法拿到東美大的推薦入學。現在的你連一般入學考都很難過關吧。聽好了,放入你的靈魂。『沒有感情的作品不是藝術』。這是……」
「是塞尚說的話對吧。」
「嘖,沒錯。」
被我說對後,秋山老師很不服氣地咋舌。
我想就讀的東京美術大學油畫學系,正如美術老師所說,是日本私立美術大學最難考的科系。應屆考上的學生,每年兩、三百人中也頂多十人,錄取率隨隨便便就低於五%。正如字面所示,是個只允許天才入學的窄門。
想要跨過這道門,就需要壓倒性高超技巧,以及獨一無二的個性。像我這樣,只懂如實作畫的無能秀才很難入門。
所以我才會以推薦入學為目標,但我國中之後沒有任何美術比賽的得獎紀錄。正如秋山老師所說,我想要得到推薦入學的名額,就需要有震撼性的結果,至少也得是個讓人感覺將來大有可為的作品。
因此,我立下在丸之內創世紀藝術大賽中獲得前三十名作品的「佳作」的具體目標。
當然,如果能拿到被評選為最優秀作品的「首獎」、「次獎」或是等同於第三名的「評審特別獎」更好,但這只能說是過分奢望了。
順帶一提,秋山老師雖然重考三次,但確實是東美大的畢業生。
「如果不行,我就乖乖去念普通大學。把畫畫當興趣也很好。」
我盯著雪白的畫布低語。
畫畫很開心,最棒就是只要有道具,從頭到尾都能獨力完成這一點。不需要他人干涉或幫忙。
所以「完成的同時即結束」也可以,但只要參加比賽,就需要面對他人的觀賞、評價。只要意識到這點,我的手就會立刻動彈不得。
「不,你得去念東美大。」
秋山老師抓住畫布上半部,發出細細嘎吱聲。我抬頭一看,只見秋山老師表情恐怖地俯視我。
「到哪都能畫畫啊。」
「我在入學前也這樣想。而你和我很像。你肯定可以在東美大找到你畫中不足的東西。」
「不足的東西?」
「對藝術家來說最必要的東西,只要有這個,你應該能成為名留後世的畫家。」
「哈哈,那怎麼可能。」
我忍不住嗤鼻一笑,但秋山老師眼神有力地看著我,那不是在說玩笑話的表情。
「……你太看重我了,我只是個凡人。」
我知道自己沒有才華。
藝術家,就是不被身邊的人左右,能夠貫徹自己,擁有強韌精神的人。我認為,那才是真正的才華。如果我也有那份才華,國一時就不會傷得那麼重,現在也能大大方方選擇美術當藝術選修課了。
「而且,現在的我沒有你口中藝術家最必要的東西,你認為我的畫有辦法在大賽中得到佳作嗎?」
當我問出這狡猾的問題後,秋山老師別開眼,嘴角隨之扭曲。
「那是……」
「第一點,我不喜歡為了得獎而畫畫。你不是總是要我畫我打從心底真正想畫的東西嗎?」
「你這小子還真囉嗦,什麼都這樣講道理思考就是你最大的缺點。聽好了,『藝術作品不是為了擺設在房裡,而是為了鬥爭的武器。』」
「這句話是誰說的?」
「畢卡索。畫出來的畫就要為了自己利用到極限,這才是藝術家的正確姿態。聽好了,你是個該成為畫家的人。為此,你要拿出自己的最高傑作參加比賽。」
「如果辦得到,我也想這樣做。但是,我辦不到。」
我咬緊下唇,如果畫得出來我當然也想畫。畫匠想要創造出好作品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萬一我真的能進入東美大念書,可以成為專業畫家靠畫畫過生活,那是件多麼美好的事情。一個人窩在深山裡的畫室,從早畫到晚。這超棒的啊。但我已經不是孩子了,當然不可能認真冀望這種沒有現實感的夢想。
秋山老師「唉」的嘆了一口氣,隨意把手插入西裝褲的後口袋中。
「你還是一樣悶在自己的象牙塔中,但是,我已經做好準備要讓你解放自己的情緒了。」
接著再次抽出手,右手抓著一張紙,看得出來那是一張機票。
「我八月初工作有事要去沖繩一趟,你放暑假對吧,跟我一起來。」
「……什麼?沖、沖繩?」
我無法理解,用愚蠢的語氣重複他的話。
「你那無聊的風景畫,或許在與平常不同的環境中,可以奇蹟似地擁有感情。」
這說詞太過分了。
「但我爸媽……」
「我已經聯絡好了,說是準備考試的一環。」
我的雙親非常信任從以前就相當照顧我的秋山老師,如果是為了考試,也不會反對吧。
「再怎麼說也太趕了吧。」
「那你要和先前一樣,只悶在這間房裡獨自畫畫嗎?你接下來的人生,不管做什麼事情都找藉口對自己說辦不到,一路逃避下去嗎?」
秋山老師皺起眉頭,低頭俯視我挑釁我。他肯定是想要故意惹怒我,試圖引出我的反骨精神。大概想讓我說出「那我就畫給你看!」吧。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為了不讓妳忘記與我共度的夏天的圖書 |
 |
為了不讓妳忘記與我共度的夏天 作者:國仲シンジ / 譯者:林于楟 出版社:台灣角川 出版日期:2022-07-21 語言:繁體中文 規格:平裝 / 272頁 / 14.7 x 21 x 2 cm / 普通級/ 單色印刷 / 初版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37 |
戀愛故事 |
$ 237 |
日本文學 |
$ 255 |
小說/文學 |
$ 270 |
戀愛情事 |
$ 270 |
中文書 |
$ 270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為了不讓妳忘記與我共度的夏天
~在一望無際的藍色小島上──兩人的邂逅將改變命運!~
那個夏天,在發生奇蹟的藍色小島上,與妳共度。
我的世界虛假不實,直到那個夏天,
我在一望無際的藍色小島上,畫出妳的樣貌。
為了準備美大的入學考試,我來到沖繩的志嘉良島旅行。
這是只能畫出缺乏感情之作的我,為了讓自己破殼而出的創作之旅。
「我叫伊是名風乃!你呢?」
我遇見抬頭看著月夜唱歌的妳,當我發現自己無可自拔愛上妳時,
我才知道有怎樣悲傷的命運等著妳。
為了不讓妳忘記與我共度的這個夏天,
我把妳給予我的第一個夏天,畫在這張畫布上。
本書特色
★日本最大規模的新人獎第27屆電擊小說大獎《Media Works文庫獎》得獎作品!
★純度1000%的戀情,正統的「Boy meets girl」物語,讓人無法忘懷的夏日戀曲!
★充滿夏日異國風情,讓人彷彿置身沖繩小島的藍天大海之中,充滿激情之作!讓找不到人生目標的你也能重拾生活中的熱情!
作者簡介:
國仲シンジ
出生於石垣島。終日在生物社團中埋首於海蛇的研究,曾在當地當過電台節目主持人。興趣是畫插畫,曾為街頭舞者。以第27屆電擊小說大獎《Media Works文庫獎》得獎作品《為了不讓妳忘記與我共度的夏日。》於文壇出道。
譯者簡介:
林于楟
畢業於政治大學日文所。研究所在學期間開始兼職翻譯,畢業之後正式踏進翻譯業界,現為專職譯者。有看到有趣文案就會衝動購物的毛病,享受每一個文字與文字創造出的奇幻旅行。
章節試閱
序曲
「風乃啊,妳知道『人魚傳說』嗎?」
小學四年級暑假,我坐在緣廊邊吃西瓜。奶奶就坐在我身邊,一道蚊香燃起的白煙,就在我們之間朝湛藍的天空飄去。
「不知道。」
如果是人魚我還知道,人魚傳說是什麼啊?
專心啃西瓜的我停下手,抬頭看奶奶。奶奶面帶溫和表情,慢慢舉起手捏掉沾在我頰邊的西瓜籽,輕聲說:「這樣啊。」
奶奶視線看著正面的庭院,瞇成一線的眼睛前方,好幾株朱槿綻放朱紅色的花瓣,正在做日光浴。
「這是石垣島流傳的古老傳說──」
石垣島距這個小島約一小時船程,雖然同為沖繩縣離島,石垣島遠比這個沒...
「風乃啊,妳知道『人魚傳說』嗎?」
小學四年級暑假,我坐在緣廊邊吃西瓜。奶奶就坐在我身邊,一道蚊香燃起的白煙,就在我們之間朝湛藍的天空飄去。
「不知道。」
如果是人魚我還知道,人魚傳說是什麼啊?
專心啃西瓜的我停下手,抬頭看奶奶。奶奶面帶溫和表情,慢慢舉起手捏掉沾在我頰邊的西瓜籽,輕聲說:「這樣啊。」
奶奶視線看著正面的庭院,瞇成一線的眼睛前方,好幾株朱槿綻放朱紅色的花瓣,正在做日光浴。
「這是石垣島流傳的古老傳說──」
石垣島距這個小島約一小時船程,雖然同為沖繩縣離島,石垣島遠比這個沒...
顯示全部內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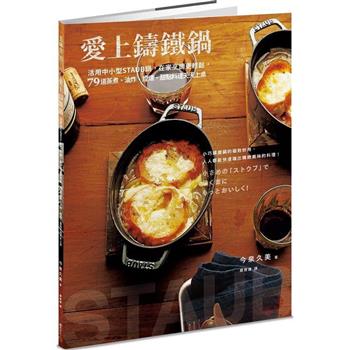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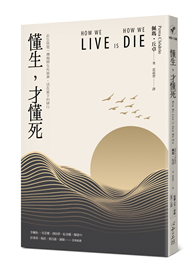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