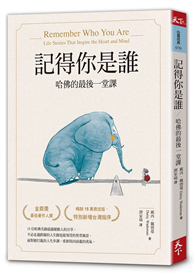「要是瑪瑙妹妹會死掉的話,世界什麼的毀滅了也無所謂吧?」
燈里跟桃子消失蹤影。遭到自己信賴的後輩背叛而陷入混亂的瑪瑙,一面被教典中傳來的撒哈拉的聲音騷擾,一面開始追尋兩人的蹤跡。
此時,燈里跟桃子即使不斷發生衝突,依然繼續逃避著瑪瑙的追蹤。由個性極端不合的兩人組成異世界人×處刑人輔佐的禁忌搭檔。然而,秉持「瑪瑙至上主義」的兩人在逃亡的旅途中,不知為何展開了由桃子主導的燈里強化斯巴達訓練——?
彼此交錯的異世界人、「第四」,還有第一身分。等待著少女們的是希望還是絕望——。少女為了殺掉少女而生的故事,被染成赤紅的第4集!
本書特色
GA文庫大獎睽違七年之久的【大獎】得獎作品!
《在地下城尋求邂逅是否搞錯了什麼》大森藤ノ老師讚不絕口!
2022年春季電視動畫即將播映!
這是一個少女為了殺掉另一個少女的旅程。
異色特務動作奇幻故事,正式揭開序幕。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04)─赤紅惡夢─的圖書 |
 |
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4)─赤紅惡夢─ 作者:佐藤真登、ニリツ / 譯者:譚志瑋 出版社:青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3-01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 211 |
中文書 |
$ 216 |
奇幻冒險 |
$ 216 |
幻奇冒險 |
$ 216 |
Books |
$ 216 |
文學作品 |
$ 216 |
日系奇幻魔法/科幻冒險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處刑少女的生存之道(04)─赤紅惡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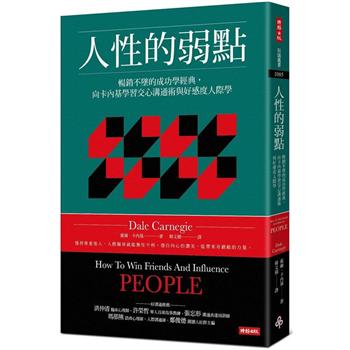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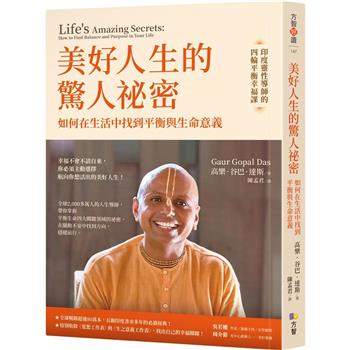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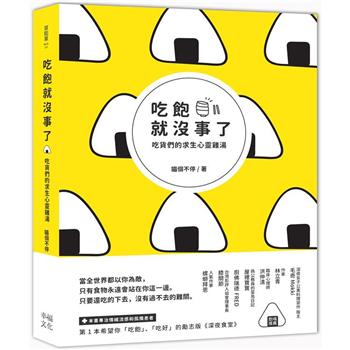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