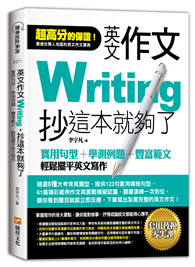第1章 全球化下的國際政經格局與危機
──張登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兩岸僵局是全球政經秩序陷入危機的切片
兩岸僵局由來已久,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未完全結束,遺留下眾多負面產物之一,甚至也可以說是二戰遺留的「未爆彈」。由於美、英、蘇三強對戰後歐洲與亞洲秩序雙重標準的處理釀成眾多衝突,從北方四島(蘇聯與俄國稱南千島群島)、兩韓、琉球(沖繩)、釣魚台、台灣、兩越(1976年以越共勝利結束)以至南海問題、印尼與緬甸少數民族獨立問題、印巴與阿富汗問題,都是大國對峙下無意或惡意留下的懸案。兩韓只有「停戰協定」,兩岸未能「結束敵對狀態」,成為二戰只是技術上分出勝負方的勢力範圍、法理上沒有徹底清理完勝負方權利義務最醒目的象徵。
但是這些懸案只引發若干「區域衝突」(韓戰、越戰是大型衝突,八二三砲戰是「中小型」衝突),未再引爆大國總體戰(total war),則是「全球化」的貢獻。「全球化」運動延緩了二戰未爆彈的連鎖爆炸,有兩個機制。第一是核能技術的「有限」全球化,使主要大國擁核後被迫保持克制,並推動「防核擴散體制全球化」。第二是經濟與貿易的「全面」全球化,使主要大國和其他中小國家難以抗拒地先後加入世界「自由貿易」的洪流,遵循相關規則,分享科技與貿易的紅利,締造了今日「複雜相互依賴」的世界。
時至今日,全球化是否還能發揮上面兩個機制的作用,已經令人存疑。反而兩岸關係的變局與危機已不再只是21世紀的全球焦點,更深深地嵌入到全球政治經濟發展的僵局之中。探求兩岸恩怨因果和找尋解局出路,既要從傳統的兩岸歷史與法理糾結繼續深入,也迫切需要從中美關係乃至全球化的政經結構病理出發,才能獲致更全面的解答。換句話說,兩岸僵局不僅是兩岸當局與民眾的政治主張與利益衝突所構成,它還是國際政經秩序和全球發展危機的一塊切片。沒有宏觀條件的配合,僅憑個人與個別團體良善的願望,難以長久、圓滿地使這二次大戰遺留的火藥庫轉危為安。兩岸危機所涉面向甚廣,有關中美關係、區域政經、貿易、抗疫、軍事等議題,後續各章將有專家帶領讀者詳細探究。本章將以簡明的綱要式分析,介紹危機背後的全球國際政經結構特點,本文稱這些特點構成了一個特定的「格局」。
當前全球政經「格局」構造的底層是「全球化」,其遭遇的危機當然就是全球化的危機。全球化基礎的上層分別是格局的兩大支柱:「行為者支柱」與「制度支柱」。全球化的「行為者支柱」眾多,舉凡主權國家與國際組織、跨國公司、恐怖主義行為者都是,但「大國政治」(great power politics)執當中的牛耳,無須諱言還是影響最大。全球化的「制度支柱」則是最早開拓「全球化」、目前仍主導國際交往規則的西方大國們念茲在茲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自由國際秩序」是西方集團贏得二戰與對蘇冷戰的成果,其內容稍後會詳細說明,讀者只需先記得它大約就是現在美、歐、中、俄紛爭中,西方領袖反覆訴求的「規則為基礎」的秩序,其「規則」的價值根基是「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全球化已到新的十字路口
工業化即西化即現代化、全球化?
全球化格局的兩大支柱都肇始於近代西方工業文明的興起。沒有西方工業文明就沒有全球化。西方工業文明以15世紀末的海盜-海商-海軍複合體為載體,藉著所謂「地理發現」,一波一波地向歐洲以外的世界大進軍。東亞在16至17世紀也陸續捲入,包括今人所稱的台灣「荷鄭時期」,到明治日本「脫亞入歐」後的「拓殖事業」皆是。全球化於是接連透過殖民主義、世界大戰不斷擴張,將歐洲文藝復興、理性主義、科學革命、資本主義、民族主義與主權制度等觀念與規範鋪向全世界。隨之改變世界各地生產與生活的工業化、城市化和後來的科技化、資訊化(總稱「現代化」,modernization),都帶有強烈的西方(20世紀中期以前是歐洲,二戰後歐洲沒落,美國逐漸取代)色彩;「現代化」幾乎就是「西化」的同義字,或說現代化就是西化,也就是全球化。
工業化為前鋒的西化一開始給世界的第一印象是「船堅炮利」,但後來也為全人類帶來了巨大的進步。它所到之處相當程度掃除了舊式專制與盲昧,帶來科學與民權,普及了教育與基建,改善了福利與公衛,延長了全球人類的壽命、提升了相當多數人的幸福。甚至包括主張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也算是一種全球化樂觀派,他們都對全世界、全人類無止境、無疆界的啟蒙與進步充滿信心。冷戰結束,曾掀起革命狂潮的馬列派雖然挫敗,但福山(Francis Fukuyama)式樂觀派繼續堅持自由主義與自由國際秩序將普惠全球,歷史還是會結束於和平與幸福之中。如果全球化樂觀派是對的,兩岸僵局當然可以順勢而解,因為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一定無法回頭;全球自由民主與「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將使兩岸趨同,但中共沒有機會與能力強迫進行兩岸統一。
增長的極限:全球化步向危機
但是全球化不是只有樂觀的一面。從70年代西方部分專家成立的「羅馬俱樂部」提出「增長的極限」概念開始,全球化能否兼具「可持續性」就被廣泛質疑。西方工業文明本來就不會無條件帶動包括民主化在內的「全盤西化」;而「全球暖化」的證據越發突出,更藉由冷戰結束後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與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長期談判凸顯出來,「可持續性」問題已經不只是「增長的極限」,更是全球迫切的危機。無奈全球化的兩大支柱:行為者和制度對這樣的危機卻回應遲緩,甚至還出現川普(Donald Trump)式的「氣候懷疑論」與「疫情懷疑論」。這些懷疑論更透過資訊化3.0助長了民粹式的「懷疑論全球化」,實是全球化樂觀派最大的挫敗。
其實更早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已在文學、社會學與藝術領域廣泛反省氾濫全球的「現代性」,認為表面上橫掃一切的西化-現代化,其實蘊藏著將人類文明庸俗化、物化、異化的危機。上個世紀經濟蕭條、納粹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反覆興起,只是現代性根源病灶反覆大發作的產物;所謂「全球在地化」,也只是全球工業生產與消費主義,戴著異國風情的文創偽裝而已。只是這些反省被消費和娛樂文化所麻痺,又被美國贏得冷戰的燈塔效應與「網際網路」的狂歡一時遮蔽。例如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90年代中期振臂提出的「文明衝突」,就是各種反樂觀派號角中響亮的一聲,九一一恐怖攻擊則是它的局部應驗,使美國陷入「大中東戰爭」,再引發多次金融海嘯與歐洲難民危機。最後是反全球化的保護主義和集團政治,在2010年後逐步取代自由國際秩序的全球化。原本試圖依靠全球化樂觀論與自由國際秩序的勝利,順勢緩解兩岸危機的機會,也逐漸消失。
百年大變局下的台海完美風暴?
此時,我們正目睹全球化的格局走到了十字路口,北京的領導人稱這是「百年大變局」,並不為過。約從2008年北京夏季奧運起連續超越法、英、德、日,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行為者支柱」的重大新變數當然是「中國崛起」。「制度支柱」的重大變化顯然是自由國際秩序從高峰步向危機。台灣社會多數只看到偏離「西化」的中國行為者崛起對制度支柱的損害,但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作為2019年G7高峰會的東道主,有感於川普造成的首次無公報結局,會後向本國使節警告:「西方統治時代行將結束。」(We are living the end of Western hegemony.)路透社還引述他的談話解釋,世界的問題不是俄、中而是美國,把俄國推離歐洲、推向中國,是「巨大戰略錯誤」。而這些巨大變化不僅使全球非傳統危機如氣候暖化和疫情、能源、糧食短缺等問題難以治理,更使主要國家將治理不善問題卸責他國,以傳統的「軍事同盟」與「集團政治」手段推卸創新不力、管治失敗的責任。台灣正處於這個秩序危機崩壞與治理失誤卸責的主要斷層線上,如何避免集「完美風暴」於一身的衝突從天而降,迫切需要社會理性思考、勇於面對。
自由國際秩序的危機(I):領導者與制度
人們熟知的「自由國際秩序」,正是戰後秩序的代稱。它雖經歷蘇聯集團的競爭,卻創造史家稱道的「長期和平」(long peace),原因不外是民族獨立的主權國家、個人主義的市場經濟,以及自由多元的民主政治三大理念,在美國領導、歐日支持的「行為者支柱」之下,逐漸落實於聯合國和布林頓森林體系等支柱性制度規範中,最終透過「全球化」贏得勝利。在這漫長的競爭中,韓戰、越戰、阿富汗戰爭此起彼落,和平的關鍵是美蘇面對危機時能保持克制,壓抑軍事領域的危險競賽。冷戰結束,美國優勢明顯,各大國也還能透過G8、G20等新舊建制,勉力維持「大國一致」。戰後東亞新興工業國的經濟奇蹟、中國經改成功,甚至印度與東協崛起,莫不是這個秩序的受益者。但是秩序盛極而衰,如何既能維持與挑戰者的距離,無法僅依靠美元量化寬鬆與設置中程飛彈,還要睿智地運作均勢,以及國內外條件的配合。
美國逐步撤出「大中東戰爭」、轉向以「印太」制衡中國為新的大戰略,自歐巴馬(Barack Obama)實施迄今已12年。當中經過川普「退群」與國會山之亂,到拜登(Joe Biden)重新加回巴黎氣候協定、透過G7收攏西方盟友,阿富汗踉蹌撤軍或許勉強算是走完全程。伴隨這整個過程的,也是從歐巴馬時代就開始的美國社會的深刻對立。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美國的主客觀條件都很難照舊支撐自由國際國際秩序運轉。喀布爾撤退雖不至於是重演1975年「西貢時刻」,但與1956年第二次以阿戰爭之後,英國漫長的「蘇伊士撤退」若合符節。美國企圖透過「政權改變」與自由化伊斯蘭世界掌握中東的構想必須放棄。
美國的中國對手雖然不像滿手核彈的蘇聯,但美國政界和戰略界的共同想像是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生存威脅」。為了應對這樣的威脅,「大西方」與北約已經老邁,團結G7、「五眼」、美日印澳「四方機制」也不夠,於是被稱為「共同記憶、共同價值、地表最強」的美英澳新三國同盟橫空出世。沒有國會批准的盟約,似乎空口無憑,新同盟第一個「具體」方案是協助澳洲新建核潛艦以取代法國先前提供的12艘柴電潛艦方案,拓展澳軍未來遠洋打擊中國的能力。美英澳合作抗中並非新鮮事。人們應該關心的,是這個比「四方機制」(QUAD,美日印澳)更像為美中戰爭準備的「準軍事同盟」,對「自由開放、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自由國際秩序的意義。
首先,美國作為現狀秩序的霸主,維護優勢的顯性(北約、四方機制、美日與美韓同盟等)與隱性工具(石油美元、五眼、環球金融電信協會)應該足夠。為何甘冒疏離歐陸、東協與日韓印的風險,疊床架屋建造新軸心?只有舊制度與能力不足,才會想到「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把力量集中在自己人手裡。而且新軸心不是依照「能力合格」與「理念相近」,且還有不可說的「更相近」的東西。否則人口稀少、軍備落後的澳洲,除了地理上可以作為美軍抗中最大的後勤轉運點與親切的前敵指揮所外,何以堪當一線主力?難道英國退歐之後,只能把所有海軍都送來「蘇伊士以東」,才能維持帝國在全球的光榮?其實透過三國同盟,美國坦白告訴全世界,「自由之家」成員也分優劣先後。
其次,要合理化在「自由開放、規則為基礎」的世界搞攻守同盟,威脅要夠大才能說服本國與盟國社會。但著名美國戰略學者史文(Michael Swine)2021年4月曾撰文指出,要達到近乎以核生化等方式攻擊他國本土、殺滅人口才算構成「生存威脅」,華府是否濫用概念,令人擔憂。美國空軍部長近來呼籲建設「令中國恐懼的空軍」,但緣由為何?答案是美軍現在無法「自由飛行於中國沿岸1,000英里之內」。他推銷轟炸機B-21可以取得增進美軍安全,以恢復「全球到達、全球摧毀」目標。但此說若信實,美國早在阿富汗就能實行「全域摧毀」,國際領導地位何以衰落?
其實美國知名評論家札卡利亞(Fareed Zakaria)2020年曾在《外交事務》撰寫一篇題為〈美國權力的自我崩壞〉(The Self-Destruction of American Power)的文章,指明歷史上沒有永遠的霸主。當今現狀國際秩序甚至不是始於70年前,而應從蘇聯解體起算,到小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美國才登上秩序頂峰。美國登峰迄今不到30年,竟走到了「自我崩壞」的邊緣。札卡利亞的盛世危言,並沒有呼應「中共百年」之意,只是希望用言過其實,使國際秩序領導者從錯誤回頭,卻正好撞上了中國初步完成「富起來」的中共建黨百年。鑄造「軟權力」(soft power)理論的學者奈伊(Joseph Nye)承認,美國優勢受到考驗的主要「外部」因素之一,當然是中國崛起。但前所未見的內因,是國內社會的分裂,使自己走到川普主義,正好掉進了「反威爾遜時刻」(Anti-Wilson Moment)。美國面對自己一手建立、領導、攪亂的霸權秩序,信念發生這樣大的裂隙,是二戰結束、70餘年來僅見。
列寧曾經說過,「最堅強的堡壘,都是從內部攻破的。」美國全球信用的核心病症,絕非來自俄、中等列強的軍事、經濟挑戰或資訊戰。所謂「銳實力」、「認知戰」,更是推卸治理失敗、沒有學術嚴謹度,只是卸責、帶風向的膚淺概念。小布希的中東戰爭折損了霸主的威信、激起了極端主義、文明衝突為底色的國際恐怖主義;恐怖主義利用資訊科技反擊,不過就是回敬美歐百年來施加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指西方對中東與亞洲的刻板印象)。
非裔當選的歐巴馬訴求團結進步,原本帶來「歐記中興」的一線曙光,也獲得從中東到亞洲普遍的歡迎,卻挑起美國自己內部宗教保守主義、白人至上論、失落的鐵鏽帶選民,與反全球化的失落中產者的群起反對。歐巴馬遂不得不揚棄「超黨派」主軸,直接訴諸東西岸、移民後裔、婦女、都會、年輕人等「進步」選票反制,形成眾多國內重大議題相持不下的50 vs. 50的兩極對立。美國政治氣氛,也從「希望、改變、超黨派」,一步步走向「恐懼、憤怒與分裂」(fear, anger, divide)。這個趨勢去年美國公廣集團(PBS)紀錄片《美國大分裂:從歐巴馬到川普》(America’s Great Divide)有深刻與細緻的探討,對美國外交與全球秩序產生深遠影響。
自由國際秩序的危機(II):價值與共識
全球治理危機與華盛頓共識的興衰
「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是全球自由國際秩序理念在國際貿易與金融領域的制度表現。這個冷戰結束後出現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概念,也隨著秩序的制度衰落而備受質疑。2021年G7峰會公報在全球治理理念上,出現改革性的新觀點。正逢30年前提出「華盛頓共識」概念的英國學者、世界銀行專家威廉森(John Williamson)於4月15日病逝,有論者認為,英國保守黨政府協助組織各國幕僚,在G7峰會前準備的備忘錄用了「康沃爾共識」(Cornwall Consensus)為標題,即是企圖重整幾乎是聲名狼藉、對挽救西方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幾無助益的「華盛頓共識」。後者是描述蘇聯瓦解後,華府向各國提倡、推廣全球化與私有化、市場化改革、商品與資本自由流動、金融開放、政府去管制化等政策的整套理念,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改革。約在華盛頓共識提出15年左右,又有高盛公司的專家拉莫(Joshua C. Ramo)提出了「北京共識」,大意是強調各國可自主適用包括威權體制在內的不同的發展道路,反對通用普適的改革。
當時中國在全球經濟大約排位第7,還沒有清楚自覺到「中國道路」、「中國故事」可以像「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這樣自信,更不會擔心「中國規則」也可能強加於人。所以「北京共識」似乎一直受到部分發展中國家的歡迎,但並未對以華盛頓共識為核心的自由國際秩序構成重大挑戰。畢竟「北京共識」並非一個邏輯一貫、成體系的經濟學與政治學觀點,採行者也未在自由國際秩序的制度性支柱(如布林頓森林體系建立的主要機構)外,另建新的對抗性體系。即便是中國帶頭建立的「亞投行」(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與「一帶一路」,也部分引用歐洲與印度的高管和制度,差別則在資方的組成,與國家的角色。
康沃爾共識vs.中國模式?
華盛頓共識的問題,其實是它的自由競爭與去管制化政策,在西方世界內部造成的社會分裂。它也無法為最近20年陸續爆發的全球性危機如金融海嘯、氣候暖化與疫情,提供對策。於是G7的幕僚們如然要走出川普主義的陰影,擺脫各國民粹派抗拒多邊合作的糾纏,勢必要為西方繼續領導世界,提出具有新的時代精神的觀念。醞釀中的「康沃爾共識」於是改而提倡「包容」(inclusion,取代優勝劣敗)、「韌性」(resilience,取代效率至上)、「公私伙伴」(partnership,取代政企分離)與「外部性」(externalities,取代對定量模型的偏執)。當然,所有這些對華盛頓共識的「改進」,都帶著對抗「中國因素」的誘因。如果沒有中國競爭造成的緊迫壓力,西方集團反省華盛頓共識,不會有急迫性。
又是15年過去,哈佛現實主義學者瓦特(Stephen Walt)2021年5月卻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提出警告:「世界也可能青睞中國規則」(The World Might Want China’s Rules),華府不應自我感覺良好地認為,自己的價值天生比中國更有吸引力。瓦特說,美國的國際秩序在政策表現上既有兩面性(two-faced)的缺失,又飽受民粹分裂社會的衝擊。反觀「中國價值」已不是毛時代的世界革命,反而是「集體利益優於個體權益」支撐的、復古的西伐利亞主權制度。短期裡,這種立場更能免疫於「偽善」指控;也能獲得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推動「政權改造」的美國更多的支持。這種秩序與理念的全球競爭將是漫長的,因為可預見的未來,美中由於規模龐大和地理距離遙遠,不可能徹底戰勝對方。美國要勝出,關鍵在於能否真正走出進步派與保守派惡鬥的惡性循環。
充滿不確定的2040
瓦特版的美國「復興之路」與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2021年3月出版的《2040全球趨勢報告》的長期預測相近。報告認為未來在美中更激烈競爭的大環境下,國際陣營也將不斷重組。資訊科技將使人們更加互聯,但全球各地的認同與價值恐將更加粉碎,致使世局更加動盪。多數國家因而寧願參加寬鬆、臨時性的安排,而非綁入冷戰式的陣營。
報告認為,全球化的動盪發展,將來有五種可能場景:(1)民主集團復興、中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2)北京兼併台灣卻無意領導大局的漂流世界(world adrift);(3)美中競爭性共存(competitive co-existence),並抑制疫情與氣候危機;(4)自足的各區域大國割據(separate silos);(5)與悲劇和流動──氣候急速惡化、全球都是失敗者。無論哪一種場景,該委員會認為,美國參戰都不應是優先考量。而2040年之前如果美中沒有發生衝突,中國沒有全面衰敗,則北京將相當接近其「第二個百年」的「全面現代化」國家目標。屆時台灣的全球位置如何,在一片「美國挺台」的短期表象外,中長期場景更值得人們深思。
接觸失敗,「薩拉耶佛」難免「勢必一戰」?
始自柯林頓(Bill Clinton)時代的對華「接觸論」到了川普執政後期,變成廣受批判的「接觸失敗論」(failure of engagement)。此論的核心是「接觸」未能導致中國「民主化」(實即中共潰敗、「和平演變」、中國崩潰等),反而被北京利用接觸獲得的資源實現和平崛起、熟悉全球化與國際制度領導權、甚至「富起來」,觸發體系權力移轉,造成今日西方似乎失控的全球政經新格局。據說接觸浪費的時間,正好被「中國發展戰略機遇期」所用,耽誤了美國的優勢,又是20年。
但從1996年白宮發佈的《接觸與擴展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來看,「接觸戰略」原本的精神是通過「競爭性共存」維繫優勢。2000年之後陸續出現的顏色革命,甚至後來的各地的「政權改造」,並不在接觸戰略的目標中。反而俄國前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末期的俄國一蹶不振,使小布希時代的美國更加自信,更常採用例外、單邊手段。可以說在錢尼(Dick Cheney)-倫斯斐(Donald Rumsfeld)路線下,「接觸戰略」早已壽終正寢,剩下的是「華盛頓共識」的全力擴張。直到歐巴馬上台,接觸戰略才有所恢復,但美國朝野分裂已經明確,世局也不復當年。可見接觸失敗論者假設1990年代接觸戰略就是要在大陸搞「顏色革命」,是移花接木的謬誤。該論又假定中國「被接觸」後理應歸順美國秩序,又是刻意簡化問題的謬誤。畢竟不僅中國從19世紀「被接觸」至今,從沒有全面接受西方價值,美國也多半也是「例外性適用」自己「基於規則」的秩序。其他「被接觸」後民主倒退、民粹興起的東歐與亞、非、拉國家,現在越來越多。只突出接觸中國失敗,主因其實是中國不但未淪為「失敗國家」,還搖身一變,站穩了「一超之下首極」的位置。
接觸失敗論的謬誤,其實證明了原本戰略目標有節制的「接觸論」,反而有利美國在競爭性共存中維持主導。完全拋棄接觸,採行龐佩奧-班農式(Stephen Bannon)的超冷戰、推倒政權的對華競爭,不但很難削弱北京精煉百年的銳利體制,反而將真正終結「自由國際秩序」主導的全球政經格局。
中小國家夾處在激烈競爭的兩強中間,本來極為困難。如果兩強實力差距明顯,或者一方進攻用意明確,中小單元自然會選擇「一邊倒」。如果兩強實力接近中,但戰略意圖穩定,則中小單元仍有不使競爭波及自己的避險空間。若是兩強實力逐漸接近但戰略意圖缺乏共識,爭奪前線的需求和壓力便會大增,還會直接干涉小國的內部秩序。如果前線小國因為身分與認同的強烈偏向,缺乏策略選擇的彈性,更可能先面臨生存風險。當然美、中交易換取綏靖的「直觀棄台」可斷言幾乎不會發生。但從兩強長期競爭與未來全球格局的不確定來看,台灣對中、美則有「利益不對稱」的特徵:對北京是政權存亡的核心利益;反觀華府則就算參加護台,也有「打多大、打多遠、打多久」的選項。不夠久、不夠遠、不夠大,雖有道義,也等於是「廣義棄台」,又可換取中國掉入衰敗陷阱。
1914年6月28日的前幾年,幾乎沒有人會相信,繁榮鼎盛的歐洲,會在短時間內陷入血腥的世界大戰。就是6月28日之後幾天看起來,衝突也將只限於「某個區域」,大國參戰顯得相當遙遠。薩拉耶佛的一個凶殺,彷彿僅是某地狂熱民族主義者偶然攪起的幻術,大國們會在最後通牒的壓力下,維持「競爭性共存」。當然,歷史告訴我們結局並非如此。幻術轉瞬間就變成了「八月砲火」,大火還燒到太平洋西岸,最終竟藉由巴黎和會,揭開了「中共百年」的序幕。
結構與地理規定了必然,但歷史仍在必然中,讓偶然適度發揮,稍稍驅散陰鬱的宿命論。大西洋的「八月砲火」,在歐洲埋葬了三千萬軍民,在太平洋催生了美國百年霸業和中共的興起。現在砲火的幽靈來到太平洋上空盤旋,人們要擦亮眼睛,冷靜看清全球格局的構造,緩和秩序變動帶來的危機,或許能得到歷史偶然的庇護。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奔向戰場:危險十字路口的台灣的圖書 |
 |
奔向戰場:危險十字路口的台灣 作者:丁守中、王信賢、王冠雄、左正東、李大中、何思慎、林祖嘉、帥化民、高長、張登及、黃介正、趙建民、魏艾、譚瑾瑜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2-22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9 |
二手中文書 |
$ 316 |
政治概論 |
$ 316 |
中文書 |
$ 316 |
兩岸關係 |
$ 316 |
Books |
$ 316 |
Books |
$ 316 |
Others |
$ 316 |
政治 |
$ 340 |
社會人文 |
$ 352 |
政治 |
$ 360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奔向戰場:危險十字路口的台灣
台海若有事,美、日會出兵援台的台灣人樂觀幻想!?
台灣正處於這個秩序危機崩壞與治理失誤卸責的主要斷層線上,如何避免集「完美風暴」於一身的衝突從天而降,迫切需要社會理性思考、勇於面對。
現在砲火的幽靈來到太平洋上空盤旋,人們要擦亮眼睛,冷靜看清全球格局的構造,緩和秩序變動帶來的危機,或許能得到歷史偶然的庇護。
此時,我們正目睹全球化的格局走到了十字路口,北京的領導人稱這是「百年大變局」;當前國際間對台海普遍擔心,視台海為美中交鋒的風暴火藥庫,唯獨台灣社會對美中霸權競爭及台灣處在火線最前線的風險普遍無感。
經濟力量無法轉成政治力!今日兩岸關係更複雜依托在美中霸權競爭中,為了自己國家利益,別期待各國在美中霸權鬥爭中選邊站。
台灣與中國大陸同文同種同血緣,大陸更是我們台灣最大的貿易夥伴,最大貿易順差來源,也是台商最大投資地,台灣為何要選擇一面倒的親美反中,自曝自己在可能的經濟杯葛抵制與霸權鬥爭的烽火最前線呢?
台灣真的走到了關鍵命運的十字路口,經濟杯葛、戰亂風險?還是繁榮安定、和平幸福?全在台灣人的選擇。本書由十四位在各領域代表的學者,從自我的專業領域,解析當前台灣面對的國際政經大局、區域經濟整合、一帶一路、地緣政治與戰略環境、美中鬥爭策略,及兩岸分合關係與風險!
作者簡介:
編著簡介
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
「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成立於1990年,由前立法委員丁守中博士擔任董事長,現任董事包含學術、科技界和企業家共有13位。基金會以研究當前兩岸發展及其互動關係等相關問題,結合各領域專家、學者,共謀台海兩岸的良性發展為宗旨。主要業務如下:
主動發掘與研究兩岸本身各自的發展及交流互動中所衍生的問題,並研擬解決辦法,適時提供有關單位參考處理。
定期舉辦公聽會,掌握民意取向。
舉辦各項專題演講或研討會,以匯集學者專家的意見,供各界參考。
接受各界委託,從事兩岸事務及兩岸發展等相關政策之研究。
提供兩岸交流之相關資訊。
協助解決兩岸交流所發生之糾紛。
獎助各界有關兩岸關係發展之研究。
其他相關事項之研究。
基金會除與大陸全國青年聯合會定期交流互訪外,也不定期舉辦兩岸各領域論壇,為兩岸合作搭橋,先後舉辦「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兩岸航空產業合作研討會」、「兩岸海洋科技合作研討會」、「兩岸鋼鐵合作研討會」、「兩岸汽車產業合作研討會」、「兩岸青少年犯罪預防研討會」、「兩岸資訊科技青年學者論壇」及「兩岸生物科技論壇」等。並曾連續主辦了兩屆「中國精神新聞獎」,鼓勵新聞媒體客觀報導兩岸真相、減少歧視。
近年來兩岸關係經歷重大轉折,未來兩岸經貿關係將更加密切,本會長年來關心兩岸經貿法規的健全,亦關注台商於大陸之投資保障,近年本會曾組團至新疆、甘肅、陜西、上海、天京、北京、蘇州、江西、山東、遼寧及浙江參訪當地投資環境及台商經營狀況,並針對台商投資之困境,提供政策上可能之協助。2012年在台北增設「台商服務中心」,加強兩岸經貿政策研擬、兩岸文化創意產業及兩岸城市交流之推動。
章節試閱
第1章 全球化下的國際政經格局與危機
──張登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兩岸僵局是全球政經秩序陷入危機的切片
兩岸僵局由來已久,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未完全結束,遺留下眾多負面產物之一,甚至也可以說是二戰遺留的「未爆彈」。由於美、英、蘇三強對戰後歐洲與亞洲秩序雙重標準的處理釀成眾多衝突,從北方四島(蘇聯與俄國稱南千島群島)、兩韓、琉球(沖繩)、釣魚台、台灣、兩越(1976年以越共勝利結束)以至南海問題、印尼與緬甸少數民族獨立問題、印巴與阿富汗問題,都是大國對峙下無意或惡意留下的懸案。兩韓只有「停戰協...
──張登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兩岸僵局是全球政經秩序陷入危機的切片
兩岸僵局由來已久,可以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未完全結束,遺留下眾多負面產物之一,甚至也可以說是二戰遺留的「未爆彈」。由於美、英、蘇三強對戰後歐洲與亞洲秩序雙重標準的處理釀成眾多衝突,從北方四島(蘇聯與俄國稱南千島群島)、兩韓、琉球(沖繩)、釣魚台、台灣、兩越(1976年以越共勝利結束)以至南海問題、印尼與緬甸少數民族獨立問題、印巴與阿富汗問題,都是大國對峙下無意或惡意留下的懸案。兩韓只有「停戰協...
顯示全部內容
作者序
序言
──財團法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丁守中
「奔向戰場:危險十字路口的台灣」,是我們一群學者對台灣當前處境的憂心與感受,也是我們決定用做書名的理由。我們認為在美中世紀霸權競爭大形勢下,政府採取一面倒的親美反中,只會造成兩岸風雲愈緊、危機日深,極有可能陷台灣成為霸權代理人戰爭的戰場。當全球媒體都擔心兩岸衝突及擦槍走火,但閲聽眾最多的台灣各新聞電視台卻仍只是充斥著社會新聞,使得國人鮮少國際觀,不關心也不了解國際大環境;更不瞭解當前台灣的處境與風險;民調顯示國人甚至還存有台海若有事,美、日會出兵...
──財團法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丁守中
「奔向戰場:危險十字路口的台灣」,是我們一群學者對台灣當前處境的憂心與感受,也是我們決定用做書名的理由。我們認為在美中世紀霸權競爭大形勢下,政府採取一面倒的親美反中,只會造成兩岸風雲愈緊、危機日深,極有可能陷台灣成為霸權代理人戰爭的戰場。當全球媒體都擔心兩岸衝突及擦槍走火,但閲聽眾最多的台灣各新聞電視台卻仍只是充斥著社會新聞,使得國人鮮少國際觀,不關心也不了解國際大環境;更不瞭解當前台灣的處境與風險;民調顯示國人甚至還存有台海若有事,美、日會出兵...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序言
──財團法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丁守中
第1章 全球化下的國際政經格局與危機
──張登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兩岸僵局是全球政經秩序陷入危機的切片
全球化已到新的十字路口
自由國際秩序的危機(I):領導者與制度
自由國際秩序的危機(II):價值與共識
接觸失敗,「薩拉耶佛」難免「勢必一戰」?
第2章 中國崛起及其政經影響
──左正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中國崛起與中國模式
中國崛起的政治經濟影響
中國崛起與中國因素
從百年變局到命運共同體
第3章 中美博奕:冷戰再起
──李大中...
──財團法人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丁守中
第1章 全球化下的國際政經格局與危機
──張登及(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兩岸僵局是全球政經秩序陷入危機的切片
全球化已到新的十字路口
自由國際秩序的危機(I):領導者與制度
自由國際秩序的危機(II):價值與共識
接觸失敗,「薩拉耶佛」難免「勢必一戰」?
第2章 中國崛起及其政經影響
──左正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中國崛起與中國模式
中國崛起的政治經濟影響
中國崛起與中國因素
從百年變局到命運共同體
第3章 中美博奕:冷戰再起
──李大中...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