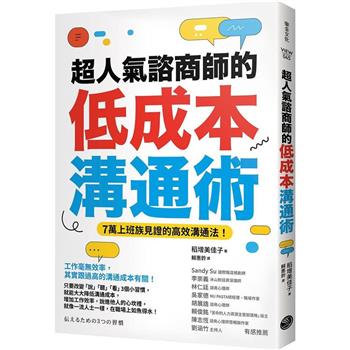失去的水平線──草嶺潭崩潰記(節錄)
前言
草嶺村位於雲林縣古坑鄉,蜷臥在東南端最偏僻的一隅。這兒,起伏著雲林縣境內唯一的山脈;一山又一山,簇擁著伸進了阿里山山脈高聳的雲天間。東與嘉義縣的阿里山番地拉拉齊地毗鄰;西以清水溪為界,與樟湖村密接;南與梅山鄉瑞峰村的三千嶺遙遙對峙;北與南投的竹山鎮為鄰。群山環抱,峰巒疊翠,清水溪蜿蜒流經其間,為一與世遠離,充滿了山光水色勝景的山村。
現時的草嶺村,下轄草嶺,竹篙水,石壁、外湖、內湖、鹿堀、堀坔、曲坑、光田等九鄰,分散在五平方公里的山林內。村內的一百五十餘戶住家,便散居在各個山坡水湄,三五人家,自成一個村落。灰瓦紅牆,綠竹合抱,有若古代的莊院,把個草嶺村點綴成山水畫裡的一幅好風景。
然而,山村裡的生活卻是清苦地。由於山地崎嶇不堪,村民們只能在狹窄的溪谷間拓植著水稻。山坡地上,則種植麻竹、山芋、百香果、苦茶、薑等類的山產。農作之暇,還得到深山裡獵些野豬、山兔等野味,來補充糧食的不足。
山村的生活,自來便是這樣地貧乏、單調。男人們僅有的娛樂,大約便是在飯後低酌淺飲一番;女人家們只能在閒聊時道長說短。這種生活雖有點單調,卻不失古樸、寧靜,在單純的山居歲月中,自有一份淡泊的情趣。
自古以來,清水溪和草嶺便是不可分的。在某些村人們的心中,它們甚至是合而為一的。它發源於阿里山北麓,從大塔山、小塔山蜿蜒流來,在全仔社與阿里山溪匯合後,便沿著草嶺村,曲曲折折地繞過村子的西南邊綠,在楓子崙一帶,流過堀坔的山腳。
這一彎帶也似的溪流,潺潺地流動著清澈的溪水,流過寬廣的河床,也流在村人們永世難忘的記憶中。
假如沒有清水溪的話,或者,假如它不流經堀坔山的話,那麼,草嶺村便會真地是一塊寧靜、安詳的樂土。何其不幸的是,它不但流過堀坔山,而且河道正好在此拐彎,從南往北,直衝向堀坔山的山腳。於是,一幕又一幕的慘劇,便在這個交會點上,在這個小小的山村裡,一代又一代地重演。
一、風雨中的崩聲
八月,在中部的山區是個不祥的月分。
戈登的裙裾才剛剛拂過,被氣象人員列為超級颱風的賀璞小姐,挾著巨大的聲勢,不旋踵又緊跟而來。山雨欲來風滿樓,直吹得草嶺的村民們人心惶惶,不可終日。
山上,正是竹筍收割的季節,每個人都在擔憂著無情的風雨,會攫去他們一年的血汗。有些人家連忙動員起來去搶收;有些只是茫然地在竹林內空打轉;更多的人都在神明前祈福,求老天的垂憐。好在雷大雨小,賀璞輕扭腰肢,略一徘徊,匆匆地便走了,並不曾帶來多大的災害。
麗日高懸,朗朗照著草嶺山坡上廣袤的竹林,映照著清水溪乾涸的河床,村內的割筍也在這時進入了高潮。不分男女,大家都披戴起來,腰際斜插著鋒利的柴刀,挑起擔子,飛快地隱入竹林的濃蔭中。高地搬運機滿載著竹筍,在林隙的小徑間來回穿梭,嘎嘎地吼叫著。路旁的筍寮內,冒著一蓬一蓬的輕煙,夜以繼日地燒烤著。火光閃閃爍爍,終宵不熄,使得村子裡裡外外,到處都洋溢著一股濃郁地、熟透地收穫的喜氣。
不過十餘天的光景,阿里山區又湧來一堆堆烏黑的雲層,擴散開來,籠罩著嘉南雲峰一帶的山峰。陰陰晦晦的雲霧,遮住了陽光,風也冷颼颼地在竹林間吹颳起來。
八月十二日晚上九點三十分,中央氣象局正式發出了中度颱風歐敏的陸上警報。十四日,暴風邊緣掃過了臺灣東北部,中心最大風速每秒三十五公尺,暴風半徑為三百五十公里,預測十五日晚間九時的位置,在臺北北北東方約四百公里的海面上。
村子裡一家家門扉緊閉,大家都聚集在收音機旁,收聽最新的颱風消息。雨也從這個時候開始,在廣大的山區間刷啦刷啦地猛下起來。村民們憂心忡忡地望著窗外,遠遠的山腳下,傳來清水溪湍急的奔流聲,每個人似乎都能預感到一股不祥的凶險,正在這個風雨交加的晚上,慢慢地醞釀著。
這股歐敏颱風的環流帶來的豪雨,足足地在阿里山區落了一個晚上。草嶺也在這陣狂風驟雨中,度過了漫長的一夜。
八月十五日,破曉時分,風漸漸地歇止,但雨仍霏霏地在山區飄著。住在公田的簡英憲,一晚沒睡好覺,老是在惦掛著筍寮的安全,因此天才矇矇亮,就迫不及待地起床。他披上雨衣,匆匆地往筍寮去走,深怕它已被溪水沖走。
二十八歲的簡英憲和他的弟弟,每年竹筍採收的時節,都出來幫人割筍。兩天前,他們才割完坎腳的一公頃竹林,連夜又轉移到上游一公里的溪邊。這一座筍寮正好位於溪邊的懸崖上,離清水溪的河床不到一百公尺,溪水若高漲的話,很可能會將它沖走。一沖走的話,那裡面的四、五百斤竹筍,當然就要蕩然無存。
外面,猶是暗濛濛一片,雨點冷冷地落在他臉上。簡英憲可顧不了那麼多,他急急地走著,及在轉彎處看到那座筍寮,才鬆一口氣。走進筍寮,看著竹林底下黝黑的溪水,內心裡突然顫慄起來。
就在這時,從堀坔山的方向,傳來了轟轟的響聲。轟隆──轟隆──一陣緊接一陣,低沉而鬱塞地,像響在遠天的悶雷;復又在沉寂的谷底溪澗激盪迴旋著,像一聲聲鬼魂的啁啾,把他嚇呆了。他直覺地想起,莫非又是堀坔山崩山了?這個念頭在他眼前一閃,他再也顧不了竹筍,拔腳就往村子跑,一邊在心底狂喊著:天啊!堀坔山又崩山了。
這時,天已經漸漸放亮了,距離堀坔山五公里之遙的草嶺,已經甦醒過來。雨絲若有若無地飄在繚繞的煙雲間。雲嶺山莊的主人蘇國棟起床後,正在打掃庭院的落葉,忽聽得鄰人們在議論著什麼似地,便圍攏過去,大家七嘴八舌,正在探詢剛才那幾聲譎詭的響聲。有人說是打雷,有人說是崩山;也有人笑著說是在做夢。眾人議論了半天,談不出一個結果來,正要各自散去,忽然見到二路頭的陳善源慌慌張張地跑過來,一邊還嚷著:不好了,堀坔山崩山了。
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往村長家裡跑去,大家也跟著過去,寧靜的明修山莊裡,突然顯得騷動起來。村長李明修和他的父親李祥,正坐在廊前等著吃早點,一邊還在談論著昨夜的風雨,不知會不會造成公路的坍方。見到一批人倉皇地湧進來,正要發問,陳善源已等不及地嚷著:堀坔山又崩了!
二路頭位於嘉義縣的瑞峯村,正好隔著清水溪與堀坔山遙相對望。當堀坔山開始崩塌的時候,陳善源和他的鄰居黃良騄都被驚醒過來,只聽到轟隆轟隆之聲不絕於耳,有如萬馬奔騰。他嚇得摟著一家大小,動也不敢動地緊抱在一起。天明後,到外面一看,崩下的砂石已將清水溪堵住。混濁的溪水正在一寸一寸地往上漲,他知道情況嚴重,連飯也沒有吃,就趕到草嶺來通報,希望大家提高警覺。
四十二歲的李明修村長,是個幹練的基層行政人員,在草嶺頗受當地村民的愛戴。他在村長任內,完成了草嶺對外的產業道路,建立了村內的電視收視網線,目前正在致力於交通路況的改善,然而在這時,又多了一樁令他擔憂的事。
吃過早飯後,他再也放心不下,立刻騎上摩托車,匆匆地往堀坔山奔馳著去。他的父親李祥,已有七十四歲的高齡,經過了歷次的山崩,使他對堀坔山的了解比任何人都來得深刻。他望著李村長的背影消失在山腰間,彷彿又看到了二十八年前的慘劇,不禁仰起花白的頭髮,嘆息道:唉!堀坔山,莫非這是天意嗎?
二、黑色的堀坔山
李村長離開草嶺後,便沿著溪邊的一條村道,飛快地往前馳去。落了一夜的雨,那條不到二尺寬的小徑上,到處都積滿了水。東一個水窪,西一個水窪,騎過去時,泥漿便濺起老高,沾得他一褲管都是。每次經過這兒時,最令他痛心的便是這條道路始終得不到縣府的重視,一味任它荒棄在這兒,大大地影響了村民的出入及山產的運輸。才不過短短的四公里,當局似乎連瞧它一眼的興趣都沒有。他想還是要盡量去爭取,否則村民們太辛苦了。
不久之後,他在一座筍寮前遇上了簡英憲,簡回去通知了鄰人後,又回到筍寮來工作了。他正在考慮今天要不要去割筍,看到村長騎著摩托車過來,便將他攔下來,告訴他堀坔山崩了,要他特別小心。李村長告訴他,他正要去崩山的現場看看,不礙事的。
二十分鐘後,小路到盡頭了,李村長捨車進入茂密的竹林中。林子裡更是潮濕,地上被割筍的人家踩得一地泥濘不堪。他東鑽西鑽,愈近溪邊,便愈多倒塌的竹林,以及橫七豎八的枯枝、石塊。等他下到溪邊,到了崩坍現場,抬頭望去,那堀坔山上果然崩下了一塊長達兩千公尺的斷面,犬牙交錯,裂痕猶新,只是面目全非,滿目瘡痍,看起來倍覺猙獰可怖。
堀坔山上,還有雲層飄浮,崩下來的巨岩砂土,滑落達二、三公里之遙,堆積成一座天然土石壩,剛好把清水溪整個都堵住了。壩上巨石磊磊,連根拔起的樹木東倒西歪,壓擠成一堆橫生的森林。到處都是石塊,都是泥沙,環顧四周,一片殘破不堪的景象,恍若歷經了一場人間浩劫。
而更令人怵目驚心地,便是被堵塞住的溪水,已在短短的時間內竄升上來。每過一分一秒,便漫過一枝枯枝,吞下一塊石塊,這麼一步緊接一步地高漲上來了。
李村長這才真的慌了,雲煙縹緲中,他望著堀坔山那醜惡的形體,不禁觸動了那永世難忘的回憶。啊!這可詛咒的惡魔,又再度來尋求它的報復了嗎?
這座令草嶺村民心驚膽寒的堀坔山,聳峙在楓子崙地段的清水溪北岸,距離草嶺村約莫有五公里。據當地老一輩的人說,早年山頂上有一個大水堀,四周土質十分軟弱,因此被稱做堀坔山(坔,音隆,臺語指水多而軟之地)。山有東西兩嶺,東嶺較高,西嶺較低,其間為東西走向的狹長鞍部,標高一○四○公尺,高聳雲天,形勢極其突兀險峻。
在地層結構上,堀坔山為砂岩頁岩或泥岩互層。砂岩易滲水,且節理多,頁岩或泥岩不易透水,地下水多自地表經砂岩滲入地下,遇頁岩或泥岩則又自地下滲出。因此,若經雨水或地下水長期浸潤後,頁岩便具有潤滑性能,而砂岩則被節理切割而成自由塊體,幾乎是各自獨立的石塊。
地質學家林朝棨教授分析說:當雨水不斷沖刷後,這些砂岩頁岩便會與泥岩脫離,而崩落下來,此種現象在地質學上稱為地層滑動(mass slip)。
據調查,阿里山區年降雨量達四千公厘以上,而蒸發量僅八百餘公厘,使得土石堆積中的含水量特別豐富。不僅風化作用甚強,更兼有水化作用,故從地表覆蓋情形來看,堀坔山表面的雨水沖刷似乎影響不大。但因地下水含量甚豐,形成「孔隙水壓」,實為促成山崩的主要原因。
省地質調查所的徐鐵良先生,很早就對堀坔山發生興趣。民國六十年,他便曾來到堀坔山下,從事現場實際勘察研究。他同樣指出:清水溪中上游的岩層地質軟弱,而節理特別發達。每於大雨之後,受雨水或地下水的侵蝕,使頁岩軟化,無力支撐,造成傾斜面的岩層表面滑落。堀坔山過去所發生的巨大崩塌,都是受這種地層變化的影響。
老一輩的村民,至今尚能繪聲繪影地談論歷次山崩的情形。從小,李村長便在這些傳言中長大。這堀坔山一直像一座魔山似的壓在村民們的心頭,因之,使他們對人世產生了一種無常的幻覺。
遠在遜清咸豐末年,堀坔山在豪雨的侵襲下,首度崩坍。崩下來的土石,將清水溪的出口堵成一個水潭。那時的蓄水量與潭水面積,雖然沒有確實的紀錄可查,但根據推斷,似乎並不很大。
同治年間某個農曆七月,山上一連下了十餘晝夜大雨,山洪猛烈地沖刷下來,那座天然壩突告崩潰,潭水狂奔而下,決定了清、濁二溪在竹山附近匯流的歷史命運;也造成了那條長達八十四公里的虎尾溪的雄姿。當然更造成了雲林、南投下游地區慘重的損失。
經過此次災變後的草嶺潭,又回復了原先的面貌。只是一個遍地狼藉,面目可憎的河床罷了。民國三十年冬十二月十七日,凌晨四時,嘉義地區發生強烈地震,震幅之大,連草嶺也不能倖免。堀坔山南坡的小山嘴再度崩塌,崩落下來的土石,堵塞在原來的潭邊,形成一條八百公尺長,一百四十公尺高的天然堤堰,由堤堰至潭尾,迤邐長達五公里。
翌年八月間,山區又降豪雨,連續三晝夜,落雨量達七百公厘。十日這天,山洪暴發,往潭底猛洩,堀坔山再度不支。崩落的土石飛越了兩公里,朝原先的天然堤堰覆蓋下來。滿潭水時的潭水面積廣達三百九十七公頃。使得沿岸二百公頃的耕地,十七戶的住家,六十四條的人命,以及數不盡的家畜,全部慘遭潭水吞沒,作了潭底的冤魂。
這座世所罕見的天然大壩,在歷經了八年的重荷後,終於顯露出不支的疲態。民國四十年夏五月十八日,山區大雨滂沱,潭水的水位驟增,超出溢流口達四公尺,不但洪流劇疾,沖刷力量尤為勁烈。晨五時,溢流口下游發現裂縫,兩岸的巨石不斷滾進潭裡。溢流口及溢水道開始全面崩潰,到中午十二點止,流出的總水量高達一億立方公尺,直向清水溪下游奔騰而下。一路怒潮洶湧,濁浪排空,洪水所經之處,無不披靡,造成了雲、嘉、彰、南四縣亙古未有的巨災。
這次災變,總計死者一百三十四人,被災者一萬一千三十餘人,房屋全毀者一千兩百餘棟,流失淹沒土地一千三百餘公頃,財產及牲畜等損失一千七百餘萬元。
這些血淋淋的慘劇,一幕幕地掠上李村長的眼前,眼前那座堀坔山看起來更讓人覺得猙獰恐怖了。它冷然聳立雲際,彷彿做勢欲撲向草嶺所有的村民,李村長頓然感到背脊一陣陰寒,渾身汗毛倒豎。他疾步退出林外,跨上摩托車,瘋狂般地馳回草嶺,一邊堅決地從齒縫迸出一句話來:這次絕不能再讓這些慘劇重演了!
李村長在八點前趕回明修山莊,即刻以電話對外發出緊急通報;「草嶺潭因豪雨崩山堵住溪流,致使潭水升高,隨時有崩潰危險,請通知清水溪沿岸居民,提高警覺,隨時注意安全。」
| FindBook |
有 11 項符合
司馬庫斯的呼喚:重返黑色的部落的圖書 |
 |
司馬庫斯的呼喚:重返黑色的部落 作者:古蒙仁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3-1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司馬庫斯的呼喚:重返黑色的部落
紀錄地景滄桑身世與榮華興衰
報導文學資深掌旗手古蒙仁,經典作品再現
今日的新聞,明日的歷史
重返臺灣七○、八○年代的山間海濱、大城小鎮,看時代的變遷
孫大川、須文蔚專文推薦
原住民雖然弱小,卻是台灣主體性和民主化實踐過程中,最具指標性的判準之一。四百年來以漢人為主流的臺灣社會,第一次學著要以平視的眼光面對原住民。古蒙仁兄當年以年輕人的熱情,完成的一系列報導文學作品,反映的就是那個大時代臺灣歷史精神的躍動。聲稱這是「文學」貢獻給台灣原住民族的禮物,應該不會是太離譜的説法吧。──孫大川
高信疆所掀起的報導文學風潮,最具體的標竿莫過於第一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類的系列作品,讓臺灣讀者眼睛一亮。其中最著稱的莫過於古蒙仁獲得推薦獎〈黑色的部落〉一文,樹立了報導文學的文體要素:作家以見證者身分調查、訪問與報導,背景歷史資料經過考據,敘事中夾述夾議,在感嘆與抒情中感動讀者關心弱小者。
本書的出版,見證了古蒙仁在風雨如晦的時代,以文字照亮人間陰暗的角落,以書寫激起社會改革的動力,從而揭顯了報導文學的影響力,具有碰撞現實與改變社會的能量。他以實踐的精神,充分的田調,多元的筆法,書寫黑暗,接引光明,成就了臺灣報導文學史上意義非凡的篇章,也是一本值得再三閱讀的經典。──須文蔚
此次司馬庫斯的邀訪,來得正是時候,可以一圓我重返部落的美夢。那是來自四十多年前的記憶和歲月的呼喚。一個當年人跡罕至的深山部落,一段千里迢迢的尋夢旅程,牽引著我離開尚未畢業的大學校園,毅然地朝它走去。
那是我年輕生命中迸發出的最灼烈的一股熱情,也是我初嘗人生挫敗時內心最深刻的一道傷痕,更是我畢生最難忘的一段記憶,都曾和這個位於窮山僻壤的部落有著千絲萬縷的糾葛和纏綿。一旦被喚醒了,就像一座沉睡千年的火山再度爆發,再也不可收拾。──古蒙仁
一九七○年代,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的推動下,各家媒體推波助瀾,臺灣掀起一股報導文學創作熱潮,當時尚為大學生的古蒙仁,以〈黑色的部落〉奪得第一屆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推薦獎」,之後在報社工作,就此開展他的報導文學寫作之路,在臺灣山間海濱、大城小鎮中走踏,至今已四十餘年,仍創作不輟,為臺灣報導文學的掌旗作家。
他對臺灣土地的自然生態、社會風貌、市井人物充滿強烈的好奇心,擁有豐富的情感投射,讓報導文學作品不再只是理性的景致描摹、歷史爬梳及冷靜敘事,而是從文學創作者敏銳善感的觀察著手,使得報導更具個人特色與靈魂。白先勇曾讚譽古蒙仁「擅長描寫臺灣社會的變遷,變遷中人世間一些無可挽回的無奈與人生的悲歡。」
本書精選古蒙仁報導文學經典作品,包括曾在文壇捲起旋風的〈黑色的部落〉等二十四則名篇,加上近年新作一篇,分為三卷。「上卷:現實的邊緣」,遠離塵囂,走踏鼻頭角、金瓜石、司馬庫斯、草嶺潭等北中南秀美壯麗兼俱的奇景,以及具魔幻風格的王船祭傳統祭典;「中卷:產業興衰」,從高山到海濱,以充滿人文關懷慈悲之眼,看臺灣各地產業的演變興衰史;「下卷:城鄉舊事」深入各地鄉里,尋找具傳承歷史價值的人、事、物,傳統技藝、風土民情、特殊景致,紛然羅列,為當地的歷史留下紀錄。
作者簡介:
古蒙仁
本名林日揚,臺灣雲林人,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文學碩士。曾任《中國時報》撰述委員、《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獎助處長、副執行長、雲林縣文化局長、文建會主委辦公室主任,桃園國際機場公司經理、航科館館長。並曾任教中興大學、中央大學,目前已退休。多次獲中國時報文學獎、吳三連文藝獎、行政院金鼎獎、中興文藝獎、文藝協會獎章。作品以報導文學、小說、散文為主,著有《黑色的部落》、《雨季中的鳳凰花》、《失去的水平線》、《凝視北歐》、《臺灣山海經》、《虎尾溪的浮光》、《大道之行》、《花城新色》、《青埔悠活》、《浯島春秋》等三十餘種,其中〈吃冰的滋味〉一文入選國中國文教科書長達三十年,流傳最廣。
章節試閱
失去的水平線──草嶺潭崩潰記(節錄)
前言
草嶺村位於雲林縣古坑鄉,蜷臥在東南端最偏僻的一隅。這兒,起伏著雲林縣境內唯一的山脈;一山又一山,簇擁著伸進了阿里山山脈高聳的雲天間。東與嘉義縣的阿里山番地拉拉齊地毗鄰;西以清水溪為界,與樟湖村密接;南與梅山鄉瑞峰村的三千嶺遙遙對峙;北與南投的竹山鎮為鄰。群山環抱,峰巒疊翠,清水溪蜿蜒流經其間,為一與世遠離,充滿了山光水色勝景的山村。
現時的草嶺村,下轄草嶺,竹篙水,石壁、外湖、內湖、鹿堀、堀坔、曲坑、光田等九鄰,分散在五平方公里的山林內。村內的一百五...
前言
草嶺村位於雲林縣古坑鄉,蜷臥在東南端最偏僻的一隅。這兒,起伏著雲林縣境內唯一的山脈;一山又一山,簇擁著伸進了阿里山山脈高聳的雲天間。東與嘉義縣的阿里山番地拉拉齊地毗鄰;西以清水溪為界,與樟湖村密接;南與梅山鄉瑞峰村的三千嶺遙遙對峙;北與南投的竹山鎮為鄰。群山環抱,峰巒疊翠,清水溪蜿蜒流經其間,為一與世遠離,充滿了山光水色勝景的山村。
現時的草嶺村,下轄草嶺,竹篙水,石壁、外湖、內湖、鹿堀、堀坔、曲坑、光田等九鄰,分散在五平方公里的山林內。村內的一百五...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推薦序一「文學」貢獻給原住民族的禮物 孫大川
推薦序二書寫黑暗,接引光明 須文蔚
原序從「失去」到「再生」─一個報導文學工作者的省思 古蒙仁
新序再生奇緣 古蒙仁
上卷:現實的邊緣
沒有鼾聲的鼻子──鼻頭漁村初旅
淘金夢碎──九份、金瓜石的原貌
黑色的部落──秀巒村透視
火海中的王船──西港慶安宮建醮側記
失去的水平線──草嶺潭崩潰記
司馬庫斯的呼喚──重返黑色的部落
中卷:產業興衰
烏魚遲來的時候
鹿谷的春茶王國
環山部落的水果傳奇
柳營酪農的曙光
太平山林場
七股的鹽田風光
臺北大橋...
推薦序二書寫黑暗,接引光明 須文蔚
原序從「失去」到「再生」─一個報導文學工作者的省思 古蒙仁
新序再生奇緣 古蒙仁
上卷:現實的邊緣
沒有鼾聲的鼻子──鼻頭漁村初旅
淘金夢碎──九份、金瓜石的原貌
黑色的部落──秀巒村透視
火海中的王船──西港慶安宮建醮側記
失去的水平線──草嶺潭崩潰記
司馬庫斯的呼喚──重返黑色的部落
中卷:產業興衰
烏魚遲來的時候
鹿谷的春茶王國
環山部落的水果傳奇
柳營酪農的曙光
太平山林場
七股的鹽田風光
臺北大橋...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