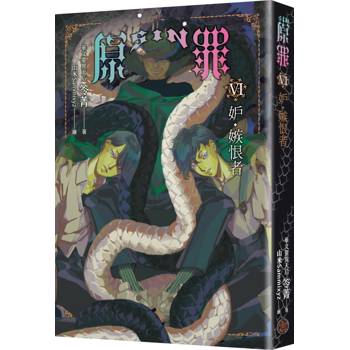後記
傳統的耶路撒冷朝聖之旅有幾種不同走法,我所走過最艱難的一次經驗是黎巴嫩、敘利亞、約旦、以色列四國路線。
進入耶路撒冷後更是辛苦,你可能會遇到猶太教節日、伊斯蘭教節日、天主教節日、東正教節日、科普特教會節日,或者亞美尼亞教會節日。又或者突然之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又有新一波政治糾紛,新一波宗教衝突。你必須隨機應變,如果大馬士革門不能進去耶路撒冷舊城,你得當機立斷,馬上叫司機繞過半座城牆,改從雅法門去逼近埋葬耶穌的聖墓教堂。
守戒律的猶太人,在安息日要休息,不能作工,包括生火、點燈、按電氣開關都禁止。於是每間飯店至少都會有一台安息日電梯。想像一下,你的房間在21樓,剛剛在B2吃完晚餐,走進電梯時發現怎麼樓層按鈕全失效了,正要走出電梯門卻自己關上了。然後,B1-LG-1-2-3…,每一層樓,門緩緩打開,停止不動,再緩緩關上。
記得那一年,茉莉花革命之火,已經從北非突尼西亞蔓延到了中東地區,我們一路上默默祈禱,最後一站終於順利進入哭牆(西牆),也登上了聖殿山。藍色天空,萬里無雲。上帝的陽光,不言不語,一整片灑在金頂清真寺之上。
猶太人說,先祖亞伯拉罕(Abraham)獻祭以撒(Isaac)的摩利亞山就是這裡,此地也是所羅門王聖殿至聖所中放置約櫃的所在,約櫃裡有兩塊石版,那是耶和華交給摩西的十誡。穆斯林說,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時所行的唯一神蹟,「夜行登霄」之處就在金頂清真寺之內。
聖殿山下方,第一世紀的羅馬帝國大道,今日已經被考古學家挖掘出來了,基督徒說,那肯定是耶穌帶領門徒曾經走過的街道。
在《耶路撒冷三千年》(Jerusalem: The Biography)這本書中,作者賽門.蒙提費歐里(Simon Sebag Montefiore)如此形容這一座城市:
世界若有十分美,九分在耶路撒冷;世界若有十分哀愁,九分也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神的殿堂,兩個民族的首都,三個宗教的聖地,更是唯一擁有「天堂」與「人間」兩種存在的城市。
若要更深入了解以色列的宗教和文化,我也推薦可以讀西蒙‧夏瑪(Simon Schama)的《猶太人》(The Story of the Jews),他在書中探詢猶太民族悠長的歷史源頭,敘述羅馬帝國攻陷耶路撒冷後的大離散,也不時提出令人信服的高明見解,比如,討論歐洲希臘文明和猶太文明的根本差異時,他說:
古希臘人和古希伯來人就好像油和水,他們以各自的方式「令人敬畏」,兩者「令人敬佩」卻不能混合。希臘人追求的是自我實現,而猶太人則為自我征服而掙扎奮鬥。「要順從」在猶太教中是無尙的命令,而「坦誠面對你的本性」對希臘人是最重要的。
希臘哲學預先假定存在著可被發現的普世真理,猶太人則認為這種封閉文化中的智慧是私人寶藏。
根據宇宙和諧原則建立的希臘神廟,是為了把人吸引過來,而耶路撒冷聖殿則是禁止「外邦人」進入的。希臘的雕像和紀念碑,旨在當建造它們的城邦消失後仍能留存與此;而以色列人的《妥拉》(Torah)則意味著要比他們的建築物流傳更久遠。
如果你是在古典傳統薰陶下長大的,你就會認為歐洲是在打敗波斯人的入侵後才有了自己的歷史,希羅多德就是這樣描述的。如果你是作為一個猶太人長大的,你會希望波斯人獲勝,因為他們畢竟曾是耶路撒冷的重建者。以斯帖(Esther)曾經是波斯人的王后──他們能有多壞呢?
我喜歡讀書,也一直在旅行的路上。我始終覺得,旅行是文本的重現、延伸、解構與再造,親臨過書中故事的真實空間現場,才會發現原來所謂的「現場」其實就是一座心靈「劇場」。等到旅途歸來,再翻開同一本書、讀同一頁的文字,字裡行間彷彿是剛剛走過的明巷暗弄,看故事的你,從此成為書中的人。
我們最稀缺的是時間,最奢侈的也是時間。
世紀肺炎疫情的影響,有很長一段日子沒有辦法出國旅行,20多年來每年有3、4個月在世界各國遊走的我,因而增加了不少的「台灣時間」,更難能可貴的是我的台灣時間居然是連續性的,不會被中斷,知覺到這樣的時間狀態時,我有一種奢侈的喜悅。
可以陪媽媽過年,可以陪兩個女兒度過完整的暑假,名字被排入家中洗碗輪班表,規劃了書和旅行的系列講座,也答應了大學兼職教學的一門課。有一回,受邀到觀光系演講,細心的教授事前特地傳訊提醒我,這是一堂壯遊與文化體驗的課程:
「…他們要自己規劃行程,然後自己做深度的體驗跟壯遊的內容,包含當地的一些深度的學習。那您的部分,可以就一般旅遊的規劃應該注意的事情跟他們分享或者旅遊體驗就可以了。」
分享注意事項、旅遊體驗的議題很容易,不過既然提到了「壯遊」,我想試著帶領同學們進一步去思考的是,什麼是你旅行的內在驅動力?什麼是旅行?
年歲漸長,漂流居停,有了一些體會,一些感悟,於是我打開電腦寫了封信,送給這堂課的同學。現在,我也把這封信,分享給正在讀這本書的你。
寫給旅人的一封信:
旅行一開始是往地圖上目的地前進,為了印證出發前的想像和期待,結束在滿意、驚嘆、錯愕或者失落的終局。綠水青山,總是豐富人生的收藏。
旅行是玩樂。放縱無罪,享受有理。在旋轉木馬一樣的日常生活之中轉久了,有誰不需要停一下,犒賞自己,暫時逃離?離開,喘口氣,向外走兩步,於是人開始旅行。想要擺脫枯萎蒼白朝九晚六的自己,欲念是如此強烈,因此人們會選擇新奇,冀望陌生的世界某個國度可以撫慰焦乾的心靈,人們會追逐吃喝享樂,哪裡好玩我就哪裡去,拍照打卡,彷彿也是一種朝聖儀式的完成。
無關享樂的旅行也是有的,移動,單純只為了圓夢。詩人戴望舒的《雨巷》名句:撐著油紙傘,獨自彷徨在悠長,悠長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著一個丁香一樣的結著愁怨的姑娘。夢見伊瓜蘇瀑布夢見撒哈拉沙漠的人,再苦再遠再累都要去,實踐夢想的旅行,非常接近信仰,幾乎等於愛情。
還有一種旅行,無關享受也無關愛情,是自我流放。流這個字有被動的意思,隨波逐流,放則是一種完全的自覺,所謂旅者無懼,行者無疆。我在肯亞草原和南極大陸,感受過人在流放之中天地孤獨的況味。
人漸漸有了歲月,就不容易再一心追逐世間的風景。世界是一本讀不完的書,讀兩頁或讀二十頁,究竟又有什麼差別?此刻的我們,目的地是哪裡似乎不太重要了,更在乎的是一起旅行的人。
等到有一天,我們都老了,孩子都離開了,再去一次京都或巴黎,旅行是為了回憶年少的自己。
認真旅行的人,也一定是認真生活的人。每一段勇敢前進的人生,就是一趟不悔的壯遊。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詹宏志說,我們誕生之際時空已定,這個人生也就跟著「註定」,還有什麼方式能讓我們擴大實體世界與抽象世界的參與?在我看起來,也許只有「旅行」與「讀書」能讓我們擁有超過一個「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