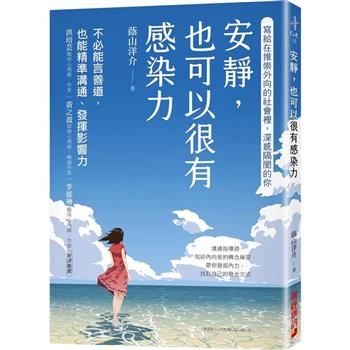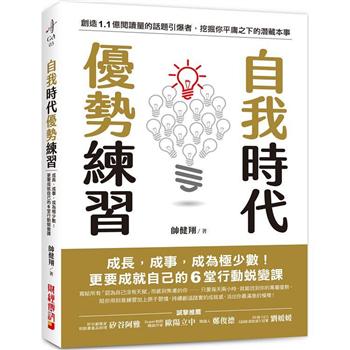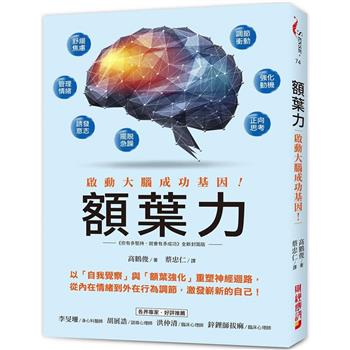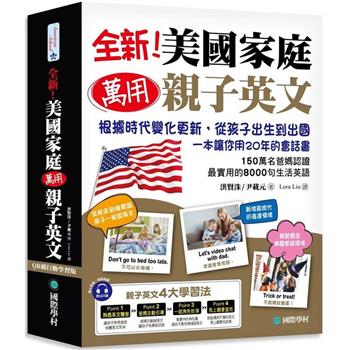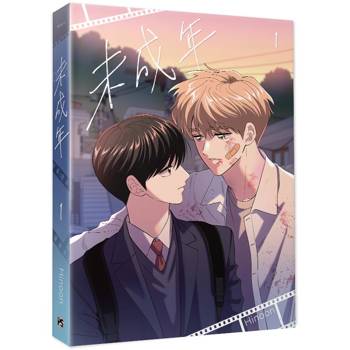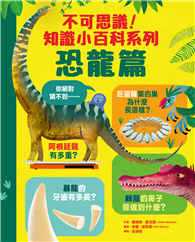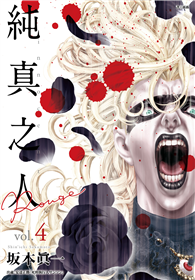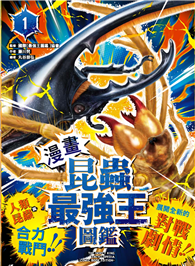前言:簡介最終理論
它的目標是要成為最終理論(final theory),那是個單一的框架,循此來統合宇宙的所有力,並編排出從膨脹宇宙的運動到次原子粒子的最細微舞動等所有動作。箇中難題在於要寫出一則具有高度數學優雅特性,並能把物理學完整包納在內的方程式。
好幾位舉世最出色的物理學家都潛心探尋。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甚至還為他的一次演說冠上一則帶有喜慶意味的標題―〈理論物理學是否終點在望?〉(Is the End in Sight for Theoretical Physics?)。
倘若這項理論成功了,那就會成為科學的巔峰成就。它就會成為物理學的聖杯,那會是一則公式,而且原則上從它就可以推導出其他所有方程式,從大爆炸開始,接著一路進展來到宇宙的終點。那會是自從古人問道:「世界是以什麼組成的?」以來,歷經兩千年科學探尋所成就的最終產物。
這是個令人屏息的願景。
愛因斯坦的夢想
我最早是在八歲童稚時期見識了這個夢想所帶來的挑戰。有一天,報紙發布一位偉大科學家去世的消息。報紙上刊出了一幀令人難忘的照片。
那是他的書桌的影像,上面有一本攤開的筆記簿。文字說明聲稱,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那位科學家,沒辦法完成當初由他所啟動的工作。我覺得很驚奇。到底是什麼問題那麼困難,連偉大的愛因斯坦都解決不了?
那本簿子裡面寫了他的未完成的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愛因斯坦稱之為統一場論(unified field theory)。他想擬出一則方程式,或許不比一英吋還長,藉此他就能夠,按照他的說法,「讀取上帝的心思」(read the mind of God)。
當時我並沒有完全意識到,那是個何等壯闊的問題,於是決定追隨這位偉人的腳步,期望能扮演個小角色,協力完成他的求知使命。
然而還有其他許多人都試過了,而且失敗了。如同普林斯頓的物理學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所述,通往統一場論的道路上,滿失敗嘗試的屍骸。
然而,時至今日,許多領導物理學家都認為,我們終於逐步向答案趨近了。
領先的(也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候選理論稱為弦論(string theory),根據這個學理,構成宇宙的並不是點狀粒子,而是纖小的振動弦,發出的每個音符分別對應於一顆次原子粒子。
倘若我們有一台倍率夠高的顯微鏡,我們就能看出,電子、夸克、微中子等,其實都只不過是模樣像橡皮圈的纖小環圈的振動。只要我們以種種不同方式來撥動橡皮圈充分次數,最後我們就會創造出宇宙間的所有已知次原子粒子。這就表示,所有物理學定律,全都可以歸結化為這些弦的和聲。化學就是我們能以那些弦奏出的旋律。宇宙就是一首交響樂。而上帝的心思,愛因斯坦以妙筆寫出的課題,則是在時空中共鳴的宇宙音樂。
這不單只是個學術問題。每當科學家破解了一種新的力,結果都改變了文明的進程,並扭轉了人類的命運。舉例來說,牛頓發現了運動和重力的定律,為機器時代和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麥可.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和詹姆斯.馬克士威(James Clerk Maxwell)有關電與磁的學理解釋,為我們的都市照明鋪設了坦途,並帶給我們強有力的電動馬達和發電機,以及藉由電視和收音機的即時通訊。愛因斯坦的 E = mc2 解釋了恆星的動力,並協助破解了核力(nuclear force)之謎。當埃爾溫.薛丁格(Erwin Schrödinger)、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其他人解開了量子理論的祕密,他們也為我們帶來了今天的高科技革命,還賦予我們超級電腦、雷射、網際網路和我們客廳裡面的種種驚人美妙器具。
追根究柢,那所有現代技術,全都根源自逐步發現世界基本作用力的科學家。現在,科學家已經有可能把統一這四種自然力―重力、電磁力和強核力與弱核力―的理論彙整起來,構成單獨一個理論。到最後,它就有可能破解科學一切範疇的最深奧謎團和問題,好比:
●大爆炸之前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一開始會出現大爆炸?
●黑洞的另一端有什麼東西?
●時光旅行有可能成真嗎?
●是否有通往其他宇宙的蟲洞?
●是否有更高維度?
●是否有平行宇宙構成的多重宇宙?
本書敘述探求這種終極理論的尋覓過程,以及當中種種離奇的迂迴轉折,鋪陳出了這段無疑是物理學史上最古怪的篇章之一。我們會回顧所有先前的革命,那些變革賦予我們種種美妙的技術產物,從牛頓革命開始,接著一路推演到電磁力的掌握,還有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的開展,以及今天的弦論。而且我們還會解釋,這項理論如何有可能也破解空間和時間的最深奧謎團。
批評陣營
不過障礙依然存在。儘管弦論激發出振奮激情,批評人士向來熱衷於指出它的缺陷。接著在種種宣揚炒作和狂熱舉止之後,真正的進展遲滯了。
最明顯的問題在於,儘管媒體阿諛稱頌那項理論的美和複雜性,我們卻沒有可測試的具體證據。我們一度寄望於大型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位於瑞士日內瓦郊外的史上最大型粒子加速器,期盼它能找到最終理論的確鑿證據,如今這卻依然捉摸不定。大型強子對撞機能夠找到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這種粒子號稱上帝粒子(God particle),卻只能算是最終理論一片細小的缺失拼圖。
儘管目前已經提出了好些深具雄心抱負的提案,建議建造威力更強大的機型,來接替大型強子對撞機,卻沒有人能擔保,這類昂貴的機器找不找得到任何東西,也沒有人能明確知道,到了哪個能量尺度,我們就能找到新的次原子粒子,好來驗證這項理論。
不過有關弦論的最重要批評或許就是,它提出多重宇宙的預測。有次愛因斯坦曾說,關鍵問題在於:當上帝著手創造宇宙,那時祂有沒有選擇餘地?宇宙是獨特的嗎?弦論本身是獨特的,然而它或許有為數無窮的解。物理學家把這個稱為地景問題(landscape problem)——我們的宇宙其實有可能只是眾多解之一,而且同等可信的解,如浩瀚汪洋般充沛。倘若我們的宇宙只是眾多可能性當中的一個,那麼哪一個是我們的?我們為什麼住在這處宇宙,而不是另一處裡面?那麼,弦論的預測力在哪裡呢?那是個「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呢,或者是「萬可理論」(theory of anything)呢?
我承認我和這項搜尋連帶有關。我從一九六八年起就投身從事弦論研究,它就是在那年偶然出現,沒有公開宣布,也完全出人意料之外。我見識了那項理論的驚人演變,從單獨一項公式,發展成為一門學科,而且研究論文可以填滿整座圖書館。如今,弦論構成了全世界領導實驗室所進行大半研究的根本基礎。期盼本書能帶給各位一項平衡的、客觀的分析,兼顧鋪陳弦論的突破性發展和侷限性。本書還會解釋,為什麼這項探尋抓住了世界頂尖科學家的想像力,還有為什麼這項理論醞釀出了那麼強大的熱情和爭議。
第一章一以貫之——古老的夢想
凝望夜空壯麗景象,天際環繞著燦爛星辰,我們很容易被那種令人屏息、十足雄偉的氣勢給湮沒。我們的關注焦點轉向歷來最神秘的幾道問題。
宇宙有宏觀設計嗎?
我們如何理解看似毫無意義的宇宙?
我們的存在有什麼節律和道理嗎,或者這完全是毫無意義的?
我想起了史蒂芬•克萊恩(Stephen Crane)寫的詩:
有個人對宇宙說:
「閣下,我存在!」
「不過,」宇宙回答道,
「這件事可沒有讓我產生什麼責任感受。」
希臘人是最早認真嘗試釐清我們周遭世界混沌亂象的民族之一。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認為,萬物都可以歸結為四大基本成份(地、氣、火和水)的混合產物。不過,這四種元素是如何醞釀出世界的豐富複雜性?
就這個問題,希臘人提出了至少兩個答案。第一個答案出現得比亞里士多德更早,由哲學家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提出。他認為,萬物都可以歸結為纖小的、看不見的、不可毀壞的粒子,他稱之為原子(atom),希臘文的意思是「不可分割的」。然而批評者指出,原子的直接證據是不可能取得的,因為它們太小了,觀測不到。不過德謨克利特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間接證據。
舉例來說,想像一枚金戒指。多年下來,那枚戒指開始耗損。失去了一些東西。每天都有一些纖小物質碎片從戒指磨耗脫落。因此,儘管原子是看不見的,它們的存在仍是可以間接測定的。即便到了今天,我們的先進科學,大半仍是間接完成的。我們知道太陽的組成成分、DNA的細部結構,還有宇宙的年齡,全都歸功於這樣的測定結果。我們知道這一切,即便我們從來沒有前往探訪恆星,或者鑽入DNA分子或者目睹見識大霹靂。當我們討論談到試圖證明統一場論的諸般嘗試之時,直接和間接證據的這種區辨,就會變得至關重要
第二條途徑由偉大數學家畢達哥拉斯開創。畢達哥拉斯發揮獨到眼光,把數學描述應用於音樂等塵世現象,相傳他注意到彈撥里拉琴琴弦發出的聲音,和鎚擊鐵桿共鳴聲響的雷同之處。他發現,兩種聲音都發出以特定比率振動的音樂頻率。因此,美妙悅耳如音樂,其根源仍是出自共鳴的數學。他認為,這或許便表明,我們在身邊所見事物的多樣性,必然也遵守這相同的數學規則。
所以,起碼我們這個世界的兩大理論出自古希臘:有關萬物都是以看不見的、堅不可摧的原子所組成的觀點,以及自然多樣性能以振動數學來描述。
不幸,隨著古典文明崩潰,這些哲學上的討論和爭辯全都流失了。有關於世上可能有某種範式可以用來解釋宇宙的理念被人遺忘,塵封了將近一千年。黑暗籠罩西方世界,科學研究大半都被迷信、魔法和巫術的信仰所取代。
文藝復興時期的重生
十七世紀期間,好幾位偉大的科學家挺身挑戰既定秩序,投入探究宇宙本質,然而面對他們的是嚴苛對抗和迫害。約翰尼斯•克卜勒(Johannes Kepler)是最早應用數學來說明行星運動的人士之一,他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魯道夫二世(Emperor Rudolf II)的皇家數學家,也或許他從事科學研究之時,虔誠納入了種種宗教元素,才得倖免未受迫害。
當過僧侶的焦爾達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一六〇〇年,他以異端邪說罪受審並被判死刑。他遭封口並在羅馬赤裸遊街示眾,最後被綁上火刑台燒死。他的首要罪名?宣揚在環繞其他恆星的行星上可能存有生命。
偉大的伽利略,實驗科學之父,險些遇上相同的命運。不過伽利略不像布魯諾那麼頑強,他在死亡之苦威脅下撤銷自己的理論。不過他以他的望遠鏡留下了一項持久遺贈,留給我們科學史上最具有革命性和煽惑性的發明。有了望遠鏡,你就可以自己親眼看到,月球密密麻麻滿佈隕石坑;金星有不同的相位,而且和它的繞日軌道對應相符;木星有成群衛星,這一切全都是異端邪說。
只可惜,他遭軟禁,不得會見訪客,最後還失明。(據說那是由於他有次用望遠鏡直接觀測太陽所致。)伽利略死時窮途潦倒。不過就在他死亡那年,一個嬰兒誕生在英格蘭,而且他會完成伽利略和克卜勒當初未能完成的理論,也帶給我們一項天空的統一理論。
| FindBook |
有 10 項符合
神的方程式:對萬有理論的追尋的圖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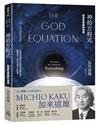 |
神的方程式:對萬有理論的追尋 作者:加來道雄 / 譯者:蔡承志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4-2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神的方程式:對萬有理論的追尋
以加來道雄特有的熱忱和清晰文筆寫成,
娓娓道出了歷來科學家們前仆後繼追尋「神的方程式」的故事。
具有權威性又明晰易懂的出色之作!
讀過此書,相當於將整個物理發展史走過一遍。
神的方程式——「萬有理論」,它是科學的巔峰成就、物理學的聖杯,從這則公式可以推導出其他所有方程式,那會是自從古人問道:「世界是以什麼組成的?」以來,歷經兩千年科學探尋所成就的最終產物。這是個令人屏息的願景。
加來道雄寫出這一段求知的故事——努力追尋「萬有理論」,一個革命性的「神的方程式」。愛因斯坦投入一生致力尋覓這個難以捉摸的物理聖杯,想藉此要把宇宙間所有力聯繫在一起,但他始終沒有找到它。物理學界幾位最偉大的心智,從霍金到布萊恩•葛林(Brian Greene),也接手展開搜尋,但迄今仍沒有人成功。
在《神的方程式:對萬有理論的追尋》這本書中,知名理論物理學家加來道雄帶領讀者踏上一趟令人難以置信的旅程,走過一段史詩般蜿蜒曲折的路途,那也是他終身大半期間都興味盎然的謎團。他引領我們走過現代物理學的關鍵爭執,從牛頓的重力理論經由相對論和量子力學,乃至於弦論領域的最晚近發展,讓讀者了解這段物理學家們前仆後繼探尋萬有理論的辛苦過程。這是一段講述令人眼花撩亂的突破,以及山窮水盡的死胡同的故事,由加來道雄秉持感人肺腑的熱情,以他的生花妙筆清楚道出。
【專文導讀】
侯維恕|臺灣大學物理學系講座教授
【專業推薦】
從古到今,「神」一直存在於人類的各種文化裡。對於科學家而言,「神」是造物者或大自然的代稱,而神的方程式即是大自然運行的規律。這本書介紹了科學家們努力追尋的過程,與發現規律的感動。正是這些過程與感動,讓科學家們樂此不疲,也將使讀者如身歷其境般地踏上探險之旅!
—— 江瑛貴|清華大學天文研究所教授
科學家們有個夢,夢想有一天能找到將四種自然力統一的萬能方程式,期待它能解開萬物的規律,宇宙的起源。這是一項艱鉅但充滿驚喜的工作。作者以淺顯易懂的故事敘述,展現了科學家們追根究柢的態度、鍥而不捨的科研歷程, 引人入勝。
—— 李景輝|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到底是否存在著一個萬有理論,能解釋我們整個宇宙的所有現象?弦理論似乎是目前最有可能的候選人。身為相關理論研究的先驅,加來道雄博士在本書中從早年的物理研究,一直論述到弦理論目前的發展,讀過此書,相當於將整個物理發展史走過一遍。儘管加來教授為從事弦理論的研究,在本書中也提及有些物理學家對弦理論的疑慮,使我們能從不同角度探討此一問題,本書是一本值得推薦的科普著作。
—— 周 翊|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所長
【國內專家學者齊聲推薦】
江瑛貴|清華大學天文研究所教授
李景輝|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周 翊|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所長
高涌泉|臺灣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陳文屏|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講座教授
【各界好評推薦】
一段明晰易解的探索求知歷程,把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和量子理論結合起來,創建出有關宇宙之本質的無所不包的「萬有理論」。
——安得魯‧安東尼(Andrew Anthony),《觀察家報》(The Observer)
加來道雄運用易於掌握的現實闡述來解釋深奧的數學,並說明理論物理學突破是如何對人類經驗產生了有形的影響……撰述出既令人費解,卻也清晰易讀令人訝異的成果。
——皮帕‧貝利(Pippa Bailey),《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這是一位高明的科學溝通者撰寫的出色書籍……倘若有任何人能掀開弦論的深奧數學和物理學的神祕面紗,那就是加來道雄了。而且在這本精彩的小書當中,他也正是辦到了這點——以清楚簡單的語彙,解釋了種種概念上的突破、死胡同和懸而未決的問題——投入搜尋大一統萬有理論……《神的方程式》令人驚豔……加來道雄,完美的說書人,為我們帶來一套引人入勝的、未經修飾的論述……他的書提出了理論物理學的最前沿理念,並讓讀者在下一場重大突破發生之時做好準備。」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具有權威性又明晰易懂!
——《自然》(Nature)
加來道雄以生花妙筆評述我們這處宇宙的結構,彰顯知識巨人所做出的貢獻,闡述延續那趟艱鉅探索使命的人士,如何在數十年期間投入尋覓捉摸不定的萬有理論……檢視這種誘人理論,加來道雄勾勒出它的許諾、問題和它所展現的令人嘆為觀止,幾乎無從領會的種種可能性。加來道雄的這部最新作品,捕捉了宇宙、我們的行星和有關於我們自己的令人敬畏又神祕難解之美,而且凡是投入思忖存在的任何人,對此都會心醉神迷。
——《書單》(Booklist)
令人迷醉……加來道雄發揮他釐清費解概念的專才,讓這部作品成為真正令學子大開眼界的作品。
——《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記錄「物理學聖杯」之搜尋的老練著述……深具啟發性……一部重要的著作。
——《柯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作者簡介:
加來道雄 Michio Kaku/超弦論奠基者、當代物理大師
日裔美籍科學家,現為紐約市立大學理論物理學教授,也是國際公認的理論物理學權威。哈佛大學畢業,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物理博士,是建立「超弦理論」的科學家之一。他寫了幾本頗受歡迎的物理教科書,成為許多一流實驗室的指定讀物。過去十年來,他在紐約市電台主持一個現場call in,全美播放,是相當受聽眾歡迎的科普教育節目。他從小喜歡閱讀科幻小說,尤其深受艾西莫夫啟蒙。由於當時小說充斥著交待不清的物理情節,促使他長大後立志從事理論物理研究。著作包括《穿梭超時空》(商周)、《平行宇宙》(暖暖書屋),以及近年來的《2100科技大未來》、《2050科幻大成真》及《離開太陽系:移民火星、超人類誕生到星際旅行,探索物理學家眼中的未來世界》(時報出版)。目前加來道雄和家人定居紐約。
譯者簡介:
蔡承志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學碩士,第七屆「吳大猷科普著作獎」翻譯類金籤獎得主。一九九四年起業餘投入科普書翻譯,一九九九年轉任全職迄今,期間也從事Discovery頻道字幕翻譯三年。累計作品近九十本,包括:《眺望時光的盡頭》、《給未來總統的物理課》、《星際效應》、《好奇號帶你上火星》、《無中生有的宇宙》、《時空旅行的夢想家:史蒂芬.霍金》、《大人的物理學:從自然哲學到暗物質之謎》、《詩性的宇宙》、《大轉折:百年科學匯流史》、《伊波拉浩劫》、《下一場人類大瘟疫》和《最後一個知識人》等。
章節試閱
前言:簡介最終理論
它的目標是要成為最終理論(final theory),那是個單一的框架,循此來統合宇宙的所有力,並編排出從膨脹宇宙的運動到次原子粒子的最細微舞動等所有動作。箇中難題在於要寫出一則具有高度數學優雅特性,並能把物理學完整包納在內的方程式。
好幾位舉世最出色的物理學家都潛心探尋。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甚至還為他的一次演說冠上一則帶有喜慶意味的標題―〈理論物理學是否終點在望?〉(Is the End in Sight for Theoretical Physics?)。
倘若這項理論成功了,那就會成為科學的巔峰成就。它就會成為物理...
它的目標是要成為最終理論(final theory),那是個單一的框架,循此來統合宇宙的所有力,並編排出從膨脹宇宙的運動到次原子粒子的最細微舞動等所有動作。箇中難題在於要寫出一則具有高度數學優雅特性,並能把物理學完整包納在內的方程式。
好幾位舉世最出色的物理學家都潛心探尋。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甚至還為他的一次演說冠上一則帶有喜慶意味的標題―〈理論物理學是否終點在望?〉(Is the End in Sight for Theoretical Physics?)。
倘若這項理論成功了,那就會成為科學的巔峰成就。它就會成為物理...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導讀
前言:簡介最終理論
第一章 一以貫之―古老的夢想
第二章 愛因斯坦對統一的探求
第三章 量子崛起
第四章 幾近萬有理論
第五章 暗宇宙
第六章 弦論興起:指望和問題
第七章 尋找宇宙的意義
結論
致謝
註釋
文獻選讀
前言:簡介最終理論
第一章 一以貫之―古老的夢想
第二章 愛因斯坦對統一的探求
第三章 量子崛起
第四章 幾近萬有理論
第五章 暗宇宙
第六章 弦論興起:指望和問題
第七章 尋找宇宙的意義
結論
致謝
註釋
文獻選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