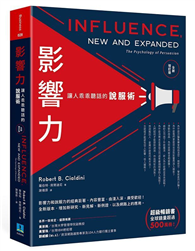|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離騷未盡的圖書 |
 |
離騷未盡 作者:楚影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5-03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113 |
二手中文書 |
$ 251 |
小說 |
電子書 |
$ 266 |
歷史小說 |
$ 300 |
現代小說 |
$ 300 |
中文書 |
$ 300 |
武俠/歷史小說 |
$ 300 |
文學小說 |
$ 323 |
小說/文學 |
$ 342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Readmoo 評分:
圖書名稱:離騷未盡
「楚影無疑是個痴心的詩人,他將〈離騷〉的故事,架骨骼填血肉地從楚國一路行吟而來,但願彼時江上風凜,腰沒滾滾疾水,形單影隻的落魄詩人屈原的魂靈知悉了,終能獲得一絲寬慰。」──詩人、散文家陳冠良
屈平雖出身世家名門,但年僅弱冠就當了楚懷王的左徒──這個地位僅次於令尹的高官,仍讓他受到朝中許多人的冷眼嘲弄甚至敵視,尤其是因為姐姐鄭袖得寵而跟著雞犬升天的公子子蘭。然而屈平面對的挑戰不僅是子蘭一人,而是他背後代表的守舊勢力。自從吳起變法後,既得利益的守舊派便不斷趁勢反撲,悼王薨逝之後,守舊派更是將吳起所做的一切變革盡皆廢除,楚國多年以來的層層積弊遂無從清理。內有國賊如此,外更有強秦時時窺伺,留給屈平興利除弊、強國富民的時間不多了……
作者楚影為了貫徹自己的筆名,從古代流傳下來的文字裡接近屈原;當他看見在「恃強凌弱,以眾暴寡」的時代中,屈原如何去守護他的國家,卻無法實現心願,最終只換來悲傷的結局,讓他決定要為屈原寫下一部小說:
屈原不會知道千百年之後,這個世界上有我的存在,可是相對遙遠未來的我,卻能夠看見他的文字,進而寫下自己的篇章;這是否說明著有一種寄託,只要透過時間的等待,一定會遇到傳承意志的人。
於是我突然明白,如果此生也背負著一項使命,那應該是要對屈原說:「致兩千年前的你,我知道〈天問〉即是問天──『時間究竟是什麼?』我聽見了,所以,這部小說,就是我要給你的回音。」
作者簡介
楚影
一九八八年生。曾獲優秀青年詩人獎。
著有詩集《你的淚是我的雨季》、《想你在墨色未濃》、《把各自的哀愁都留下》、《我用日子記得你》、《指路何去》。小說《封魂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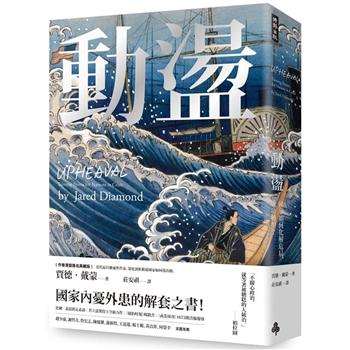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 塔木德:猶太人的致富聖經[修訂版]:1000多年來帶領猶太人快速累積財富的神祕經典](https://media.taaze.tw/showLargeImage.html?sc=1110069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