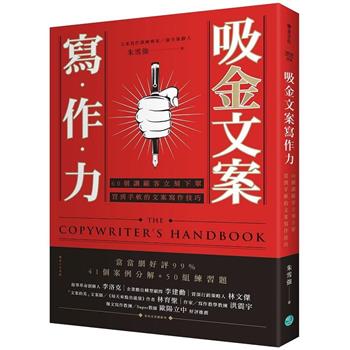天地不仁,不擇手段。
法國文壇最高榮譽龔古爾獎得獎小說《天上再見》精彩完結篇!
被掩蓋的歷史,被遺棄的孩子。
自私的愛,人人為己。
若諸善有序,最後誰能得到救贖?
一九四○年,大戰一觸即發,納粹德軍即將進入法國。當年那名陪伴在愛德華與阿爾伯特兩名逃兵身旁的小女孩,路易絲如今長大成人。只是她不幸捲入一椿命案,醜聞逼得她在巴黎無處容身,卻在無意間發現母親生前留下的情書,當中的祕密令她震顫,世間像她孤身無依的人有多少?同一時間,往南方的路上,每日成千上萬的市民拉成一列迤長的隊伍,無人能夠預測這場浩劫何時會終止……
『到處都是臉,一張又一張的臉。
這列綿延不絕的送葬長隊,成了我們難以面對自己苦難與戰敗的一面殤鏡。』
歷經十年,皮耶‧勒梅特以三部曲的篇幅,描寫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的法國──表面風光,人性敗壞。萬眾期待的完結篇始於希特勒侵略荷比盧,直到占領巴黎為止。短短一個月內,法國境內湧現上千萬人攜家帶眷,從巴黎逃向南方的羅亞爾河區,成了西歐史上首次爆發最大規模的難民潮。作者更將敘事視角切換到社會底層的小人物身上,孤苦伶仃懷藏祕密的路易絲,嗜財如命的勞爾、秉性純良的加百列,為病中愛妻千里返鄕軍士長費爾南、身分神祕的騙子德希雷,他們各有各的道德模糊與生存智慧。皮耶‧勒梅特以緊湊文字節奏帶出連環冒險,情節難以預料,高潮迭起,透過小人物的經歷,寫實地描繪了法國之殤。正如法國文豪斯湯達爾曾述:「一部小說猶如一面在大街上走的鏡子。」勒梅特的這面鏡子不僅顯現法國滿目瘡痍的悲傷與恥辱,也寫出了苦難靈魂中潛藏的人性與希望。
「十五天內有上千萬人走到街上,我覺得在當代歷史中,沒有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事件。而這件事又成為了一面鏡子,反射出我們每個人的真實。」──皮耶‧勒梅特
法國年度暢銷十大暢銷書
法國《文學雜誌》年度選書
「假戰」──虛假信息漫天謊言,百姓家破人亡。
揭露法國近百年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令人欲罷不能。
「我真希望再多兩百頁,閱讀皮耶‧勒梅特的小說,是一種享受!」
──法國讀者拭淚推薦
『災難中的孩子』三部曲
──向大仲馬致敬
首部曲《天上再見》
二部曲《燃燒的玫瑰》
最終曲《殤鏡》
獲獎紀錄
入圍2020 年Audiolib 獎決選名單
國際好評
「皮耶‧勒梅特是當代的大仲馬。」──《巴黎人報》
「令人嘆為觀止的輝煌。」──《費加羅報》雜誌
「這簡直是一部黑白電影。」──《解放報》
「史詩般的出走。」──《世界報》
「這是一本高品質、雄心勃勃的文學小說。壯麗磅礡,獨具一格,充滿生命力!」──《法國新聞廣播電視台》
| FindBook |
有 8 項符合
殤鏡的圖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電子書 |
$ 364 |
歐美文學 |
$ 410 |
中文書 |
$ 411 |
法國現代文學 |
$ 411 |
法國文學 |
$ 411 |
文學小說 |
$ 411 |
新書推薦79折起 |
$ 442 |
小說/文學 |
$ 46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殤鏡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皮耶.勒梅特(Pierre Lemaitre)
1951年生於巴黎,法國作家、編劇,龔古爾文學獎得主。
曾任文學教師多年。他迄今的小說作品備受各界讚賞,譽為犯罪小說大師,曾經榮獲2006年干邑處女作小說獎、2009年最佳法語推理小說獎,以及2010年Le Point週刊歐洲犯罪小說獎。《籠子裡的愛麗絲》榮獲2013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CWA)國際匕首獎。同年,以描寫一次大戰的作品《天上再見》,榮獲龔古爾文學獎.暢銷突破兩百萬本,並榮獲國際匕首獎。並以《籠子裡的愛麗絲》三部曲完結篇《凡人的犧牲》勇奪第三座國際匕首獎。
膾炙人口的「卡繆探長」三部曲:《籠子裡的愛麗絲》《魔鬼的手稿》《凡人的犧牲》在日本造成轟動,連續三年蟬聯「週刊文春」年度十大推理小說第一位。《籠子裡的愛麗絲》更創下日本推理史上首見年度推理選書六冠王的輝煌紀錄。
2019年出版《燃燒的玫瑰》登上法國年度暢銷排行榜。
最新代表作『災難中的孩子』三部曲──《天上再見》《燃燒的玫瑰》《殤鏡》。
譯者簡介
繆詠華
台法文化獎得主。
中英法文專職譯者、作家、電影字幕翻譯師、文物導覽員。著有《巴黎文學散步地圖》及《長眠在巴黎》二書。電影字幕翻譯近千部。譯有《燃燒的玫瑰》、《天上再見》、《三天一生》、《凡人的犧牲》、《非人》、《犬列島》等作品二十餘部。故宮文物中英法三語導覽志工。
皮耶.勒梅特(Pierre Lemaitre)
1951年生於巴黎,法國作家、編劇,龔古爾文學獎得主。
曾任文學教師多年。他迄今的小說作品備受各界讚賞,譽為犯罪小說大師,曾經榮獲2006年干邑處女作小說獎、2009年最佳法語推理小說獎,以及2010年Le Point週刊歐洲犯罪小說獎。《籠子裡的愛麗絲》榮獲2013年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CWA)國際匕首獎。同年,以描寫一次大戰的作品《天上再見》,榮獲龔古爾文學獎.暢銷突破兩百萬本,並榮獲國際匕首獎。並以《籠子裡的愛麗絲》三部曲完結篇《凡人的犧牲》勇奪第三座國際匕首獎。
膾炙人口的「卡繆探長」三部曲:《籠子裡的愛麗絲》《魔鬼的手稿》《凡人的犧牲》在日本造成轟動,連續三年蟬聯「週刊文春」年度十大推理小說第一位。《籠子裡的愛麗絲》更創下日本推理史上首見年度推理選書六冠王的輝煌紀錄。
2019年出版《燃燒的玫瑰》登上法國年度暢銷排行榜。
最新代表作『災難中的孩子』三部曲──《天上再見》《燃燒的玫瑰》《殤鏡》。
譯者簡介
繆詠華
台法文化獎得主。
中英法文專職譯者、作家、電影字幕翻譯師、文物導覽員。著有《巴黎文學散步地圖》及《長眠在巴黎》二書。電影字幕翻譯近千部。譯有《燃燒的玫瑰》、《天上再見》、《三天一生》、《凡人的犧牲》、《非人》、《犬列島》等作品二十餘部。故宮文物中英法三語導覽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