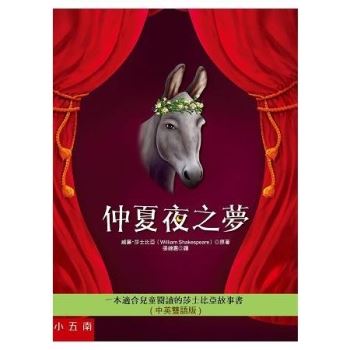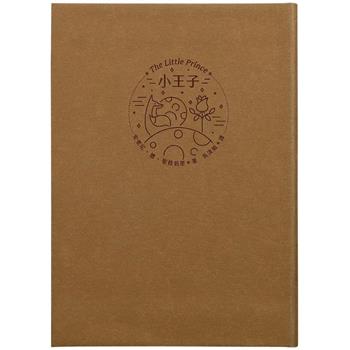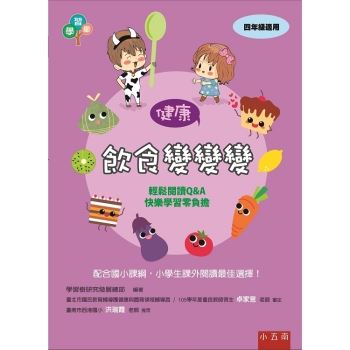第一章 熱飲、電熱毯與孤獨──溫度與人際關係
謝爾頓走進自家公寓的客廳,看到好友李奧納德與霍華德窩在那裡,現場氣氛緊繃。
「怎麼了?」他問道。
「霍華德今晚要睡這裡,他跟老媽吵架。」李奧納德解釋。
「你幫他倒一杯熱飲了嗎?」
李奧納德一臉不解地瞪著謝爾頓看,霍華德則是癱坐在沙發上,不發一語。
「李奧納德!這是社交禮儀,朋友鬱卒時,你應該幫他倒杯熱飲,比如熱茶之類的。」
「來杯茶確實不錯。」霍華德坦言。
謝爾頓是美劇《宅男行不行》(The Big Bang Theory)的主角之一,網路迷因「以熱飲安撫朋友」可能就是源自於他。不過,認為身體溫暖與精神支持是相通的人,肯定不只他一個。幾個世紀以來,詞曲家與詩人把愛與關懷跟暖心的溫度連結在一起,孤獨與背叛則令人心寒。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唱道:「回到家,渾身暖洋洋。」巴西樂團Jota Quest也高唱:「愛是溫暖心靈的暖流。」披頭四樂團(Beatles)聲稱幸福是「一把溫暖的槍」(a warm gun),這句歌詞諷刺地扭曲了《史努比》漫畫家查爾斯.舒茲(Charles M. Schulz)的名言「幸福是一隻溫暖的小狗」(a warm puppy)。
我們的日常用語也充滿類似的譬喻。我們以「溫暖、熱情」(warm)來形容有愛心、反應熱烈的人。我們作客時,可能獲得「熱情接待」或「冷眼對待」。波蘭人可能mówiciepło(熱情地談論)某人;在法國,大家有時會用battrefroid a quelqu’un的說法(字面意思是「冷對某人」),意思是「故意冷落某人」。
早在一九四六年,現代社會心理學之父阿希(Solomon Asch)的實驗就發現,描述一個人時,加入「熱情」或「冷淡」等字眼,會明顯改變別人對那個人的看法。別人可能認為你很聰明、技巧高超、很堅毅,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究竟是熱情還是冷漠。阿希發現,一般人認為熱情的人是慷慨大方、善於社交、溫厚良善的。冷漠不僅表示你缺乏上述特質,大家也會覺得你展現出相反的特質:小氣、疏離、刻薄。阿希認為,冷熱之別是社會觀感的基礎。然而,科學研究經過多年才揭開一個事實:這種根本特質不是簡單的語言學或人為譬喻的產物。我們是在「生理上」,真實感受到人際關係中的「冷暖」。
現在把時間快轉到二十一世紀。二○○八年,研究人員在耶魯大學的宏偉建築中做了東西。不久,電梯門打開,她們一起走了出來。那位學生不知道的是,實驗的第一部分已經結束了。一旦進入實驗室,研究人員會請她讀一段文字,那段文字是描述一個虛構的人「某甲」,某甲是聰明、熟練、勤奮、堅定、務實、謹慎的。學生的任務是針對十種性格特徵,為某甲打分數,其中五種性格特徵在語義上與「熱情」或「冷淡」有關。
這項實驗總共有四十一位大學生參與,他們不知道的是,研究人員已經把他們分成兩組。在電梯裡,其中一半人被要求拿著的,是從當地咖啡館買來的熱咖啡;另一半的人是拿冰咖啡。這個小差別就足以影響學生對某甲的觀感,相較於拿著冰咖啡的人,拿著熱咖啡的人明顯覺得某甲比較「熱情」。對心理學家來說,這種發現是突破性的。那表示,身體實際感受到溫暖,確實可能增加心理或社交上的溫暖印象。
這個實驗就此敞開了研究的閘門(包括我自己的研究):研究溫度與社交性之間的關聯。如果暫時拿著一杯熱飲,就足以讓我們覺得某人比較善於交際、值得信賴,那是否也能讓我們覺得自己跟他比較親近呢?不是身體上的親近,而是心理上與社交上的親密─就像我們說「親近的朋友」或「親近的家人」那種親近?我決心找出答案。
電梯裡拿咖啡的實驗做完一年後,我和荷蘭烏特勒支大學(Utrecht University)的指導教授一起發表了我們的變化版本。我們設計了一個實驗室的研究,當實驗人員忙著在一項簡單的實驗。一位自願參與的大學生走進心理系大廳,她在那裡遇到一名女性研究助理,說要帶她去四樓的實驗室做實驗。那位助理的手上拿了很多東西:一杯咖啡、一個寫字板、兩本課本。她們兩人一起走向電梯。
在電梯裡,研究助理請那個學生暫時幫她拿著杯子,好讓她在寫字板上隨手記下一些筆電上安裝問卷時,她會請參與者幫忙拿著一個杯子。半數參與者是握著裝熱茶的杯子,另一半是握著裝冰茶的杯子(幾年前,冰咖啡在荷蘭還不是常見的飲料,我們擔心荷蘭人覺得冰咖啡很怪,所以改用茶。荷蘭人比較熟悉熱茶與冰茶)。無論是在電梯裡、還是在實驗室裡,讓人拿著一杯熱飲或冷飲,都會影響參與者對他人的看法。
接下來,是我們實驗的下一步。我們請參與者看一份基本的評估量表,那是畫在一張紙上的幾個簡單的文氏圖(Venn diagram)。每個文氏圖是由兩個圓圈組成。在量表的左端,兩個圓圈幾乎沒有接觸;在量表的右端,兩個圓圈幾乎完全重疊。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兩個圓圈的重疊面積持續增加。我們請參與者假設其中一個圓圈代表他本人,另一個圓圈代表實驗人員。我們想知道參與者畫出的兩個圓圈是否有重疊;如果有重疊,重疊比例是多少?我們已經知道,人際關係更好(更投入、更忠誠、更融洽)的人,通常會把圓圈畫得比較重疊。在我們的實驗中,拿過熱飲的人所畫的圓圈,比拿過冷飲的人所畫的重疊更多。我們因此推論,熱飲組覺得他們自己與實驗人員的自我更融合。簡言之,他們感覺自己與實驗人員更親近了,只因為實驗人員給了他一杯熱飲,而且不用喝下肚,只要拿著就好。
後來,我們又繼續做相關的實驗,結果發現,參與者甚至會開始使用更多的詞彙來描述自己與他人的親近感。這項研究是這樣運作的:在烏特勒支大學,我們不是請參與者握住熱杯或冷杯,而是請他們待在一個暖氣房(攝氏二十二至二十四度)或冷氣房(攝氏十四至十八度)裡。接著,讓他們觀看一段西洋棋的紅棋與白棋移動的影片。我們請參與者描述他們看到的情況時,一位待在暖氣房的參與者提到:「我看到一個紅棋跟在其他棋子後面,後來吃掉那些棋子。她先吃下左邊的第二棋子,然後吃掉右邊的棋子。接著,她往後移動,又吃下一個棋子。之後,她往前移動,又吃下一個棋子。」一個待在冷氣房的參與者說:「小兵與皇后去冒險,但皇后不喜歡他,自己走了。這對白方不利,她的行為引發了衝突與問題。小兵只是個蠢蛋,他放任皇后消失,後來大家都很不滿,連驕傲的國王與小兵都很不滿。」不管是待在冷氣房還是暖氣房,參與者都很容易採用擬人化的敘述。不過,待在暖氣房的參與者使用較多的動詞來描述看到的情況,待在冷氣房的參與者比較喜歡用形容詞。
▌究竟只是譬喻,還是生理需要?
語言的譬喻及謝爾頓所說的「社交禮儀」,讓我們常以玩笑心態來看待身體冷熱與社交冷熱之間的關係,那種輕忽的態度往往有礙、而不是有助於深入探索與思考。即使是發展心理學家或熟悉發展假設的門外漢,也可能覺得我們觀察的結果是「顯而易見」或「不證自明」的。嬰兒時期,父母照顧我們的時候,我們學到了溫度與關愛之間的關聯。之後,我們在一生中反覆地同時體驗心理與生理上的溫暖,又會持續強化這些連結。想想新生兒依偎在母親的臂彎裡,喝飽了奶,感到安全,免受風寒。這種連結很容易就流入我們的語言與譬喻中,因此我們稱那些充滿愛心的人「古道熱腸」,稱那些冷漠的人「冷若冰霜」。後來,當我們觸摸溫暖的東西時,即使是熱騰騰的咖啡那樣平淡無奇的東西,也會喚起一些跟信任、包容、關愛有關的理性與感性聯想。把暖呼呼的杯子捧在手心裡,就像感受到慈父慈母的撫摸一樣。
以「關聯」來解釋這種現象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在於這聽起來很符合常識,而常識是生活中的寶貴資產。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與精力去探索及深思遇到的每件事情、煩惱每個決定,然後還努力去證明它合情合理。常識是一種經驗法則,它讓我們對生活中的多數事情有足夠的瞭解或想像,足以應付日常大小事。穿越車水馬龍的街道之前,注意左右來車是一種常識;過馬路只需要這點經驗法則就夠了,沒必要站在街角盤算活著穿越馬路的機率,只要看看左右兩邊即可。
然而,科學研究沒那麼急著完成,愛因斯坦有句名言:「常識是十八歲以前累積的各種偏見。」科學並不排斥常識,但要放眼常識以外、常識底下、常識旁邊的一切。以生理溫度與心理溫度之間的關聯為例,新的實驗資料不斷湧入期刊。這些研究的數量與內容都顯示,人生早期的學習與譬喻還不足以解釋所有的關聯。
在多倫多大學的一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請五十二名大學生玩一種名叫Cyberball的電腦遊戲─心理學家喜歡用這種遊戲來讓參與者感到孤立。這個遊戲的運作如下:研究人員告訴你,你將玩一種線上遊戲,你會和另兩名對象一起拋接一顆虛擬的球,那兩人隱身在某處的兩台電腦之後,你不認識他們,他們也不認識你。遊戲很簡單,它沒有《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的視覺效果,畫面上只是陽春的小人物在扔球。研究人員沒告訴你的是,「另兩人」其實不存在,它們是軟體的一部分;它們存在的唯一目的,只是為了讓你產生歸屬感或孤立感。如果實驗者要讓你產生孤立感,「他們」只會拋球給你一、兩次,然後就忘了你的存在;他們兩人會自己玩在一起,讓你鬱悶地盯著螢幕看。然而,如果實驗者要讓你產生歸屬感,另兩人在遊戲中會不斷向你拋球。
在多倫多大學的那個實驗裡,幾位參與者在Cyberball遊戲中遭到孤立後,研究人員請他們去做另一項據稱不相關的研究(這裡給各位一個小建議:心理學家告訴你「另一個」研究「不相關」時,絕對不要信以為真)。在這項研究中,研究人員請參與者以零到七分來評鑑食物,零分是「超想吃」,七分是「超不想吃」。他們準備的食物包括熱咖啡、熱湯、蘋果、餅乾、可樂等等,也就是說,有熱食、也有冷食,有鹹食、也有甜食。
實驗結果的分析,顯現出一個清晰的型態。在遊戲中遭到忽視而感到孤立的人,比那些經常接到球的人更喜歡熱食。然而,談到他們有多想吃對照組的食物時(例如可樂或蘋果),被忽視的參與者和被接納的參與者並沒有差異。所以,下次你覺得伴侶很疏離又突然很想喝熱茶或熱湯時,這種情況下的饑餓感可能與體溫調節比較有關,而不是跟消化系統有關;溫暖的擁抱也許更能滿足你的渴望。
你和朋友大吵一架後,如果突然想啟動恆溫器,那也很正常。多倫多大學的同一團隊做了另一個相關的實驗,他們請Cyberball遊戲的參與者估計室溫(據稱是維修人員問參與者的)。有些人猜室溫是攝氏十一度,有些人猜室溫接近攝氏四十度。遭到忽視的參與者所臆測的平均溫度,比獲得接納的那群所臆測的平均溫度低。兩群人臆測的平均溫度差了近攝氏三度;遭到忽視使學生的體感更冷。
在一些評論者的眼中,多倫多大學的那項研究結果好到令人難以置信。順道一提,當時我也做了實驗,研究社交溫度與實體溫度之間的關聯,但那時我還沒準備好發布研究結果。後來,我對研究結果比較有信心了。我的結果和多倫多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我發現,參與者覺得自己和其他人不同時,會覺得周遭溫度較低;當參與者覺得自己和其他人相似時,就會覺得周遭溫度較高。當參與者讀到有關「熱情者」(即忠誠、友好、樂於助人)的描述時,也會覺得室溫較高一些。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做個有溫度的人:溫度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行為、健康與人際關係的圖書 |
 |
做個有溫度的人:溫度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行為、健康與人際關係 作者:漢斯.羅查.艾澤曼 /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07-05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39 |
二手中文書 |
$ 303 |
中文書 |
電子書 |
$ 322 |
心理學 |
$ 363 |
人際關係 |
$ 363 |
心理勵志 |
$ 363 |
普及科學 |
$ 391 |
社會人文 |
$ 405 |
心理學理論 |
$ 414 |
社會人文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做個有溫度的人:溫度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行為、健康與人際關係
但為何捧著溫暖的杯子會影響我們的情緒?
為何我們想到善良親愛的人就感到溫暖?
為何我們看見悲傷殘酷的事件會覺得心寒?
觸摸與溫度是強大的人類交流方式,
社交體溫有時甚至攸關生死,
我們是需要彼此的動物。
「本書搭配熱飲享用最佳,你讀了就會明白。」
——莉迪亞.丹維斯,《友誼》作者
我們都喜歡與溫暖親切的人交朋友,也會盡量遠離冷酷刻薄的人,但為什麼「熱情、溫暖、冷淡、冷冰冰」這些用來形容一個人的性格或態度的詞彙,都與「溫度」有關?
社會心理學家艾澤曼透過無數的科學研究證明,小至語言與習性,大至社會文化與人類歷史,溫度如何在無形之中影響我們的行為、人際關係與健康。這些關於體溫調節的精彩實例,及其對人類文明的重大影響,將讓我們看到自己身為生物與人類的本質。
▌社會心理學家艾澤曼在本書中將一一深入探討:
.手拿熱飲的人,會覺得他人較親切、好相處?
.在室溫較低的法庭裡,陪審團判的罪更重?
.提高體溫可以改善憂鬱症?
.低溫的天氣賣房子最容易成交?
.提高實體店鋪的溫度,消費者更容易買單?
★溫度會影響社交關係
研究證實,手拿一杯熱飲就足以讓我們覺得對方比較值得信賴且親近;實體溫度會影響人們對社交冷暖的觀感。
★社交關係也會影響溫度
根據研究,當我們覺得自己與他人有隔閡時,會覺得周遭溫度較低;他人是支持我們體溫調節能力的關鍵。
★「有溫度」的行銷
人們接觸到實體溫暖,就更有可能聯想到情感溫暖,引發正面反應。溫度較高會促使消費者購買更多,並提高評價。
★溫度能改善身心健康
有情感疾病的人對溫度有不同的感知,他們不見得能調節體溫。研究顯示,提高體溫可能有治療憂鬱症的療效,降低體溫則可能改善糖尿病。
★溫度讓個性大不同
比起在極端氣候地區成長的人,在氣候溫和的地區成長的人,較為正向隨和、情緒穩定,對於新體驗會保持開放心態。
對動物來說,除了呼吸以外,調節體溫是最基本的任務之一。就像擠在一起取暖的企鵝一樣,人類長期以來也依賴彼此以維持體溫;幾千年來,這種本能塑造了我們的生活與文化。
過去,溫度促進人類演化——直立行走、毛髮減少、大腦發育——現在,溫度仍持續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響我們的生活。研究顯示,寒冷的法庭使陪審團更容易將人定罪,低溫的天氣讓人更有可能買房。我們的身心連結也以另一種方式運作:想到友善親愛的人就感到窩心。了解體溫與溫度,有助於人際關係、工作,甚至是行銷與社群媒體上的發展。
艾澤曼在闡述溫度如何影響人類社會時,也探究一些引人入勝的新問題:為什麼提高體溫可能改善憂鬱症?體溫調節能讓人際關係更親密?即使相隔兩地亦如此嗎?本書將從冷暖的角度,帶領讀者展開一場迷人的溫度之旅。
有溫度的推薦
王道還/生物人類學者
林嘉俊/臺大醫院家醫科醫師
洪仲清/臨床心理師
海苔熊/心理學作家
黃貞祥/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
蔡宇哲/哇賽心理學創辦人兼總編輯
謝伯讓/臺灣大學心理系副教授
(以上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國際讚譽
「漢斯.羅查.艾澤曼以溫度計測量人類與動物的行為,以顯示內外溫度對體溫的影響程度。這是一種驚人的觀點,遠比你想像的更有啟發性。」
——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紐約時報》暢銷書《瑪瑪的最後擁抱》(Mama’s Last Hug)作者
「體溫調節是生理運作最明顯的面向之一,不然我們何必發明中央空調系統呢?不過,以『溫飽』來說,我們對『飽足』的重視總是多於『溫暖』,這本資訊豐富的好書將會讓你改觀。」
——安東尼歐.達馬吉歐(Antonio Damasio),《事物的奇怪順序》(The Strange Order of Things)作者
「從擠在一起的企鵝,到生活在溫暖地帶的好處,本書帶領我們展開一場精彩的體溫之旅——我們如何控制它,它又如何控制我們。事實證明,體溫調節與你關心的幾乎所有事情都有關:你的健康、你的社交生活、你賣房子的能力。而且,這本書搭配熱飲享用最佳,你讀了就會明白。」
——莉迪亞.丹維斯(Lydia Denworth),《友誼》(Friendship)作者
「熱茶、中央暖氣系統、冰咖啡、依偎:由於古老的大腦迴路,物理上的溫暖和寒冷深深影響了我們思考與決策的方式,甚至是我們的愛。這本關於『社會體溫調節』的書將改善你的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解釋你與朋友視訊通話時的隱藏訊息、你對家的懷念,以及你在舒適的咖啡館裡度過的時光。這本書包含了硬科學、原創想法、動物的故事,以及發人深省的見解。實在太迷人了!」
——海倫.費雪(Helen Fisher),《我們為什麼愛》(Why We Love)作者
作者簡介:
漢斯.羅查.艾澤曼(Hans Rocha IJzerman)
格勒諾布爾大學(Université Grenoble Alpes)的社會心理學副教授,人類社交體溫調節方面的頂尖專家。其文章散見於《紐約時報》與《哈芬登郵報》。現居法國。
譯者簡介:
洪慧芳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管理碩士,曾任職於西門子電訊及花旗銀行,現為專職譯者,從事書籍、雜誌、電腦與遊戲軟體的翻譯工作。近期譯作有《加密貨幣之王》、《以太奇襲》、《吃佛》等。
Blog:cindytranslate.blogspot.tw
章節試閱
第一章 熱飲、電熱毯與孤獨──溫度與人際關係
謝爾頓走進自家公寓的客廳,看到好友李奧納德與霍華德窩在那裡,現場氣氛緊繃。
「怎麼了?」他問道。
「霍華德今晚要睡這裡,他跟老媽吵架。」李奧納德解釋。
「你幫他倒一杯熱飲了嗎?」
李奧納德一臉不解地瞪著謝爾頓看,霍華德則是癱坐在沙發上,不發一語。
「李奧納德!這是社交禮儀,朋友鬱卒時,你應該幫他倒杯熱飲,比如熱茶之類的。」
「來杯茶確實不錯。」霍華德坦言。
謝爾頓是美劇《宅男行不行》(The Big Bang Theory)的主角之一,網路迷因「以熱飲安撫朋友」可能...
謝爾頓走進自家公寓的客廳,看到好友李奧納德與霍華德窩在那裡,現場氣氛緊繃。
「怎麼了?」他問道。
「霍華德今晚要睡這裡,他跟老媽吵架。」李奧納德解釋。
「你幫他倒一杯熱飲了嗎?」
李奧納德一臉不解地瞪著謝爾頓看,霍華德則是癱坐在沙發上,不發一語。
「李奧納德!這是社交禮儀,朋友鬱卒時,你應該幫他倒杯熱飲,比如熱茶之類的。」
「來杯茶確實不錯。」霍華德坦言。
謝爾頓是美劇《宅男行不行》(The Big Bang Theory)的主角之一,網路迷因「以熱飲安撫朋友」可能...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章 熱飲、電熱毯與孤獨──溫度與人際關係
第二章 人類機器──溫度與體現認知
第三章 企鵝哈利──動物如何因應溫度
第四章 人也是企鵝──體內恆溫器的運作原理
第五章 鼠媽火辣辣──溫度與依附
第六章 不是單靠下視丘──文化如何改變社交體溫調節
第七章 為什麼你該在冷天賣房──溫度對行銷的影響
第八章 從憂鬱症到癌症──溫度療法
第九章 快樂的哥斯大黎加人──溫度、氣候與幸福
後記
謝辭
注釋
第二章 人類機器──溫度與體現認知
第三章 企鵝哈利──動物如何因應溫度
第四章 人也是企鵝──體內恆溫器的運作原理
第五章 鼠媽火辣辣──溫度與依附
第六章 不是單靠下視丘──文化如何改變社交體溫調節
第七章 為什麼你該在冷天賣房──溫度對行銷的影響
第八章 從憂鬱症到癌症──溫度療法
第九章 快樂的哥斯大黎加人──溫度、氣候與幸福
後記
謝辭
注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