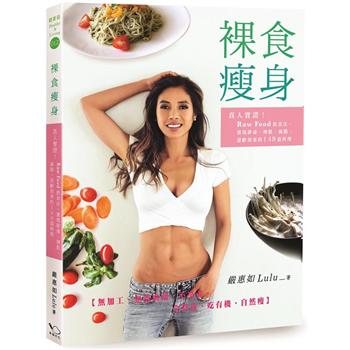前言
在書寫前現代中國的男同性戀史時,無疑地不存在資料匱乏的問題。事實上,從戰國時期(西元前四八一至二二一年)一直到二十世紀初的帝國晚期,關於這個主題的文獻資料卷帙浩繁。當然,可獲得的材料類型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書寫成何種類型的歷史。例如,我們有關前帝國時期和帝國初期的絕大多數文獻材料都來自官方正史,它們在本質上具有政治色彩,而且主要涉及宮廷貴族的生活。十三世紀之後,這種情況明顯發生了改變,我們開始獲得文類更加廣泛的作品,它們呈現出各個社會階層的生活,其中最劇烈的變化發生在十六世紀,這主要是由於書籍出版業前所未有的發展,以及尤其是通俗小說的興起。這種有利的環境解釋了為什麼這項關於中國同性戀的研究聚焦於帝國晚期——其時間範圍大致是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最後一個世紀和整個清朝(一六四四—一九一一),並主要依據小說類資料來源。具體而言,本書探討在大致跨越三百年時間的小說作品裡——從出版於一五五○年的《水滸傳》到一八四九年的《品花寶鑑》——呈現出來的同性戀與男性氣質和情愛的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
但是,在進入按年代論述的核心部分的研究之前,先讓我們考察一下中華帝國之前和帝國早期最知名的同性戀文獻,即使在帝國晚期,我們仍然能夠發現其中的某些術語和觀念。將中國性文化進行歷史化的進程最近才出現,當然,我不是主張漢代(西元前二○六年至西元二二○年)的同性戀修辭可以不假思索地運用於一千五百多年後的晚明文化。然而,在這些古文獻裡,已經可以發現帝國晚期關於男性之間性和愛情話語的某些重要特徵;兩千多年來,有關同性戀的古文學詞彙的連續使用證明,在前現代中國看待男男關係的某些基本方式具有很強的適應力。在歷史記載和哲理故事中,我們可以找到這些根本性觀念早期的結晶形式,它們形成了同性戀關係的「典故」,其發人深省的力量仍然存在於現代語言裡。從最早的文獻來源中,它產生的基本假設之一是:少年的男色堪比女色,並且它成為男性慾望之自然的和合法的目標。這一自明之理在政治上產生的必然結果是:對君主和國家而言,男寵與愛妃同樣是危險的。君主的男色之好,如同對女色之好一樣,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素,他可能因此變得墮落,不知不覺地陷於狂熱的痴迷,從此不理朝政。這種評價從根本上影響了史學家司馬遷(西元前一四五年至西元前八五年)的立場,他在《史記》裡描述漢代皇帝的男寵之好時,專闢〈佞幸傳〉。司馬遷的後繼者班固(三二—九二)在《漢書》中同樣有〈佞幸傳〉,裡面記載了「斷袖」的故事,直到如今,源自於它的「斷袖」這一文學表達,仍然能夠令人聯想到男同性戀關係。據說,漢哀帝(西元前二五年至西元前一年)極為迷戀寵臣董賢,有一天,為了不吵醒正靠在他袖子上睡覺的董賢,漢哀帝割斷了自己長袍的袖子。這兩位史學家都指責君王痴迷於「佞幸」,而這些佞幸無甚才能,徒有招人喜歡的外表——諸如年輕的鄧通,他被授權開礦造幣,因而富甲一方;或韓嫣,因為喜歡玩彈弓,專門為他提供金彈丸。男寵的嫵媚是危險的,統治者應清醒地意識到,他們是猶如西施那樣的「紅顏禍水」,最終將導致「傾國」。更為甚者,這些得寵者可能懷著險惡的野心,他們潛入女人的閨房、進入她們的身體——就在她們合法男人的眼皮子底下。在明清小說裡,這種威脅成為名副其實的隱喻(它涉及任何男性精英的家庭,而不唯獨是王室),這種現象是如此之多,以至於在十七世紀的小說集《情史》裡,關於男性愛情的那一卷將此類少年歸入「情穢類」的標題下。
在古文獻裡,除了對同性戀關係和男色象徵的威脅進行政治上的勸誡,我們還可以發現對男寵一定程度的同情,甚至有一種處於萌芽狀態的關於男性浪漫關係的話語。關於前者的例子是,西元前四世紀的哲學著作《韓非子》裡有一則故事,它產生了男同性戀關係的另一個典故:「分桃」。據說,衛靈公的寵臣彌子瑕有一天吃到了特別香甜的桃子,他將這個咬了一口的桃子給衛靈公吃,後者大為感動。但是,後來當彌子瑕美色衰退時,卻因此事而受責備。這個典故強調的是慾望的易變以及男寵身分的易逝和不穩定。一旦他們的青春容顏消逝,便被以前曾為之痴迷的庇護者拋棄。以前,無論少年做什麼事情都是稱心合意的,甚至違反禮儀規範都可以容忍,而如今卻成為君主惱怒的原因,以致令少年遭受懲罰。在這裡,男寵表現為無權無勢的、令人憐憫的——他們的困境旨在激起多愁善感的讀者同情,在歷史上,這些軼事確實具有這樣的功能。然而,西元前三世紀的《戰國策》裡有另一則經典的故事,它記載了魏王的寵臣龍陽君(因此,「龍陽」通常用來指代一個男人的男性愛人,後來甚至指男妓)。龍陽君與魏王一起外出釣魚,每次當魏王釣到更大的魚時,他就把原先釣到的小魚扔掉。突然,龍陽君意識到,魏王有一天也會這樣對待他,這一想法不禁令他潸然淚下。但是,魏王的安慰使他消除了擔憂,魏王以一種威脅性的形式宣告全國:「有敢言美人者族!」這個故事表明,男寵猶如被反覆無常的垂釣者釣到的魚,他會無情無義地繼續垂釣,一心想釣到更大的魚,然後丟棄之前成為獵物的小魚。應該注意的一點是,魏王指男寵的競爭者時,用的是普遍性的稱呼「美人」,它顯然包含了男人和女人。這反過來也表明,男寵面臨著雙重競爭,使其特權地位岌岌可危。儘管魏王對龍陽君說了寬慰的話,但這則故事與之前的故事之間未必是矛盾的。畢竟,龍陽君尚年輕貌美,但被君王拋棄可能只是遲早的事情。然而,這個故事強調的無疑是男寵對君王的忠誠和君王對男寵特別的寵愛。
在早期同樣廣為人知的其他傳說故事裡,也存在類似的強調。例如,關於安陵君的故事便是如此,安陵君對楚共王極為忠誠,甚至要求死後與他埋葬在一起;還有關於鄂君的故事,它也發生在楚國,有一天晚上,鄂君無意中聽到有位船夫吟唱關於他的情歌,他聽了之後,將繡被輕輕地披在這位年輕人的肩上。一直到明清時期,這些關於男同性戀的典故不斷地出現在中文著述裡,從知識考古學的角度而言,它們表達的觀念成為後來所有視角的核心。
※
自十六世紀後半葉開始,印刷業的迅速發展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通俗小說興起成為帝國晚期最流行的文學體裁之一,從而前所未有地產生了關於性別模式和性風俗的大量描述,它們呈現出來的社會圖景比之前任何時期都更加廣博和複雜。
無論是小說還是其他類型的文獻,它們通常都表明,男同性戀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社會實踐。正如第一章將會詳細闡述的,在明清時期,規範性的同性戀關係是一種跨年齡和跨階級的現象。較年輕的伴侶通常是僕人或男妓(他們可能是歌妓或男旦)——也即法律上的「賤人」——而他的庇護人則是「良民」。原則上,他們關係性的性角色是固定的,在肛交行為中,少年是受,而他的愛人則是攻。小說通常反映出這種默認的社會性的性協議,但也會經常出現違反這種性協議的情況。也存在很多關於「良民」之間「非常規的」同性戀關係的描述,我們將在第二章看到,在這些同性戀關係裡,(性角色的)違犯行為通常是以愛情為基礎的。因此,儘管大多數文獻資料關注精英男性寵愛階級地位低下的少年,但是我們不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即認為男同性戀現象被精英排他性地壟斷,就像有些學者對晚明的男妓之風以及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對帝國晚期伶人的恩客作出的評論那樣。顯然,我們應該承認這些顯著的現象,但同時不應該忽略參與同性戀實踐的其他社會行動者和類型。也就是說,就歷史化的意圖而言,必須承認小說作為文獻來源確實有其局限性。它們傾向於描繪文人雅客的生活,即使當我們碰到關於底層的社會性文化的表徵形式時,可以肯定的是,這些表徵形式的描述仍然受參與文學活動的仕紳階層的價值觀影響。因此,為了更加精確地描繪中華帝國晚期底層群體的同性戀狀況,借助於一些法律案件可能更加有幫助,儘管我們也無法忽略嵌入在司法敘述中的修辭滲透。蘇成捷(Matthew Sommer)探討了明代中後期以來與同性戀有關的犯罪案例,他的研究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即隨著勞動力遷移的趨勢,必然會增加這一時期社會地位低下的男同性戀關係的活躍度。喬治•昌西(George Chauncey)和馬特•霍爾布魯克(Matt Houlbrook)分別研究了二十世紀之交的紐約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倫敦的同性戀現象,他們令人信服地表明,與不同社會階級相對應的是極為不同的性制度。研究性態(sexuality)的歷史學家無疑需要更多地關注階級差異;我們可以預見,對於我們所關注的中國而言,這種努力也將會產生越加精細化的描述。
※
在明清小說作品裡,男同性戀是熱門的話題,它同時被呈現為性慾望和浪漫愛情。例如,在晚明的情色文學裡,我們可以發現三部專門描寫同性戀的作品。除了專門的作品之外,晚明以及之後的(大多是異性戀)豔情小說並不乏關於男同性戀的內容,而且該主題同樣經常出現在其他類型的小說裡。文學領域對描述男男關係的興趣也受到男妓行業的影響,該行業始終明顯存在著。男性的性消遣通常與戲院和男旦相關,這在整個晚期帝國時代的都市中心頗為盛行。關於晚明的男妓之風已有大量的文獻記載,最近吳存存和郭安瑞(Andrea Goldman)的研究表明,作為帝國晚期的社會現象,對戲子的狂熱事實上可能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與京劇的興起同時達到鼎峰。大體而言,帝國晚期的小說主要表達了這樣一種觀念,即欣賞男色被認為是審美和性趣味高雅的標誌。晚明關於優伶的品鑑話語便屬此種情況,例如,它出現於十六世紀末的名著《金瓶梅詞話》以及本書探討的最晚近的文獻資料,即十九世紀中期的小說《品花寶鑑》,其社會背景是愛好男旦的達官名士迎合歷史悠久的文學傳統,醉心於男旦的美貌和才藝,即「花譜」。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十年裡,關於同性戀傳統觀念的抹除過程伴隨著戲院的逐步改革,戲院這種機構對美化男色和男性愛情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情,包括男性之間的情,是明清小說的核心關注點,因此也成為本書的關注點。在晚明的哲學和文學文化裡,對感情的思考占據著重要的位置,並對此後的帝國晚期產生了形塑作用。因而,在這種話語背景下,不斷地出現關於男性愛情的敘述並不令人吃驚。正如我在第二章闡明的,晚明文化中流行的愛情觀念從根本上受男性之間關於俠的友誼模式影響。換句話說,根據意識形態的「考古」,男性情誼的平等主義式同性社交模式對於塑造普遍的愛情觀念——無論戀人的性別如何——起著重要的作用。男性之間的愛情被認為可以與男女之間的愛情相媲美,也即它可以作為愛情的一種獨特表現形式。在明清小說裡,雖然男性愛情有時被斥為荒誕的情感,或成為嘲諷的對象,但是它普遍享有受尊敬的地位,並且經常出現這樣的觀念,即愛少年說明男人的感情細膩而敏銳。即使我們對同性戀關係提出更為嚴厲的批評,如第四章探討的十八世紀的小說作品那樣,愛情也很少成為抨擊的目標。例如,在小說《姑妄言》裡,對男同性愛慾的同情與對風流浪子放蕩不羈(其中同性戀關係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尖銳批評是並存的。在作為最佳典範的愛情名著《紅樓夢》中,男性愛情也有著重要的地位,該小說出版於一七九二年,如本書第五章將探討的,它深刻地影響了十九世紀中期的男性愛情故事《品花寶鑑》。人們普遍認為,後者在文學上屬於「同性戀傳統」的一部分,該傳統可以追溯至晚明《弁而釵》之類的豔情小說。它們無疑是頗為不同的作品,其中主要的區別是以不同的方式對待情和性。在晚明的作品裡,情和性是和諧共存的;但在晚清的小說裡,情和愛之間出現徹底地、甚至是過度地分離,它從《紅樓夢》延續了這樣一種趨勢,即貶抑性結合,而讚美崇高的情感交流。然而,有一條線將這兩類同性愛慾作品聯結起來,這便是(多少有些色情化的)平等的愛情觀念,從根本上而言,它本身受俠的同性社交理念影響。因此,很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男性結交具有進步意義的去性化只是強化了它崇高的品質。從這種意義上而言,風流浪子拋棄異性戀的極樂世界,而與他的知己(和曾經的戀人)共同走向超脫之途——第三章探討的豔情小說正是以這種敘事為特徵——已經暗示著這種同性愛慾的崇高品質,對它的追尋正是《品花寶鑑》的核心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