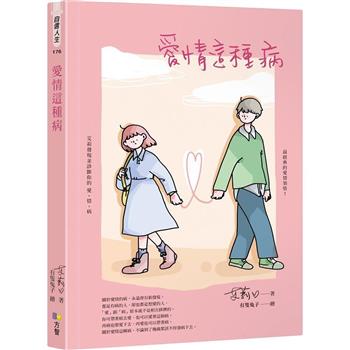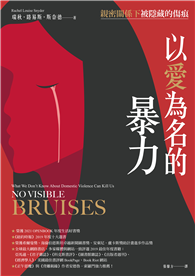古言女王桩桩繼《小女花不棄》、《蔓蔓青蘿》後又一部匠心之作──
無涯與穆瀾間的暗潮洶湧、似有若無的情愫,因不再隱瞞天子身分而蒙上陰影……
而國子監的監生生涯,在各方博弈之下,才正要開始。
◆◆◆
▏即將改編電視劇,蕩氣迴腸而又趣味橫生的治癒古言江湖劇!
▏作者桩桩獲封「百變故事女王」、「溫暖系言情掌門人」,作品《小女花不棄》、《蔓蔓青蘿》、《一怒成仙》皆改編影劇!
◆◆◆
國子監入學禮的凶案,震驚朝野上下。區區落第的舉子,怎會引來殺機?
靈光寺血案由錦衣五秀丁鈴主理,目擊行兇的蘇沐之死蹊蹺非常,故無涯再次派其來查審。穆瀾鬼才弟子的身分讓她備受矚目,她心細如髮,儘管探出花匠的異常卻不願居功,已知穆瀾祕密的林一川為了護她,主動承受眾人探詢的目光。
然凶手並未給予他們機會,毀容自盡以保幕後主使者。線索中斷,花匠這枚隱於國子監十年的棋子,不可能僅為蘇沐而設,其真實目的為何?
天子無涯於入學禮親自勉勵新監生,除培養己方人脈以對抗外戚與東廠,更是直接向穆瀾昭示自己的身分。兩人間的暗潮洶湧、似有若無的情愫,或許將蒙上陰影……
而國子監的監生生涯,在各方博弈之下,才正要開始。
/網友讚譽/
▪ 女主男主都很強大,互相算計的時候很帶感。
▪《珍瓏.無雙局》不輸《鳳求凰》,男主腹黑升級,超好看。
▪ 文筆讓人驚艷!裡面的人設到位,女主的權謀讓人佩服。
▪ 論甜寵不輸《月下蝶影》,論文筆權謀宅鬥更勝《尤四姐》。
▪ 第一遍看的是情節,第二遍更注意細節。文章裡最打動我的也是細節。所有的鋪墊和前景都在情節推動中娓娓道來。
作者簡介:
桩桩
畢業於中國新聞學院,從事多年記者編輯工作,多產作家,有「百變故事女王」之美譽,已累計出版十餘部暢銷作品。
代表作:《小女花不棄》、《一怒成仙》、《蔓蔓青蘿》、《珍瓏 無雙局》、《皇后出牆記》、《永夜》、《放棄你,下輩子吧》、《女人現實男人瘋狂》、《流年明媚.相思謀》等作品。
章節試閱
第三十章 花匠老岳
很多時候穆瀾都在暗暗提醒自己,離林一川遠一點兒。事實上,她卻和林一川走得越來越近。她的武功、她的武器,她和面具師父的那一戰都被林一川看在眼中。
如果不想暴露她的祕密,她應該殺了林一川。穆瀾心裡暗嘆,她下不了這個手。這樣的情形讓她不得不信任著林一川。
也許,如他所說,她真能多信任他一點兒。
「妳瞧。」林一川專心作畫,並未發現穆瀾眼中的掙扎與猶豫。
他畫了兩幅圖,栩栩如生。
一幅是他在靈光寺時追出去看到的凶手背影,前方是寺中碑林,凶手身穿黃色僧袍,戴了頂僧帽。黃衫飄蕩,身形應該比較魁梧;個頭據林一川所說,比他矮一點兒,比穆瀾高一點兒。
另一幅畫是靈光寺老嫗的廂房外,一個蒙面的黃衫人從門中躍出,手中拿著一柄匕首。紅梅樹下,蘇沐驚嚇在地。
他擱下畫筆,轉過臉來。穆瀾發呆時,眼神愣愣的,有點可愛。他笑著屈指朝她額頭彈去。
剎那間,穆瀾平平往右移動一步,躲開他的手指,眼神重新變得清亮。
林一川的手落了空,有點尷尬,更多的是好奇,「小穆,妳連發呆時都在防備,妳不累嗎?」
穆瀾愣了愣,淡淡說道:「習慣了。」
她才十六歲,得練多少年,才練成這樣的習慣?養成這樣的習慣是為了冒死進國子監嗎?
也許最初是穆瀾的性情吸引了他,也許是她的神祕吸引了他,但此時,林一川心裡浮現出淡淡的憐意。他真的很想保護她,想攏著她入懷,讓她能暫時放下所有的警戒與心防,在他懷裡歇息一會兒。
那雙比尋常人顏色更深的眸子噙著的情緒讓穆瀾蹙眉。林一川知曉自己太多祕密,好奇心太強了吧?他又在想她為什麼發呆?同時生出的還有一絲惱怒,「別以為知道我一些事,我沒殺你,就得寸進尺!」
小鐵公雞!小刺蝟!林一川暗暗惱恨自己又一次表白給了瞎子看,心裡暗罵著,臉上還得裝出一副誇張的表情,「我這不是關心妳嗎?」
「用不著。」穆瀾答了一句,提筆也畫出自己所見的林中凶手。
凶手一躍而起,提刀遮著面門。那柄刀很普通,握刀的手筋骨分明。
穆瀾回想著當時的情影,「他的手比較粗糙,膚色較黑。刀很普通,但很短,容易藏在身上。」
林一川想了想,慢慢地總結道:「他的年紀應該在三十到四十左右。身長七尺五寸左右。手粗因為習武,膚黑不似養尊處優之人。看體格,或許他留有濃密的鬍鬚。那麼早就能準確找到蘇沐,他是國子監裡的人,或許是近期才來到國子監。」
穆瀾的手在桌面上滑動著。那幾根淺淺的弧線究竟是什麼呢?她突然想到面具師父的面具。看到老頭兒的丹桂刺青之後,她才認出面具師父面具上刻的是一模一樣的丹桂花。
「也許他在靈光寺輕鬆殺死老嫗時,並未蒙面。聽到蘇沐賞梅的腳步聲後,一心想遮擋面目逃走。汗巾、帕子不正是隨身所帶之物嗎?於是他拿出自己的帕子或者是從老嫗的針線籃中拿了塊繡好的帕子蒙在臉上。這塊帕子上……」穆瀾看到了畫上的紅梅,肯定地說道:「蒙面的汗巾上繡著一朵梅花,蘇沐畫的弧線是梅花的花瓣!」
林一川眼睛亮了,「新監生報到,國子監或許會臨時招一批雜役進來幫忙。」
兩人幾乎異口同聲,「他可能是飯堂的雜役!」
穆瀾將桌上的畫紙捲好放進懷中,兩人興奮地跑出去。
丁鈴正翻動著名冊。
國子監臨時招進的雜役是他最懷疑的對象。
這批雜役分別去了四座飯堂和織衣局。
他先召齊了織衣局的雜役,挨著核對名冊,一一排除能讓他雙眼生疑的對象。緊接著,他先到了天擎院旁的飯堂。這裡離蘇沐遇害的地點最近,也許凶手看到蘇沐從飯堂離開,然後跟蹤了他。
飯堂來了八名雜役,丁鈴對照著名冊,詢問他們是由誰人所薦、家住何處這些瑣事。他認真看著他們的手,然而他沒有看出一個人有問題。他去了玄鶴院。這裡是蘇沐第一次上吊的地方,和天擎院的位置是對角線。
照丁鈴的想法,排除掉這兩間飯堂,再去地字院和黃字院附近的飯堂。
去的路上,丁鈴看到一名雜役正在掃地。他心中微動,招來國子監繩愆廳的官員,「不是說臨時來的雜役都安排在飯堂和織衣局嗎?」
這種雜務不歸繩愆廳管,旁邊跟隨的小吏翻看名冊,笑著答道:「入學禮前,臨時知曉御駕親臨,就抽了一些人負責清掃。」
丁鈴本能地回頭望向天擎院的方向。
林一川和穆瀾出了宿舍。入學禮後,新監生們得了半天假,正是開課前彼此熟悉結交同窗、向老監生打聽各種消息的時間,留在宿舍的人很少。
天擎院有獨立的浴堂,有一間燒熱水的小屋。兩名雜役正在整理柴垛。院子清幽美麗,比旁處多了幾名花匠。
一名花匠正拿著大剪刀,將春來新冒出頭的冬青枝葉修剪整齊。
剪刀發出的卡嚓聲極有韻律,枝葉分離間散發出一股淡淡的清香在空中瀰散開來。
也許是這排低矮的冬青樹讓穆瀾想起了樹林中凶手藏身的冬青,也許是這片苗圃旁邊就是蘇沐只住過兩晚的宿舍,穆瀾隨意看去一眼,發現這名花匠無論是身形和執剪刀的手都與林中的凶手極為相似。
花匠眼中只有這一片冒出頭的冬青樹,低著頭認真修剪。直到穆瀾的身影擋住他面前的陽光,他微微佝僂著身體,有點手足無措地望向穆瀾,不知道這名眉目如畫的監生有何事找上自己。
林一川莫名其妙地看著穆瀾走到花匠面前。
「大叔,你是新來的吧?」穆瀾的笑容很有感染力,燦爛得不染一絲塵埃。
花匠被她的笑容感染,露出了憨厚的笑容,「不是。小人在這裡幹了十年的活了,一直是天擎院的花匠。」
在國子監做了十年的花匠,不是新來的雜役。林一川放下戒心,以為穆瀾看走眼了,「小穆,走啦!」
「哦。」穆瀾答了聲,跟著林一川離開。
她走了十來步,伸手折下一根冬青樹枝,拿在手裡玩。
「小穆……」
林一川正想打趣她看走眼了,穆瀾手中的冬青樹枝已閃電般射出去,他吃驚地張開嘴。
那名花匠背對他們,手中的鐵剪繼續發出清脆的卡嚓聲。
樹枝掠起一縷風聲,如弩箭射出的箭矢,強勁有力。
穆瀾是在試探那個花匠。林一川腦中剛閃過這個念頭,就發現那根樹枝絲毫沒有減弱力道。如果她認錯了人,那名花匠一定會受重傷。
這兩個念頭剛閃過,那根冬青樹枝已經到了花匠背後,眼見就要刺進他的身體,林一川迅速地轉過身,警覺地看向院子。這時候,他心中只有一個想法,如果被人發現,自己該怎麼替穆瀾遮掩?
卡嚓!
一聲剪刀剪斷樹枝的聲音傳進林一川耳中,沒有意料中的痛呼聲,讓他很是吃驚地轉過身來。
那名花匠手執剪刀面對兩人,穆瀾射出的冬青樹枝斷成兩截落在他腳下,露出斷口新鮮的白茬。他佝僂的腰身挺直了,憨厚的眼神變得凶狠冷戾。
「今晨是你?」
穆瀾的笑容燦如春陽,那片陽光卻沒有染暖她的眼睛,清亮雙瞳像屋簷下的陰影,帶著幾分冷意。
花匠似有幾分不明白,打量了下自己。他穿著國子監發下來的雜役服,渾身上下實在沒有絲毫破綻。
如果能輕易被人看出破綻,他也不會在國子監裡做了十年的花匠。
「為何會懷疑我?」
看到花匠剪斷冬青樹枝的時候,林一川已經慢慢挪動步子,站在他的背後。林一川自詡目力過人,也實在沒想明白穆瀾為何會確定這個花匠就是殺害蘇沐的凶手。
花匠身後的監舍房門緊閉,門旁釘著寫有「甲三」的號牌。這間房原是林一川花五百兩銀換來的,再換給了蘇沐。天擎院的甲字號房間又比其他的房間更好,房門外低矮的冬青樹呈弧型圍成一個小小的庭院,就像是多出的私人庭院。
穆瀾緩緩開口道:「你剪得太過了。」
什麼叫剪得太過了?林一川看向那圈冬青樹,四下一對比,這才發現甲三號房間外面這圈冬青樹修剪得很整齊,唯有花匠所在處的冬青樹被剪得比旁處低了寸許。
「冬青樹開了春會生枝發芽,需要修剪才能保持原來的整齊美觀。我住在丁字號,房間外也有一片苗圃。出門的時候,我看到那片苗圃裡的冬青葉已經長得參差不齊。既然你在天擎院做了十年的老花匠,難道不應該先把這些冒頭的枝葉修剪整齊?然而你卻一直修剪著這裡早就修剪得平整的冬青樹。」
穆瀾慢慢地說道,分析著。
「你一直留在這裡,只有一個原因。雖然蘇沐的物品被國子監繩愆廳的官員拿走了,你卻不放心,還想進他的房間再搜一遍。早晨你完全可以趁著新監生參加入學禮進去搜。但你做了十年花匠,你不著急,想穩一穩、等一等。然而,皇上下旨,令錦衣衛查案,來的人卻是丁鈴。你害怕心細如髮的丁鈴會找到繩愆廳官員找不到的東西,你想趁丁鈴再來查看蘇沐房間之前,進去再搜一遍。」
「所以我一直站在這裡修剪著這片冬青樹,觀察著天擎院的情況,等待時機進屋。」花匠嘆了口氣,微瞇著眼望著溫暖的陽光,喃喃說道:「這樣美好的春天,你二位為何不去踏春遊覽國子監的風景,卻來看一個老花匠修剪樹枝?」
那個「枝」字從他嘴裡說出的瞬間,粗大的鐵剪發出卡嚓一聲,冬青樹被剪下一片寸許長短的枝葉。他隨手拂過,細碎的枝葉朝空中散開,像漫天灑落的暗器朝著穆瀾飛射而去。他腳步一頓,地上的泥土濺起一些細小的塵煙,面對著穆瀾,人朝身後躍出去。
一道掌風朝他襲來,林一川出手了。
花匠感覺到掌風的凌厲,心往下沉了沉。他之所以面對穆瀾,是想盯著她出手。在他看來,兩個少年中最大的威脅是穆瀾,站在身後的少年並不足為懼。然而他沒想到林一川的功夫並不弱,他凌空翻動身體,手中的鐵剪當成了棍子,揮向林一川。
這一掌延遲他逃跑的時間,當他的腳踩在地面的瞬間時,瞳孔猛的收縮了下。穆瀾像是一柄劍,破開面前飛至的樹枝花葉,已到了他的身邊。一簇銀光從她手中吐放,花匠明白了,這是早晨射向自己的那柄匕首。
鐵剪在他手中張開,不偏不斜夾住穆瀾刺來的匕首。這一次,沒有剪斷匕首的卡嚓聲傳來。他用力揮動鐵剪,又一次判斷錯了。穆瀾鬆開手,身體如春天飄蕩的柳絮,藉著他一甩之力蕩向空中,然後輕巧翻轉,手中竟又多出一柄匕首,身體從上往下朝他刺來。
這時,林一川的雙腿已踢向他的下盤。
如果他攻向林一川,就避不開穆瀾;避開穆瀾,他勢必被林一川踢中。花匠冷笑了聲,鐵剪當成暗器扔向林一川,手從衣襟下抽出一把刀迎上穆瀾的匕首。
兩個聲音幾乎同時發出。「咚」的一聲,是林一川躲開的鐵剪掉在地上發出的。花匠的刀與穆瀾的匕首在空中相擊數下,叮噹聲不絕。
花匠無心戀戰,邊打邊退。兩人都想生擒,只纏不攻,拖延著時間。花匠每下殺手,就發現兩人躲得比兔子還快;收手逃跑,穆瀾的輕功勝他一籌,纏著他不放。林一川又奔過來加入圍攻,花匠漸漸焦躁起來。
很快的,這邊的打鬥就會傳開,然後丁鈴會來……思索中,他腳下微涼,竟踩進了天擎院的湖水中。
刀順勢貼著水面一掠,銀色的水花疾射而出。穆瀾和林一川配合默契,往旁閃開。嗤嗤數聲,水花灑落在岸上,溼潤的泥地上出現一片密集的凹坑。
林一川撇嘴道:「湖裡的水多得很,你往裡面跳唄!」
花匠果然縱身躍向湖水。
「真賤!叫你跳就跳啊!」林一川罵了句,自問沒有這種踏萍渡水的輕身功夫,但他相信穆瀾有,「小穆,妳追他,我去對岸攔他!」
花匠的身體在空中墜下的瞬間,他抽刀擊水,借力再躍。
穆瀾卻停住腳步。
「小穆?」林一川不明白。
「我聽到了鈴鐺聲。」既然丁鈴已經趕來,她為何要暴露自己的實力?
她的話音剛落,清脆的鈴鐺聲在湖面響起。丁鈴的身法太快,紅色的斗牛服像是落在湖面上的一縷晚霞,飄逸無比。鈴聲停住,他落在湖對岸,擋住花匠的去路。
花匠沉默地看著丁鈴,準確說,是盯著他手中的金鈴。
「你逃不掉了。」
「束手就擒吧!」
丁鈴悠然地望著他說了這兩句話。
隔岸湖邊,林一川和穆瀾見丁鈴擋住花匠的去路,同時鬆了口氣。
林一川這時才有時間誇穆瀾,「小穆,妳真厲害,這麼快就發現了殺蘇沐的凶手。當時我都嚇了一跳,生怕妳傷錯了人。」
穆瀾笑道:「那我真認錯人怎麼辦?」
林一川輕鬆地說道:「我給他很多銀子,向他賠禮便是。」
一個窮苦的花匠,被莫名其妙的樹枝刺傷,因此得到大筆銀錢養傷,應該會很高興。
「我胡亂傷了無辜,你還會喜歡我這樣的性子?」穆瀾想起林一川說過的話,疑心漸起。
「哎,小穆妳哪會隨便傷人呢?」林一川有苦說不出,又不敢讓穆瀾知道自己早就曉得她的性別,只好睜著眼睛說瞎話,「妳看,妳一試,他就露出原形了。」
等於沒有回答。望著林一川英俊的側臉,穆瀾心裡的感覺怪怪的。
湖岸對面刀光閃爍,打斷了穆瀾的思索。
花匠揮起了刀,丁鈴擲出了手中的金鈴。
刀光中鮮血四濺,鈴聲「叮」了一聲後沉默了。
花匠的身體倒向後面的湖水,濺起一大片水花。水聲之後,暗紅的血暈開,染紅了這片湖水。一雙金鈴牢牢地挨在一起,細長而韌的銀索緊緊纏住他的雙腿。
花匠一共揮出三刀,前兩刀削掉了自己的臉頰,第三刀割斷自己的咽喉。他睜大著雙眼嘲笑地望向天空,似在譏諷丁鈴也有判斷失誤的時候。
他根本沒有想過能從丁鈴手中逃走,他選擇了毀容自盡。
「我日哦!」丁鈴氣得直跳腳。
他想抓活口,所以沒理會花匠出刀,他對自己的金鈴有信心;然而花匠的刀不是砍向他,而是砍向自己。
兩案並查,凶手就在眼前,卻自盡了,而且是當著他的面自盡。丁鈴像生吞了隻蒼蠅一樣難受。
這時聽到動靜趕來的人越來越多。已有住在天擎院的老監生認出了花匠來,「這不是咱們院裡的花匠老岳嗎?」
「是啊,我在國子監快四年了,從來不知道老岳會武藝。」
原來他是天擎院的花匠,怪不得能盯死蘇沐的行蹤,一大早殺了他。丁鈴恨恨地盯著湖裡的花匠,又笑了起來。
「其實你已經告訴我很多東西了。一,你在國子監十年,蘇沐一定不會是你的目標。二,本官已經見過你的臉了。你執意毀容,是不想讓人因為你的臉去指認你的主子,那麼你應該不是個默默無聞的人。本官一定會查出你的祖宗三代!最後,甭以為你自盡了,本官就會結案。你給我等著!」
丁鈴說這一長段話時,只是動了動嘴皮,沒有人聽到他的聲音。可是他的表情極其豐富,一會兒自信地笑,一會兒咬著腮幫子瞪眼。跑到湖對岸的林一川見著,笑個不停。
「很好笑嗎?」丁鈴突然回過頭,指著林一川道:「說的就是你!你怎麼發現他的?」
怎麼搶在本官找出他之前,發現他的?
林一川下意識回頭,卻發現穆瀾沒有跟過來。她不想在丁鈴面前露面?無涯看起來和錦衣衛走得近,穆瀾如果被丁鈴盯上,弄不好,無涯會知道她是女子。這樣一想,林一川理所當然地把發現花匠是凶手的「功勞」扛到自己身上。
他繪聲繪色地將自己如何發現花匠站在蘇沐宿舍門口修剪冬青樹的不對勁,然後出手試探,「……出手一試,他就逃了,我趕緊叫上小穆一起追。才追到湖邊,眼看著他躍湖要逃,幸虧大人及時趕到!大人英明!」
「穆瀾呢?」丁鈴習慣性地想聽兩人的說法,看到穆瀾還遠遠站在湖對岸,又氣不打一處來。錦衣衛想招攬,穆瀾卻有多遠躲多遠。當錦衣衛少了她不行?丁鈴哼了聲。
見他望向對岸的穆瀾,林一川大步上前,擋住他的視線,奉承道:「大人怎麼查出這個花匠有問題?他在國子監待了十年呢,不是新招的雜役。」
丁鈴是想回天擎院查一查那幾個臨時抽去掃地的雜役,聽到動靜後趕來的。他臉也不紅地說道:「本官焉能不知道?」
國子監繩愆廳官員和小吏們也趕到了。
丁鈴惱火地對國子監的小吏說道:「還不趕緊把凶手撈起來!」
小吏們將面目全非的花匠從水裡拖出來。丁鈴親手解下那雙金鈴繫回腰間,親自查驗了花匠的屍身,擺手讓人抬走了。
繩愆廳的官員已經從旁處知道這名花匠的身分。一個在國子監幹了十年花匠的人,在錦衣衛的大刑下能說出多少國子監的陰私事?看到花匠的臉血肉模糊,頸邊一道深深的刀痕,死得不能再死,官員們心中鬆了口氣,討好地對丁鈴說道:「丁大人名不虛傳,這才半天工夫就抓到了凶手……」
馬屁自然拍到了馬腿上。丁鈴冷冷地望著他們道:「他在國子監裡隱藏了十年,繩愆廳吃白飯的?都沒發現他身分可疑?」
一句話將繩愆廳的官員氣得臉都綠了。監生數千、官員數百,誰犯了案,難不成就責怪繩愆廳失察失職?
丁鈴慢悠悠地朝北拱手道:「皇上英明,所以令本官親自來調查此案啊。」
他臉上的神情太過自戀,官員們硬著頭皮繼續恭維,「有丁大人接手,這案子才能破得這麼快、這麼輕鬆……」
見官員們的臉色也像是生吞了蒼蠅般難受,丁鈴氣消一半,讓林一川帶路去蘇沐的房間。
「丁大人,蘇沐的行李、物品我們已經搬去了繩愆廳。」一名官員覺得多此一舉。
丁鈴又朝北拱手嘆道:「皇上之所以令本官徹查此案,就是知道本官能看出你們看不見的線索啊!」
這句話噎得繩愆廳上下等人半晌無語,訕訕應道:「皇上聖明!」
林一川險些憋成內傷,他強忍著笑在前面領路,心想見過的兩個東廠飛鷹大檔頭,朴銀鷹威風嚴肅,梁信鷗笑裡藏刀。從前他覺得神祕的錦衣五秀應該是與之匹配的人物,今天才知道,被六扇門視為神捕的心秀丁鈴其實就是個自戀毒舌的活寶。
丁鈴的聲音突然出現,「花匠是穆瀾發現的是吧?」
還挺賊的!林一川反應極快,「丁大人可不能信口開河抹了學生的功勞!」
丁鈴背負著手往前走,鈴鐺叮叮噹噹響個不停,「除非你幫我找到點兒有用的東西,我才相信。」
小綠豆眼精明地在林一川臉上打了個轉,心想這是個人才,不用白不用。
林一川愣了愣,看到湖邊的穆瀾已經消失無蹤,不由得暗罵,小鐵公雞太沒義氣了!誰教他捨不得她有事呢?林一川嘆了口氣,無奈地帶著丁鈴去了蘇沐的宿舍。
第三十章 花匠老岳
很多時候穆瀾都在暗暗提醒自己,離林一川遠一點兒。事實上,她卻和林一川走得越來越近。她的武功、她的武器,她和面具師父的那一戰都被林一川看在眼中。
如果不想暴露她的祕密,她應該殺了林一川。穆瀾心裡暗嘆,她下不了這個手。這樣的情形讓她不得不信任著林一川。
也許,如他所說,她真能多信任他一點兒。
「妳瞧。」林一川專心作畫,並未發現穆瀾眼中的掙扎與猶豫。
他畫了兩幅圖,栩栩如生。
一幅是他在靈光寺時追出去看到的凶手背影,前方是寺中碑林,凶手身穿黃色僧袍,戴了頂僧帽。黃衫飄蕩,身形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