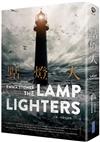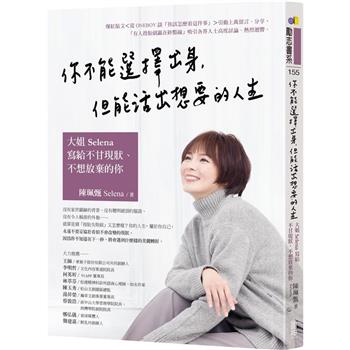☆☆☆
「懸疑」、「驚悚」、「推理」、「燒腦」、「反轉」、「改編自真實事件」……
【SP SELECT系列】的關鍵字,也是你閱讀時的關鍵字嗎?
由熱愛歐美驚悚類型懸疑小說的編輯精心挑選,從真實懸案啟發到影視改編作品,囊括歐美各國暢銷排行榜常勝軍,SP SELECT系列將帶給你全新的歐美懸疑閱讀體驗!
☆☆☆
★震驚全球歷史懸案改編,至今未解的世紀之謎!
★售出全球25國版權,打進英國《泰晤士報》暢銷榜前五名!
★空降美國邦諾書店排行榜冠軍、強勢登陸德國《明鏡》排行榜!
★布克獎得主《狼廳》作者希拉蕊・曼特爾:「今年讀過最喜歡的一本小說!」
★《別相信任何人》作者S.J. 華森盛讚:「從頭到尾愛不忍釋,實在棒透了!」
他們說,遺失在海上的靈魂將永遠失落。
他們說,
海,會保守它深不可測的祕密──
【▼以下皆為真實事件▼】
一九○○年,蘇格蘭外海的弗蘭南群島發生了一起離奇事件:
三名燈塔看守員神祕消失,至今下落不明。
弗蘭南島雖然地處偏遠,但位於重要的商業航線上,
因此島上的燈塔配置了三個看守員,指引航道上來往的船隻。
該年十二月,一艘商船發現燈塔一片漆黑,船長遂登陸調查,
卻發現燈塔從內部反鎖,
破門而入後,三人無影無蹤。
看守員遺留下來的日誌上記載:
「十二月十二日起暴風雨來襲,其勢猛烈,堪稱前所未見;
暴風肆虐三天,直到十五日方才停歇。」
日誌也就停在十五日。
但是所有行經附近的船員都能作證,
十二日至十五日島上風平浪靜,
暴風雨是十七日才抵達。
三名看守員都經驗豐富,深知無論任何情況,
都必須要有人留守燈塔,不能同時離開。
被遺留在燈塔內的物件與擺設毫無邏輯,
看守員日誌的內容更是詭異無比,
即使經過百年,依然無人能提出合理解釋。
所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以上皆為真實事件▲】
在一個世紀後,
作家艾瑪‧史東尼克斯試圖以虛構之筆,
替全世界解開這場百年懸案!
▊「今年讀過最喜歡的一本小說!」──各家媒體與歐美作家齊聲盛讚!
「文筆優美、意味深長,集推理、愛情和鬼故事於一身,讓我從頭到尾愛不忍釋,實在棒透了。」──S.J.華森,著有《別相信任何人》
「今年讀過最喜歡的一本小說!」──希拉蕊・曼特爾,著有《狼廳》
「了不起的作品……每一頁都與大海的黑暗、強大的存在產生共鳴。」──蕾諾‧溫,著有《鹽之路》
「這是一個透過生動的文字講述謎團、讓我從頭到尾全神貫注的完美作品。令人難以忘懷、令人痛徹心扉,也令人心碎,這是一部肯定會留在你身邊的小說。」──艾希莉‧歐娟,著有《在所有母親之間》
「《點燈人》是一本集推理、懸疑、靈異,以及集所有心理驚悚探祕於一身的驚人作品!」──《衛報》
「仇恨、不信任、謊言和一種始料未及的愛,將這些角色包裹在一部優美的小說裡,這部作品不只著重在學會放下和希望,它同樣著重謀殺和復仇。」──《衛報》
「一個令人久久無法釋懷的謎團,被史東尼克斯用絕美的文字給包裹住……大家現在只想立刻讀到下一本史東尼克斯的作品!」──《出版者週刊》,星級評論
「史東尼克斯巧妙地利用真實故事,引導讀者進入這個獨樹一格的作品──一系列詭譎且近乎神秘的謎團並列,使讀者牢牢抓住這本書不放。絕無僅有的閱讀體驗!」──《書單評論》
【故事大綱】
三名燈塔的管理員離奇失蹤,
資歷最深的亞瑟・布拉克,和他搭檔多年的比爾・沃克,
以及新加入的菜鳥文森・伯恩,
全在一夕之間音訊全無,彷彿人間蒸發。
在失蹤之謎仍未解的二十年後,
以一系列海戰冒險小說聞名的暢銷作家丹・夏普,
突然宣布自己打算挑戰非虛構的紀實文學,
以燈塔失蹤事件為題,並找上當年管理員的遺孀和女友。
亞瑟的妻子海倫早就接受了丈夫已死的事實,
也不在乎這背後到底有何隱情,
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
比爾的太太珍妮則拒絕相信丈夫已死,
堅信他只是下落不明,一直等待比爾再次出現的那一天。
文森的女友蜜雪兒如今已結婚成家,也有了孩子。
在丹試圖釐清真相的過程中,
他察覺神祕失蹤故事的背後,似乎有更多比大海更深的祕密……
作者簡介:
艾瑪‧史東尼克斯Emma Stonex
艾瑪‧史東尼克斯出生於英格蘭東部的北安普敦郡,熱愛燈塔與海岸線,曾任出版編輯,現為作家,著有《點燈人》。
目前她與丈夫以及兩個女兒住在英國布里斯托。
譯者簡介:
黃涓芳
畢業於臺灣大學外文系及語言所,曾任創意編輯、英語研究員等職。目前為英、日文自由譯者。
章節試閱
1
接班
朱利打開窗簾,看到灰濛濛的天已經亮了。收音機播放著似曾聽過的歌。他邊喝紅茶邊聽新聞報導:一個女孩在北方的公車站走失了,可憐的母親傷心欲絕──那是當然的。朱利在腦中想像那個女孩的模樣:短髮,短裙,有一雙大眼睛,在冷風中發抖。他也想像到空無一人的公車站 。先前應該有人在那裡,以溺水者般的動作招手;公車停下來又開走,沒有察覺到異狀,人行道在黑暗的雨中閃閃發光。
大海風平浪靜,呈現狂風暴雨之後特有的鏡面質感。朱利打開窗栓。新鮮空氣感覺幾乎像是可吃的固體,在海邊小屋之間發出叮噹聲,就如飲料中的冰塊般。沒有任何東西和海水的氣味一樣:鹹鹹的,很乾淨,令人聯想到放在冰箱裡的醋。今天的海沒有聲音。朱利看過狂風呼嘯的海與靜悄悄的海,驚濤駭浪的海與鏡子般的海;有時憤怒的大海會讓人感覺這艘船是人類僅存的依靠,甚至相信最荒誕的念頭,譬如大海是通往天堂或地獄的路徑,或是天上和深海潛藏著未知的怪物。曾經有個漁夫告訴他,大海有兩張面孔,你必需要了解它好的一面與壞的一面,千萬不能漠視任何一者。
經過漫長的等待之後,今天的大海總算有利於出航。他們今天就要去執行任務。
☆
朱利負責決定要不要出船。即使風勢在九點時處於穩定狀況,也不代表到了十點仍舊相同。而且不論港口此刻的狀況如何,到了燈塔周圍就會增強到十倍的程度。比方說假設港口的浪高四英尺,那麼他可以猜想到燈塔周圍會有四十英尺高的浪。
這次要送去的是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他有一頭金黃色的頭髮,戴著厚厚的眼鏡,讓他的眼睛看起來又小又侷促不安。這個年輕人讓朱利聯想到被關在籠子裡、住在木屑裡的動物。他站在棧橋上,燈芯絨喇叭褲的褲口被濺起的海水打濕,使顏色變深。清晨的碼頭很安靜,只有一個遛狗的人,以及正在卸下牛奶箱的人。這是介於聖誕節與新年之間、寒冷而短暫的閒暇。
朱利和他的手下的人把這名男孩的行李(特利登協會的紅色紙箱中,放了兩個月的衣服和食物、新鮮的肉、水果、不是奶粉的正常牛奶、報紙、一盒茶葉、GV香菸)拖過來,用繩索把它們運下去,然後用防水布覆蓋。燈塔上的管理員應該會很高興──他們在過去四個星期當中,只能吃很稀的濃湯,最新資訊也只有上一個接班者帶去的《每日郵報》首頁。
淺水區的水面漂浮著海藻,海水打在船身周圍。男孩爬上船,腳上的帆布鞋都濕了。他像個盲人般摸索著船身,一隻手臂夾著用繩子綁起的包裹,裡面放的是他的個人用品,包括書本、錄音機、卡帶等打發時間的東西。看來他很有可能是學生。特利登近年來雇用很多學生。他的興趣大概是寫曲子吧。他會在燈塔上想,這就是人生。燈塔管理員都需要找些事情來做,總不能把時間都打發在跑上跑下樓梯。朱利很久以前認識一個手工很巧的管理員,在值班期間製作瓶中船,而且做得很漂亮;後來燈塔上裝了電視,這名管理員就拋棄這項興趣,而且名副其實地把工作道具從窗戶拋到海裡,從此之後空閒時間都坐在電視機前看電視。
男孩問朱利:「你做這行很久了嗎?」朱利說:「是啊,比你活過的歲月還要久。」男孩又說:「我沒想到可以成行。我從星期二就一直在等。他們讓我寄宿在村子裡,雖然住得不錯,但是也沒有好到讓我想要繼續待下去。我每天都望著外面想: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出發?那場暴風雨真的很誇張。我真不知道如果又來一場暴風雨,在燈塔裡會是什麼樣子。他們告訴我,沒有從海上看過暴風雨,就不能算是真正看過暴風雨。據說感覺就像整座燈塔即將從腳底崩塌,然後被海浪捲走。」
新來的人總是很多話。朱利認為這是因為緊張:他們擔心在渡海時遇到風向轉變,擔心靠岸是否安全,擔心燈塔上的其他成員是否容易相處,擔心自己是否能夠適應他們,擔心那裡的主任是什麼樣的人。那座燈塔還不屬於這個男孩,或許永遠不會屬於。臨時雇員來來去去,有時到陸地上的燈塔,有時到礁石上的燈塔,像彈珠台的彈珠一樣,在全國各地往返。朱利看過很多像這樣的年輕人,一開始非常熱情,對這份工作抱持著浪漫的想法,但這份工作並沒有他們想像的那麼浪漫。三個男人孤立在海上的燈塔,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就只有三個男人和無盡的海。要有一定的特質才能承受被關在燈塔裡,忍受寂寞、孤獨、單調。在方圓幾英里內,除了海水以外什麼都沒有;沒有朋友,也沒有女人,日以繼夜只看到另外兩個人,無法逃離他們。這種生活簡直會把人逼瘋。
等好幾天、甚至好幾個星期才等到輪班也是常見的事。朱利曾遇過一名管理員因為接班者失蹤,結果在燈塔待了四個月。
朱利對男孩說:「你會習慣天氣的。」
「希望可以。」
「而且你不會比那個準備要回陸地的可憐蟲更火大。」
他的水手聚集在船尾憂鬱地看著海面,邊發牢騷邊抽菸,濕濕的手指沾濕香菸。他們就像一幅陰沉的海景畫中的人物,以厚厚的油畫顏料和粗糙的筆觸勾勒。其中一人喊:「還在等什麼?難道要等潮水在出發前轉向嗎?」船上也載了要去修無線電的工程師。一般來說,在輪班的日子,他們應該和燈塔之間已經聯絡五次了,但是暴風雨使他們斷了音訊。
朱利把最後幾箱行李蓋起來,發動馬達,船便出發了。船身在海中搖晃起伏,就如漂浮在浴缸裡的玩具般。一群海鷗在遍布鳥蛤的岩石上爭執,一艘拖網漁船發出「突突」的引擎聲駛入港口。當海岸線消失,海面變得更加動盪,白色水花在綠色的浪峰濺起又消失。更遠處的顏色更深,海面變成卡其色,天空則是不祥的灰色。海水拍打著船首,海面上出現條狀泡沫後又擴散開來。朱利叼著在他的口袋被壓扁、但仍舊勉強能抽的捲菸,雙眼注視著海平線。他的雙耳在冷風中感到刺痛。在他的頭上,一隻白色的鳥在遼闊而無彩色的天空盤旋。
朱利可以看到霧中的處女岩燈塔,孤單的塔尖高聳在遠方。燈塔位於十五海里外。朱利知道管理員比較喜歡離岸邊遠一點,免得從燈塔看到陸地而想到家。
新來的男孩背對著燈塔。朱利心想,背對著自己即將前往之處,這樣的啟程滿可笑的。男孩擔心著大拇指的擦傷,表情顯得虛弱而病懨懨的,感覺很生澀,不過每個海員最終都得適應才行。
朱利問:「小伙子,你以前上過燈塔嗎?」
「我之前在特雷弗斯(Trevose)燈塔,接著又到聖凱瑟琳(St Catherine’s)燈塔。」
「可是你沒待過海上的燈塔吧?」
「從來沒有。」
「要待在海上燈塔,必須具備膽量才行,而且還要和其他人員相處,不管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喔,我可以適應。」
「那當然了。你的主任管理員是個好人,這點很重要。」
「其他人呢?」
「我聽說要小心那個兼職管理員。不過他跟你的年齡相仿,你們一定可以合得來。」
「他有什麼問題?」
朱利看到男孩的表情笑了,對他說:「你不需要那麼擔心。工作上有各種傳言,不過未必都是真的。」
風吹過海面,掀起陣陣波浪;海水在他們下方翻滾,黑暗的波濤拍打著船身;當浪花濺灑在船首,波浪便再度從深處湧起。朱利小時候從萊明敦搭船到雅茅斯時,會從甲板的欄杆往外看,注視著海水在不為人所知的地方悄悄展現如此驚人的景觀;大陸棚陡降而陸地消失,如果掉下去就會沉入好幾百英尺的深度;海中會有長嘴魚和星鯊,外型怪異、臃腫、閃亮的生物伸出柔軟的觸手,眼睛宛若白底藍紋大理石般。
燈塔越來越近,原本像一條線,接著變成直條狀,然後又變成手指的形狀。
「那就是處女岩燈塔。」
此時他們可以看到燈塔底部海水侵蝕的痕跡。那是長年以來的惡劣天候累積而成的傷痕。雖然朱利已經開船來過這裡無數次,但每次接近這座燈塔中的女王,總是會讓他產生特別的情感──感覺自己受到斥責、非常渺小、甚至懷著恐懼。這座燈塔建立於維多利亞時代,有五十公尺高,蒼白地聳立於海平線前方,作為保障海員安全的堅固堡壘。
朱利說:「它是最早完成的燈塔之一,建於一八九三年,在成功點燈之前曾經被摧毀過兩次。據說在狂風暴雨的時候,風吹過岩石之間,它就會發出好像女人在哭泣的聲音。」
燈塔的細節逐漸從灰濛濛的霧中顯現,可以看到塔上的窗戶、底下環狀的水泥平台、以及通往檢修門的狹窄鐵製階梯(通稱「狗階梯」)。
「他們看得到我們嗎?」
「現在可以。」
然而朱利在說話時,雙眼搜尋著他預期應該出現在燈塔底部的人物。藍色制服、白色鴨舌帽的燈塔主任管理員、或是助理管理員應該要在那裡揮手迎接他們才對。那些管理員應該從日出就在觀察海面。
朱利注視著燈塔底部的波浪,考慮最佳的作法:是要繼續前進還是後退,要拋下錨或是繼續航行。冰冷的海水盪過水底一連串的礁石。當海水上漲,這些礁石會消失,當海面下降,它們就會像黑色閃亮的臼齒般浮現。朱利認為在所有燈塔中,主教、野狼和處女是最難靠岸的;如果要從中再作選擇,他認為處女岩燈塔難度最高。在水手的傳說中,這座燈塔是建立在海中怪物化石的牙齒上。在建造它的過程中,死了好幾十個人,這裡的礁岩也害死了許多迷途的水手。這座燈塔不喜歡外來者,也不歡迎訪客。
不過朱利仍舊在等待管理員出現。除非有人在靠岸設備的另一邊,否則他們沒辦法讓這個年輕小伙子下船。此刻的海水起伏相當劇烈,他會一下子往下掉十英尺、一下子升高十英尺;一個不注意,繩索可能被扯斷,害他掉入冰冷的水中。
這是很驚險的工作,不過海中的燈塔就是這樣。對習於陸地的人來說,會以為大海好像很穩定,但朱利知道大海並不穩定,而是反覆無常、無法預期的。如果不提防,就會被它吞沒。
「他們在哪裡?」
朱利在海浪的聲音中,幾乎無法聽見他身旁的人在喊什麼。
朱利示意手下繞行燈塔。年輕小伙子和工程師的臉色都變得蒼白。朱利必須安撫他們,但他自己也感到不安。在他開船到處女岩的這麼多年來,他從來沒有繞到燈塔的後方。
完全以花崗岩建造的燈塔高聳在他們前方。朱利探頭看入口處。這道緊閉的門高出海面六十英尺,以青銅打造。
船員高喊管理員的名字,並吹出尖銳的口哨聲。在更高處,燈塔逐漸變細並往天空延伸,而天空則俯視著他們的小船迷惘地轉向。跟著他們飛到海上的那隻鳥再度飛來,不斷盤旋,叫著他們聽不懂的訊息。男孩靠在船側,手中的早餐掉落到海裡。
他們坐在上下起伏的船上,一直等待。
朱利抬頭仰望燈塔,駛出它的陰影,耳中只聽見海浪沖刷在岩石之間的聲音,腦中想的是他今天早上在廣播中聽到的那個女孩,還有空無一人的公車站,以及毫不歇止的大雨。
2
燈塔奇聞
《泰晤士報》,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特利登協會得知該協會有三名管理員從處女岩燈塔失蹤。該燈塔位於距英格蘭東南端十五英里的海上。三名失蹤男子為:主任管理員亞瑟・布拉克、助理管理員威廉・比爾・沃克,以及兼職助理管理員文森・伯恩。發現三人失蹤的是當地船夫及其船員。他們在昨天早上原本要送接班的管理員到燈塔,並把沃克先生接回岸上。
目前失蹤者仍舊行蹤不明,協會也還沒有正式聲明。調查行動已經展開。
3
九層樓
靠岸過程花了好幾個小時。十幾個男人爬上「狗階梯」,舌頭上感覺到鹽巴與恐懼混合的滋味,耳朵和雙手也都凍僵了。
他們到達燈塔的門,發現門是從裡面鎖上的。這道鐵門是為了承受海浪與颶風而建造的,此刻則必須用臂力與棍棒破壞。
後來其中一人出現不斷發抖、臉色蒼白的症狀;部分理由是因為精疲力竭,部分理由則是在朱利的接班船沒有接到人、特利登協會叫這批人「去看看」之後,他心中一直有不祥的預感。
他們當中的三人進入燈塔。裡面很暗,有種發霉的生活氣味。這是海上燈塔在窗戶緊閉狀態很典型的氣味。倉庫裡沒有太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在黑暗中只看到龐大的物體輪廓,幾捆繩子、救生圈、以及上下顛倒懸掛的小艇等,沒有任何東西被動過。
管理員掛在這裡的雨衣在黑暗中看起來就像上鉤的魚。搜尋者朝著天花板上的檢查井呼喚管理員的名字,聲音沿著階梯往上迴旋。
亞瑟!比爾!文森!文森,你在那裡嗎?比爾?
他們的喊聲劃過寂靜的塔內,顯得格外詭異。在凝重的寂靜中,他們的聲音大到感覺不敬。他們並不期待有人回答。特利登告訴他們這是一場搜救行動,但他們的任務是要找到屍體。門是鎖上的,燈塔管理員逃亡的可能性已經消失。那些管理員一定在燈塔內的某個地方。
特利登協會交代過,要悄悄地把他們帶回來。過程要謹慎,找到能夠守密的船夫,不要大肆張揚,不要引起糾紛,不要讓任何人知道,另外也要確保燈塔沒問題──看在老天爺的份上,一定要有人去確認這一點。
三人一個接著一個爬上去。上面這一層的牆上排列著起爆劑和霧砲的火藥。這裡沒有爭鬥過的跡象。每個人都想到自己的家、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小孩(如果有的話),想到自己坐在溫暖的火爐前方,有人撫摸自己的背說:「親愛的,今天辛苦你了。」燈塔裡沒有家人,只有三個管理員,而這三人此刻已經死在燈塔內的某處。屍體在哪裡?那些屍體的狀況如何?
一行人來到四樓,看到石蠟槽。接著到五樓,這裡存放著燈頭用的油。其中一人再度呼喚管理員的名字,主要是為了驅走難以忍受的靜寂。現場沒有逃跑的跡象,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那些管理員逃到其他地方。
他們離開存放燃油的樓層,爬上沿著牆壁內側通往燈室的鑄鐵螺旋樓梯。樓梯的扶手閃閃發亮。燈塔管理員是很特殊的人種,非常執著於室內環境的細節,不斷擦拭、清理、打掃。燈塔可以說是最乾淨的地方。他們檢查銅製扶手,沒有看到任何指印。這是因為管理員為了保持清潔,都會避免去碰扶手。除非有人跑得很急,或是有人摔倒而緊急抓住扶手,或是因為發生可怕的事件而一時忘我……不過這裡並沒有特別奇怪的跡象。
一行人的腳步聲聽起來就像死亡的鼓聲,堅定而深沉。他們已經在懷念安全的拖輪與陸地了。
他們來到廚房。這裡有十二英尺寬,中央有垂直通過的重錘管。牆上安裝了三個櫥櫃,裡面整齊堆放各種罐頭食品,有焗豆、蠶豆、米、湯、OXO高湯塊、加工肉、鹹牛肉、醃菜等,角落則放置沒有打開的玻璃罐,裡面裝滿了法蘭克福香腸,看起來就像實驗室的組織標本。窗邊有水槽,紅色水龍頭打開是雨水,銀色水龍頭則是淡水。水槽旁邊晾著洗滌盆。在內牆與外牆之間、管理員用來儲藏食物的架子上,放了一顆枯乾的洋蔥。水槽上方有一個附鏡子的儲物櫃。管理員把這裡兼作浴室使用,因此放了牙刷、梳子、沐浴用品及古龍水。在它旁邊則是裝刀叉與杯盤的餐具櫃,每一件東西都一如預期收納得很整齊。牆上的時鐘停在八點四十五分。
「這是怎麼回事?」留著小鬍子的男人問。
桌上擺好餐具,準備迎接沒有吃的一餐。餐具只有兩份,各有一組刀叉及一張等著放食物的盤子,另外還有兩個空杯子、鹽巴和胡椒、軟管裝的芥末醬、已經清乾淨的菸灰缸。料理台是美耐板材質,作成新月狀,剛好沿著重錘管周圍設置。料理台下方擺了一張長椅和兩張椅子,其中一張的泡棉露出來,另一張則斜斜放置,彷彿坐在這張椅子上的人很匆促地離開座位。
另一名頭髮往後梳的男人檢查烤爐,確認裡面沒有在烤東西,不過溫度是下降的,烤箱裡也沒有東西。透過窗戶可以聽到海浪拍打底下岩石的聲音,聽起來宛若嘆息。
「我實在是搞不懂。」這句話與其說是回答,不如說是承認普遍而可怕的無知。
一群人抬頭看天花板。
重點是,在燈塔中沒有地方可以躲藏。從下到上的每一間房間,只要走兩大步就會碰到重錘管,再走兩步就會到另外一邊。
他們上樓到臥室。沿著彎曲的牆壁有三張香蕉形的床鋪,每一張的簾子都是打開的。這些床鋪都鋪得很整齊,床單繃得很緊,枕頭和駝色的被子摸起來很粗糙。上方有兩張較短的床是給訪客用的,而且都有附梯子。梯子下方是拉上簾子的儲物空間。頭髮往後梳的傢伙屏住氣拉開簾子,但卻只找到一件牛皮夾克和掛起來的幾件上衣。
他們爬到第八層,來到位於海面上方一百英尺的地方。客廳裡有一台電視機和三張破舊的Ercol扶手椅。在最大的那張椅子(他們猜測那是主任管理員的椅子)旁邊的地上,放了一個杯子,杯裡殘留些許冷掉的茶。重錘管後方是來自樓下的暖氣管。也許主任管理員隨時都會下來見他們,告訴他們他剛剛在上面的燈室擦燈,其他人也在那裡,在外面的迴廊,所以很抱歉沒聽到呼喚聲。
這裡的壁鐘也停在同樣的時間:八點四十五分。
一道雙開門通往第九層的值勤室。死者有可能在這裡──緊閉的空間有可能阻止氣味外流。不過一如他們的預期,這裡也沒有人。那些管理員離開了這座燈塔,只留下燈。整整九層樓都沒有找到人。一行人來到樓頂,看到處女燈。這是一口巨大的煤氣燈,被宛若鳥翼般脆弱的鏡片覆蓋。
「到此為止。他們不見了。」
海平線附近形成羽狀的雲。風再度吹起,改變方向,掀動浪峰的白色泡沫。那些管理員彷彿一開始就不在這裡,或者是爬到樓頂飛走了。
1
接班
朱利打開窗簾,看到灰濛濛的天已經亮了。收音機播放著似曾聽過的歌。他邊喝紅茶邊聽新聞報導:一個女孩在北方的公車站走失了,可憐的母親傷心欲絕──那是當然的。朱利在腦中想像那個女孩的模樣:短髮,短裙,有一雙大眼睛,在冷風中發抖。他也想像到空無一人的公車站 。先前應該有人在那裡,以溺水者般的動作招手;公車停下來又開走,沒有察覺到異狀,人行道在黑暗的雨中閃閃發光。
大海風平浪靜,呈現狂風暴雨之後特有的鏡面質感。朱利打開窗栓。新鮮空氣感覺幾乎像是可吃的固體,在海邊小屋之間發出叮噹聲,就如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