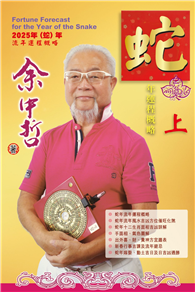◎睽違17年!直木賞、山本周五郎賞雙冠王◎
祂,代表世間的無常,
是「當下之主」,
像「夜」與「風」一樣,無所不在、捉摸不定。
在至上神靈的操弄之下,
我們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嗎?
祂,代表世間的無常,
是「當下之主」,
像「夜」與「風」一樣,無所不在、捉摸不定。
在至上神靈的操弄之下,
我們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嗎?
☀☀☀
犯罪小說全新境界
阿茲特克文明⨉暗黑神話⨉毒品走私⨉器官販賣
突破日本當代大眾文學疆界,窺見社會角落,嶄新大膽的重磅之作
熱銷超過105,000冊,Amazon.jp讀者5星評價逾1,000則
☀☀☀
★ 知名作家宮部美幸盛讚:「一瞬間都不讓人鬆懈的傑作。」
★ 入選寶島社2022年「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TOP2
★ 入選早川書房《推理小說雜誌》2022年「好想讀這本推理小說!」TOP2
★ 作者曾獲群像新人文學賞、江戶川亂步賞、大藪春彥賞、吉川英治文學新人賞等重要獎項
墨西哥古文明阿茲特克最重要的信仰神祇──特斯卡特利波卡,
不代表任何一種自然力,也不是部落的守護神,而是無常的化身,
人們為了終結無常,甘願成為祂的奴隸,奉上「跳動的心臟」,做為獻祭……
『在阿茲特克帝國滅亡將近500年之後,
橫跨墨西哥、印尼、日本,
一場空前絕後的慶典正準備揭開序幕!』
2015年,承襲了阿茲特克祭司血統與信仰的後代──
墨西哥販毒集團的首領瓦米洛.卡薩索拉,
與敵對組織發生衝突,舉家遭到殲滅,孤身逃離墨西哥。
他在藏身地印尼,遇到一名日本器官掮客,
一群亡命之徒決定合作,開創前所未有的跨國事業──「心臟買賣」,
輾轉來到日本,瓦米洛逐步重建起屬於自己的犯罪集團。
在日本川崎,他遇見一名孤獨少年──小霜。
瓦米洛發掘小霜的獨特才能,將他納入麾下、視如己出,
教導他關於阿茲特克文明、特斯卡特利波卡的事物。
不知不覺間,小霜從瓦米洛身上得到從未體會過的「家人」羈絆,
卻也被迫捲入一場勢必會犧牲人命的偉大計謀……
「沒有人知道生命的目的。」
面對世界的殘酷,瓦米洛與小霜,兩個無家可歸的人,
他們的生命軌跡不可思議地跨越汪洋交會,
這一切,似乎冥冥夾雜著特斯卡特利波卡的意念。
「了解恐怖,我們就能獲得面對現實的智慧。」
關於家人、復仇、權力、欲望、命運、信仰……
看見人類的虛渺,人心永恆的黑暗與光潔,
一部令人欲罷不能的犯罪小說!
本書以距今數百年的中美洲阿茲特克文明做為背景,
自然巧妙地融入當今的生活面貌,大膽叩問現代社會萬象,
包括毒品濫用、器官販賣、無戶籍兒童等問題,
也反映「以信仰之名,行犯罪之實」的現象。
在閱讀的過程中,彷彿一步步陷入一場阿茲特克的狂暴幻夢中,
同時,也看見在命運的框架之下,試圖活出自我意志的人類身影。
作者以大量文史材料為基礎,讀來卻不艱澀,
反而會與主角的經歷產生共鳴,令人沉浸其中,難以自拔。
究竟,在恐怖之神的陰影之下,瓦米洛與小霜會走向什麼樣的境地?
對未來失去希望的人們,真的能夠逃離黑暗,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嗎?
※封面設計理念※
主視覺的設計原型來自大英博物館的重要館藏──
以骷髏頭製成的特斯卡特利波卡面具。
過去,阿茲特克人為了表現出他們所崇敬的「特斯卡特利波卡」之形象,
以黑曜石的馬賽克裝飾骷髏頭,外側覆以褐煤及綠松石,
眼中嵌著黃鐵礦,鼻子襯著紅牡蠣殼,
展現出中美洲原住民獨有的技藝與想像力。
本書以特斯卡特利波卡的面具做為發想,
重新繪製一款屬於現代的特斯卡特利波卡,
以鮮豔的色彩及花紋裝飾,營造出阿茲特克的神祕風格。
讀到此書尾聲,便會發現原來封面栩栩如生的圖像,
正與燦爛偉大的古代文明遙相輝映著。
入迷推薦
吳曉樂│作家
馬雅人│FB馬雅國駐臺辦事處
盛浩偉│作家
盧建彰│導演、作家
各界齊聲讚譽
「直木賞漫長歷史中最燦爛的黑色太陽。」──宮部美幸,作家
「雖然不想使用『只能說是傑作』這樣陳腐的說法,但只能說這本書是真正的傑作。」──三浦紫苑,作家
「這是一部充滿力量、恐怖、悲傷和美麗的小說。」──江國香織,作家
「可怕的現代暴力和古代祭典的共存。與其說是想看電影版,不如說是讀完便有一種看完電影巨作的感覺。」──押井守,電影導演
「正因為是血淋淋的極惡世界中,某一瞬間的人心交流,才讓我更被打動!雖然是以神話為主題的作品,卻感受到了無庸置疑的人類讚歌。」──板垣巴留,漫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