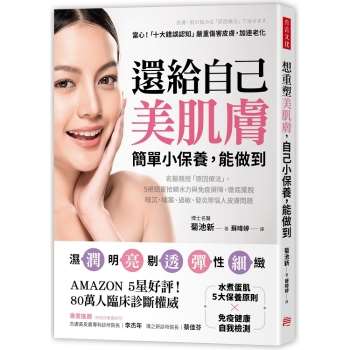★ 心理創傷治療大師彼得.列文,深入剖析創傷與記憶之作
★ 《心靈的傷,身體會記住》貝塞爾‧范德寇醫師專文推薦
聽到小孩哭就大發雷霆、看到水杯掉落就驚慌失措地躲到桌子下,
也許你會記得那是小時候的某個事件,導致你現在的激烈反應,
也許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為何會如此。
一般的記憶會隨著時間過去而消褪,
但創傷記憶卻是會伴隨恐懼、憤怒、崩潰等強烈負面情緒,
成為創傷印記,如影隨形……
▍解構創傷與記憶,走出記憶裡的傷
彼得.列文博士在本書中,將完整分析過往記憶造成的創傷,以及那些扭曲、不存在的記憶,為何會變成創傷。解構、梳理、覺察創傷記憶,才能拋開創傷的束縛。
>>讓人重蹈覆轍、深陷危險的創傷記憶
兒時受到騷擾,成人後會故意與暴力男發生關係;戰場老鳥對危險事物「上癮」,退伍之後加入霹靂特警隊。這樣的創傷記憶無意中讓自己暴露在危險情境中,讓歷史不斷重演。
>>高壓與危險,產生記憶扭曲與錯置
美國知名主播布萊恩‧威廉斯,曾說自己在伊拉克戰場採訪時,乘坐的直升機被砲火擊中,後來被踢爆為造假,被擊中的是在他前面的直升機。前美國第一夫人希拉蕊,曾宣稱自己在波士尼亞受到狙擊,後來調查發現她並未受到直接狙擊。這些名人是為了自身利益說謊的騙子,還是有別的原因?其實在高壓與危險的情況下,每個人都有可能產生記憶扭曲。
不管是真實記憶或是虛假記憶,背後隱藏的是盤根錯節的創傷,
這些創傷會震懾大腦、麻痺心智、凍結身體,成為痛苦的來源。
彼得博士認為解決創傷,必須處理身體上的癱瘓、煩躁與無助,
並採取一些身體行動,來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
作者簡介:
彼得.列文(Peter A. Levine, PhD)
擁有醫學生物物理學與心理學博士雙學位。列文博士發展出一種療癒創傷的身體覺察方法,也就是身體經驗創傷療法。他是美國太空總署NASA太空梭開發計畫的壓力顧問,也是世界事務協會心理學家社會責任專案小組的成員,負責發展大規模災害與種族政治戰爭的因應對策。暢銷著作《喚醒老虎》已被翻譯成二十四種語言。列文博士對於身體心理治療的原創貢獻,於二○一○年獲得美國身體心理治療協會(USABP)頒發終身成就獎。另外,在嬰兒與兒童精神病學方面的研究工作,獲頒雷斯‧戴維斯研究所(Reis Davis)的榮譽主席。
關於列文博士的培訓、專案與文獻等資訊,可參考www.somaticexperiencing.com。
譯者簡介:
徐曉珮
政治大學英語系、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研究所畢。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肄業。工作語言為中英日,熱愛英美文學及日本動漫藝能與寶塚。譯有《故事‧解構‧再建構》、《他與她》、《擁抱陰影》等書。Email: hikari1974@gmail.com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彼得‧列文在又一部重要的著作中解構了創傷記憶,讓創傷更容易療癒與轉化──嘉柏‧麥特醫師(Gabor Maté)/《當身體說不的時候》作者
治療大師彼得‧列文以深入且洞察的角度,撰寫了關於程序性記憶的心理生物動力學,並提供了重要的工具,讓治療師得以進行創傷記憶的轉化。
──史丹‧塔特金(Stan Tatkin)/心理學博士
列文博士運用已經建立的神經科學,以清楚易懂的詞彙解釋了各種記憶的類型、記憶的神經基礎,以及記憶在創傷治療中扮演的角色。
──彼得‧佩恩(Peter Payne)與瑪蒂‧克瑞恩葛楚博士(Mardi Crane-Godreau)
理解記憶從來不客觀、會不斷被當下經驗改寫後,讓我感到謙卑,鬆動主觀的執念,並多一份寬容的好奇。
──王裕安/身體經驗創傷療法治療師
很多時候我們不自覺的反應都來自潛意識的投射,而這些投射深深影響著我們的一生。只有認出這些潛意識的創傷記憶,才有改變生命的契機。
──田定豐/聲波療癒師、心靈作家
作者是創傷領域的先驅,作品經典且深入實用!
──李旻珊/身心科醫師
周志建/資深心理師、故事療癒作家
劉仲彬/善言心理治療所所長、臨床心理師
蘇益賢/臨床心理師
鐘穎/心理學作家、愛智者書窩版主
名人推薦:彼得‧列文在又一部重要的著作中解構了創傷記憶,讓創傷更容易療癒與轉化──嘉柏‧麥特醫師(Gabor Maté)/《當身體說不的時候》作者
治療大師彼得‧列文以深入且洞察的角度,撰寫了關於程序性記憶的心理生物動力學,並提供了重要的工具,讓治療師得以進行創傷記憶的轉化。
──史丹‧塔特金(Stan Tatkin)/心理學博士
列文博士運用已經建立的神經科學,以清楚易懂的詞彙解釋了各種記憶的類型、記憶的神經基礎,以及記憶在創傷治療中扮演的角色。
──彼得‧佩恩(Peter Payne)與瑪蒂‧克瑞恩葛楚博士(Mardi Crane-Godr...
章節試閱
阿諾與我
請容許我再舉一次自己的例子。以下的小故事說明了程序性、情緒、情節與陳述性記憶的功能,如何靈活地編織出我們的生活結構。
大約二十五年前,我到紐約市探望我的父母。在參觀了一整天的博物館後,我坐上往北的地鐵D線。剛好是下班高峰,車裡擠滿了身穿深深淺淺灰色西裝、歸心似箭的上班族,大部分人的腋下都夾著摺得整整齊齊的報紙。有名特別高大的男性引起我的注意。我朝他看了一眼,這個陌生人讓我感受到一種模糊但發自內心的溫暖,還有一份不可思議的輕鬆自在。我發現自己的胸部和腹部特別地開展或說敞開,同時還有一絲絲想要靠近他的欲望。
我們兩個人都在205街,也就是布朗克斯區的最後一站下了車。我順著雙腳的奇特衝動走到他身邊,發現自己碰了他的手臂。我們懷著共同的好奇望向對方。「阿諾」這個名字意外地從我嘴裡冒了出來。我不知道究竟是誰比較驚訝,但我們倆就這樣站住不動,困惑地看著對方好一會兒。那時我才意識到我和阿諾是小學一年級的同學,這已經是距離這次地鐵上偶遇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六歲那時,我是班上年紀最小的孩子。我的耳朵特別大,經常被人欺負。阿諾是唯一一個一直都和我當朋友的孩子。就這樣,我們為一段持久的友誼關係奠下了基礎。幾十年來,他的友善保護以一種印記的形式儲存,蟄伏在我的情緒與程序性記憶庫中,直到那一瞬間的姿態與長相提供了再認(recognition)的指示線索,才又帶領我走向他,並發現我們擁有的共同過去產生了新的情境。
我一邊爬上山坡往爸媽住的公寓走去,一邊感受著脊椎挺了起來,好像有一根隱形的線輕輕把我的頭往天空的方向提起。我的腳步明顯變得輕快。小學一年級時的許多畫面與感覺感動了我。有了這些情節記憶加上心胸敞開的感覺,我才能夠去反思一些痛苦的時刻。我記得我的同學們如何用「小飛象」這個綽號嘲弄我,只因為我有一副大耳朵。
然後,在我走進公寓時,清晰地感覺到了我的雙腿與雙臂湧出了身體上的力量,胸口也充滿著自豪。因為這種程序性意識,另一段情節記憶具體浮現出來,我回想起最後一次遭受霸凌的時候,是距離現在六十多年前了。那時我被兩個最兇惡的小霸王包圍,事實上是一對雙胞胎。我現在眼前還能浮現當初把我逼到干丘路上迎面而來的車流中,那兩張刻薄嘲弄的臉。我們所有的人都很驚訝,因為我開始瘋狂揮動手臂,挑釁地朝他們走去。他們停下腳步定住不動,表情急遽變化,從嘲笑輕蔑變成震驚恐懼,然後逃走了。那是我最後一次被欺負,之後其他孩子都很尊重我,會邀請我跟他們一起玩。
這個故事說明了程序性記憶與情緒記憶持久的重要性,是我們一生中可以隨時取用的具體化資源。我第一次在地鐵上注意到阿諾時,浮現的「記憶」是一種微弱的內隱記憶,對他有種奇特的親近感,完全沒有任何緣由或情境。這種程序性記憶化作長時間的凝視,胸口微微擴張、脊椎挺直延展,然後我的腹部產生一股溫暖而寬闊的感覺。然而,當我朝他走近,口中說出他的名字時,就開始從內隱的程序性記憶(身體感官、姿勢、肌肉動力)轉變為情緒記憶(驚訝、好奇),然後再變成可以讓我順應與反思的情節記憶(參見圖2.2)。
隨著通往過去的大門打開,我能夠更有意識地去回憶那年發生的一些冒險片段,或說是情節記憶。我因為年紀的關係,所以半途插班,面對新環境與大家格格不入而感到難受,不過有感受到阿諾給予我的支持,讓小時候的我能獲得自己的力量與自信,最後重新連結到我如何起身對抗班上的小霸王,獲得其他孩子的接納,取得勝利。在這些情節記憶中,當我想像自己對抗那些小霸王的時候,就能感覺到手臂和肩膀蓄勢待發、充滿力量。就在這一刻,我的情節記憶再次喚醒了防衛、力量與自我保護的程序性記憶。充滿勇氣與活力地走在公寓的樓梯上,我感覺到溫暖、感激與自豪。我現在可以將這段情節記憶運用陳述的形式,敘述成一個連貫的故事。
與最初在地鐵上遇到阿諾的程序性吸引相較,我在走向爸媽家時,回想起小一遭遇的回憶,則是情節記憶。這些記憶是在相對比較有意識的層面進行的回想,雖然說主要還是屬於自發性動作。與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一樣,我在阿諾身上感覺到的那種神祕(程序性)吸引力,是因為內隱的觸發因素而喚起。普魯斯特書中的情節,觸發因素是糕點浸了茶水後的味道。他想的不是:「喔,這塊糕點讓我想起小時候,媽媽會給我一杯茶和一個瑪德蓮蛋糕,這讓我想起上學的那段路。」相反地,茶加上瑪德蓮的感官體驗觸發了大部分在潛意識中運作的程序性、情節與情緒過程。對我來說,觸發點在於我對於阿諾的長相、姿勢與動作呈現的各種樣貌與輪廓,有著久遠而內隱的再認。不知不覺中,我透過某種方式,整理了在這一生中接觸過的數十萬張面孔、身體、姿勢與步態,然後推斷出小時候見過的這些模式,屬於這名四十六歲的男性!唯一可能的原因,是阿諾在將近四十年前,在生理、情緒與人際關係上,對我造成強大的影響。
如果做為成年人,碰巧在街上遇到小時候認識的人,我們很可能不會有意識地認出他們。然而,我們可能會體驗到一種特別的感覺基調與相關情境:如果曾經是朋友,會感到快樂;如果曾經受欺負,會感到恐懼。換句話說,我們會區分朋友與敵人,雖然可能連對方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記得是在哪裡認識他們,甚至是不是真的認識他們。也就是說,要等到情緒的程序性記憶轉化成情節記憶的拼貼,再變成陳述性形式,才可能真正想起。超級電腦,例如IBM的華生,面臨的正是能否執行如此複雜的模式再認工作。即使是最先進的超級電腦與其菁英軟體工程師,都無法像人類與動物一樣再認並運用「情緒基調」。這就是內隱記憶顯而易見的力量,能夠紀錄情緒上的精微差別、人際關係的經驗,並在我們整個人生的發展弧線中持續對意義進行計算處理。
在內隱與外顯記憶之間移動的能力,從較無意識到更有意識(反之亦然),也是創傷經驗整合與全面了解我們過去、現在、未來是誰的重要主題。我對阿諾的記憶證明了內隱與外顯記憶系統之間連貫交流的價值正是這種感官、感覺、意象與行動之間的流動關係,讓我能夠編織出嶄新的成人敘事,增強了我在掌控、成功、活力與自我等方面的覺察。能夠重新獲得自信並感覺到自己的力量與能動性,對我來說正是時機。我相信這有助於提供一個基礎,讓我下定決心放棄一個消耗精力的「正職」,抓住能夠讓我釋放出創造力的自由。這也許更給了我信心,讓我全心全力在學術與產業界之外的領域,做到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這種獨立的能動性激勵我對治療願景的追求,讓身體經驗創傷療法成為我一生的志業。事實上,這段旅程說明了程序性記憶的重要性,是讓人生前進的具體化資源。
有多少人像阿諾一樣「活」在我們的心靈中,加強或擾亂我們的情緒,並控制我們的身體反應呢?儘管我們可能很難感覺到他們的存在,但我們都處在他們的隱影之下,無論好壞。事實上,意識範圍的雷達通常無法偵測的這些內隱記憶運作,多半會在我們最不期待或希望他們出現的時候啟動。為了打破這些負面的「情結」(通常與我們的父母有關),並增加正面的「情結」,我們需要培養自我探索與自我覺察反思的能力。我與阿諾相關的這個故事就是一個例子,說明我們如何敞開心胸,對生活充滿好奇與探索,以及讓這種能力帶動我們並賦予我們力量。
阿諾與我
請容許我再舉一次自己的例子。以下的小故事說明了程序性、情緒、情節與陳述性記憶的功能,如何靈活地編織出我們的生活結構。
大約二十五年前,我到紐約市探望我的父母。在參觀了一整天的博物館後,我坐上往北的地鐵D線。剛好是下班高峰,車裡擠滿了身穿深深淺淺灰色西裝、歸心似箭的上班族,大部分人的腋下都夾著摺得整整齊齊的報紙。有名特別高大的男性引起我的注意。我朝他看了一眼,這個陌生人讓我感受到一種模糊但發自內心的溫暖,還有一份不可思議的輕鬆自在。我發現自己的胸部和腹部特別地開展或說敞開,同時還有一絲絲...
推薦序
推薦序
創傷記憶研究在心理學與精神病學領域有著古老而悠久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至一八七○年代的巴黎,神經學之父讓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對於硝石庫慈善醫院病房裡歇斯底里的病人,為何會發生癱瘓、抽搐、昏厥、突然崩潰、瘋狂大笑與劇烈哭泣的狀態十分感興趣。沙可與他的學生逐漸了解,這些怪異的動作與身體姿勢,是創傷的身體印記。
一八八九年,沙可的學生皮爾‧珍妮特(Pierre Janet)寫了第一本與我們現在所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相關的《心理學無意識行為》一書。他在書中指出,創傷儲存於程序性記憶中——存在於自發動作與反應,以及感官與態度之中,同時創傷會以身體內部的內臟覺(焦慮與恐慌)、身體動作或視覺意象(夢魘與閃回)等形式重現與重演。珍妮特將記憶這個議題放在創傷處理的首要與中心位置,只有在情緒淹沒狀態干擾正確記憶處理時,事件才會變成創傷。之後,受到創傷的患者會在遇到觸發創傷的事件時,產生與最初威脅相應的緊急反應,但現在這些反應完全不合時宜——像是水杯掉在地上時驚慌失措躲到桌子下,或是聽到小孩哭就大發雷霆。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已經了解,創傷的印記不是儲存為過去發生壞事的敘事,而是變成遭遇當下生命威脅體驗到的生理感官。在這段時間裡,我們逐漸明白一般記憶(隨著時間過去而改變與消褪的故事)及創傷記憶(伴隨強烈負面情緒,例如恐懼、羞恥、憤怒與崩潰,反復出現的感官與動作)之間的不同,是負責創造「自傳式記憶」的大腦系統崩潰的結果。
珍妮特還指出,受到創傷的人會陷入過去出不來,他們會固著於自己有意識地想要拋掉的恐懼,但是表現出的行為與感覺又彷彿恐懼一直存在。在無法放下創傷的情況下,如果不想讓情緒失控,就必須付出代價,放棄照顧當下的需求,能量也因此消耗殆盡。珍妮特與他的同事從痛苦的經驗中了解到,他們所照顧的那些受到創傷的女性,無法透過推理或洞察,以及行為矯正或懲罰,來療癒創傷,但她們卻能對催眠暗示做出反應,藉由在催眠失神狀態下重溫創傷事件來解決創傷。在腦海中安全地重演過去發生的事件,然後建構出一個想像中令人滿意的結果——是他們在最初的事件中,因為被無助與恐懼淹沒而無法做到的狀態。他們開始可以充分理解到,事實上自己已經在創傷中倖存下來,而且可以恢復並繼續原有的生活。
大約二十五年前,我第一次見到彼得‧列文,以為自己遇見了一位古老魔法師轉世,因為我曾經在老醫院圖書館書堆裡的許多發霉手稿中,熟讀這位大師的著作。彼得不像古早照片裡那樣繫著領結、穿著晚禮服,而是身著雷鬼歌手巴布‧馬利(Bob Marley)的T恤與短褲,站在加州大蘇爾埃薩倫研究所(the lawn of the Esalen Institute in Big Sur)的草坪上。彼得表示,他對創傷有著完全的理解,認為這是身體上的印記,療癒創傷就必須創造一種受到保護的失神狀態,可以從中安全地觀察可怕的過去。然後他添加了探索創傷精微生理印記的關鍵要素,並專注於身體與心靈的重新連結。
這立刻就引起了我的興趣。從最早研究創傷壓力的學生開始,一直到最新的神經科學研究,科學家已經注意到身體動作與記憶之間的重要關係。人類有機體被壓垮而產生無助與癱瘓反應時,這個經驗就會成為創傷——因為不管做什麼都無法改變事件的結果,所以整個系統就會崩潰。
甚至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對創傷與身體動作之間的關係很感興趣。他認為,人們不斷重複創傷的原因,是由於他們無法完全記得發生過什麼。因為記憶受到壓抑,患者「被迫將這些被壓抑的素材視為當下的經驗不斷重複,而無法……記得這件事其實已經屬於過去。」
如果一個人不記得,就很可能會以身體行動表現出來:「他不是將之複製為記憶,而是複製成行動;他會不斷重複,而且當然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重複……最後我們了解,這是他用來記得的方式。」但是佛洛伊德沒有意識到的是,只有在幫助人們內心感到安全與平靜的情況下,他們才能重新獲得自主權。
彼得了解,為了解決創傷,必須處理身體上的癱瘓、煩躁與無助,並找到一些可以採取的身體行動來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即使只是講述發生的事情,也是一種有效行動的方式,敘事的構成可以讓你與周圍的人知道發生了什麼。悲哀的是,非常多受到創傷的人都陷在自身的創傷中,永遠沒有機會發展這種重要的敘事。
我對彼得認識得越多,就越會意識到他對生理感官與身體動作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了解得有多深。他表示,創傷後行為不僅包括粗暴的動作,例如對任何冒犯你的人暴怒,或在害怕時整個癱瘓,而且還包括難以察覺到的摒住呼吸、肌肉緊張,以及縮緊括約肌。他讓我知道,整個有機體,也就是全部的身、心、靈,變得動彈不得,並持續表現出好像當下有一個非常明顯的危機。彼得最初接受的是神經生理學家的訓練,後來在埃薩倫研究所學習艾達‧羅夫(Ida Rolf)的身體工作療法,我在觀摩他如何進行工作時,想起了摩謝‧費登奎斯(Moshe Feldenkrais)。他認為世界上沒有純粹的精神(也就是心理)經驗:「生命的概念可以分成身體與心靈……這種想法比實際運用的存在還要久遠。」我們的主觀經驗總是存在身體的成分,就像所有所謂身體的經驗都存在心靈的成分一樣。
大腦是由身體動作表達出的心理經驗編碼而成。情緒是透過臉部表情與身體姿勢來傳達:我們透過握緊的拳頭與緊咬的牙關感受憤怒,透過緊繃的肌肉與短淺的呼吸明白恐懼。思想與情緒伴隨著肌肉張力的變化,而為了改變習慣模式,我們必須改變連結感官、思想、記憶與行動的身體循環。因此治療師的主要任務,是觀察與處理這些身體的變化。
在我還是芝加哥大學的學生時,尤金‧簡德林(Eugene Gendlin)試圖教導我何為「身體覺知」,也就是對於自我的意識,以及思想與行動之間的空間。但我對身體覺知並未完全理解,直到目睹彼得運用生理覺察作為學習的關鍵。他對觸摸的運用讓我學到了很多。在我接受的訓練中,觸摸是被嚴格禁止,而在我的成長過程中也被嚴重忽視。但彼得對觸摸的運用幫助我更能覺察自己的內在經驗,並理解到觸摸的巨大力量,可以幫助人們從彼此身上獲得撫慰與生理安全。
覺察到內在的感官,也就是我們的原始感覺,會讓我們能夠直接體驗自己的生命體,從快樂到痛苦的整個範圍,這些感覺源自於腦幹的最深層面,而不是大腦皮質。對於這一點的理解非常重要,因為受到創傷的人很害怕自己內在發生的事情。要他們專注於自己的呼吸,可能會引發恐慌反應;單純請他們靜止不動,通常只會增加他們的焦慮。
我們可以在腦部掃描中,觀察出這種與身體自我疏離的神經推論:患有慢性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的人,負責自我覺察(內側前額葉皮質)與身體覺察(島葉)的大腦區域,通常會萎縮,因為身體/心智/大腦已經學會自我封閉。這種封閉伴隨著巨大的代價:傳達痛苦與沮喪的大腦區域同樣也負責傳遞喜悅、快樂、目的與關係連結的感覺。
彼得告訴我,也在這本書中告訴大家,對自己或他人的負面判斷,如何造成心智與身體緊張,進而讓我們無法學習。想要恢復的話,人們要能夠自由探索並學習新的動作方式。只有這樣才能讓神經系統自行重組,並形成新的模式。這只有在透過研究新的動作、呼吸與啟動方式才能實現,而不能透過指定為了「修復」而做的特定行動來完成。
在接下來的章節中,彼得‧列文解釋了創傷記憶的內隱性質,以及在身體與大腦中以感官、情緒與行為拼湊起來的方式。創傷性印記悄悄地強加在我們身上,與其說是故事或有意識的記憶,不如說是情感、感官與「程序」,是身體自動做出的事情,就像是心理的無意識行為。如果創傷是以程序性的無意識行為展現出來,那麼療癒就不能透過建議、藥物、理解或修復來完成,而是要透過獲得與生俱來的生命力(我使用的詞彙),也就是彼得所說,「我們對堅持與勝利執著的固有驅力」。
這是由什麼來組成?了解自己,感受生理的衝動,注意身體的僵硬與收縮狀態,以及內在覺察的增強如何影響情緒、記憶與衝動的產生。創傷的感官印記對我們接下來的反應、行為與情緒感覺狀態有著強大的影響。習慣於隨時警覺不讓過去的惡魔進入意識之後,我們反而必須學會單純而不帶判斷地注意到這些印記,並觀察其原本的樣貌,也就是啟動天生運動動作程式的訊號。遵循自然的過程有助於重新調整我們與自己的關係。不過,這種正念的自我監測很容易解離,進而引發恐慌、爆發、凍結或崩潰。
處理這種容易解離的敏感,基本概念之一是彼得的「擺盪」理念:在知道自己會習慣於這種感覺的情況下,接觸內在感官並學習容忍,然後從容地回到更安全的日常生活。這種工作方式並非宣洩療法,或者說,我喜歡稱之為「吐出創傷」。學習仔細地接觸「身體覺知」,讓我們更有可能了解潛伏在內心深處的危險訊號,並有機會加以掌控。在能夠安全地感受與恐懼及毀滅相關的感官之前,首先必須了解內在力量與健康攻擊是什麼樣的感覺。
本書中最精彩的獨創討論之一,是彼得解釋為了應對極端的逆境,要如何同時啟動大腦的動機系統與行動系統。動機系統是由大腦的多巴胺系統運作,行動系統則是由正腎上腺素系統運作。為了能在巨大挑戰中創造生命的意義,兩個系統都需要在治療過程中獲得激勵。這些是面對並轉化過去的惡魔,從無助的屈服通往擁有完全自主權的必要條件。
好的治療方法包括學習喚起身體覺知,但不會被潛伏在內心的陰影淹沒。不管使用哪種療法,最重要的提示句都是「注意」以及「注意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允許自己觀察內在過程,可以啟動連結大腦理性與情緒部分的大腦通路,這是目前所知個人能夠有意識地重新調整大腦知覺系統的唯一通路。為了與自我保持連結,必須啟動前島葉這個負責感覺身體與自我的重要大腦區域。列文指出,大部分靈性傳統都發展出呼吸、運動與冥想技巧,以促進深層情緒與感官狀態的容忍與整合。
身體經驗創傷療法緩慢、細緻、正念地專注於內在感官與精微動作,大多數表達性治療則多半著重於外在引導的行動,而不是自我的身體覺知,兩者非常不同。專注於內在經驗能夠發掘傾向於無意識與反射性的程序性動作,這些動作可能牽涉到不同的大腦系統,像是小腦與椎體外系統,而非出於意志的刻意行動。
這種工作也與其他治療方法形成鮮明對比。其他療法鼓勵倖存者仔仔細細地反覆重溫創傷,同時創造出的條件帶有風險,會讓受到創傷的個體處於高度恐懼與生理喚起的狀態,可能因此強化過去遭受的痛苦。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創傷記憶會與那些新產生的恐懼一起重新鞏固並產生連結,這樣只會增加被內在世界淹沒壓垮的感覺。
本書記錄了豐富的案例過程,並詳細說明如何具體實施身體經驗創傷療法的原則,案例不僅包括像是車禍的創傷受害者,還有新生兒、學步兒、學齡兒童與戰鬥士兵。身體經驗創傷療法主要不是透過重溫創傷來「拋棄」創傷制約的反應,而是創造出與淹沒無助感相反的新經驗,並運用生理反應與感官的自主權來取代創傷制約的反應。
這種工作透過協助完成與解決創傷在身體上造成的爆炸性攻擊,消除凍結的羞恥、悲傷、憤怒與失落感。彼得的工作幫助我們超越他所謂的「破壞性解釋強迫症」,並創造一種內在自主權與對之前失控感官與反應的掌控。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創造一種具體行動的經驗,以對抗無助的屈服與無法控制的憤怒。只有等到我們能夠退一步來評估自我,降低感官與情緒的強度,並啟動與生俱來的生理防禦反應,才能學會修正我們根深蒂固、適應不當的自發生存反應,同時藉此讓我們陰魂不散的記憶得以安息。
貝塞爾‧范德寇醫師(Bessel A. van der Kolk),二○一五年七月十六日,於佛蒙特州卡博特
推薦序
創傷記憶研究在心理學與精神病學領域有著古老而悠久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至一八七○年代的巴黎,神經學之父讓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對於硝石庫慈善醫院病房裡歇斯底里的病人,為何會發生癱瘓、抽搐、昏厥、突然崩潰、瘋狂大笑與劇烈哭泣的狀態十分感興趣。沙可與他的學生逐漸了解,這些怪異的動作與身體姿勢,是創傷的身體印記。
一八八九年,沙可的學生皮爾‧珍妮特(Pierre Janet)寫了第一本與我們現在所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相關的《心理學無意識行為》一書。他在書中指出,創傷儲存於程序性記憶中——存在於自發動...
目錄
推薦序
導論:現狀
第一章 記憶:天賦與詛咒
第二章 記憶的結構
第三章 程序性記憶
第四章 情緒記憶、程序性記憶與創傷結構
第五章 英雄旅程
第六章 兩組個案研究:親密關係的觀察
第七章 真實性陷阱與虛假記憶陷阱
第八章 記憶分子
第九章 代際創傷:陰魂不散
後記
註釋
推薦序
導論:現狀
第一章 記憶:天賦與詛咒
第二章 記憶的結構
第三章 程序性記憶
第四章 情緒記憶、程序性記憶與創傷結構
第五章 英雄旅程
第六章 兩組個案研究:親密關係的觀察
第七章 真實性陷阱與虛假記憶陷阱
第八章 記憶分子
第九章 代際創傷:陰魂不散
後記
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