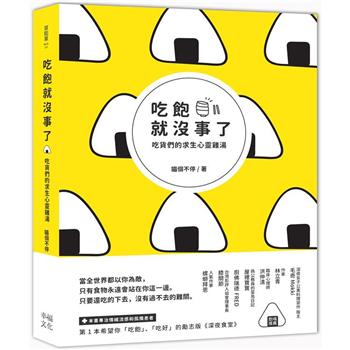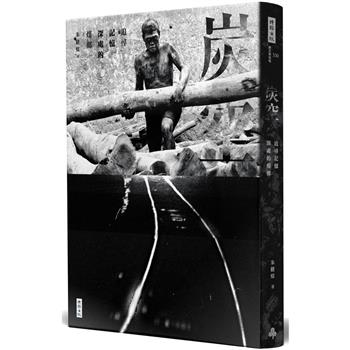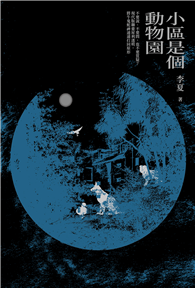姜雪寧不惜冒險闖進天牢也要替即將被流放的燕臨送行。
與上一世不同,命運的軌跡正在慢慢改變,
能保住多數人的性命,已是萬幸。
但好巧不巧,姜雪寧撞上了謝危的連環計──
除去公儀丞、清理京中勢力、借刀殺人。
環環相扣無半點缺漏,
卻因姜雪寧捲入其中而增添變數。
聽聞姜雪寧如今下落不明,正在斫琴的謝危心神一恍,
刻刀劃過指腹留下了深深的血痕……
本書特色
★晉江文學古言大神時鏡,72億積分超高人氣、9.8分高分作品。
★白鹿、張凌赫主演電視劇《寧安如夢》原作小說。
繁體中文版獨家設計書衣:
採用水彩紙紋理的麗綺紙,美術紙手感獨特。書名「坤寧」二字,以鏤空方式仿古風雕花門窗,以呈現坤寧宮的雅致。
※繁體中文版《坤寧》全八冊。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坤寧 五《寧安如夢》電視劇原著小說的圖書 |
 |
坤寧(五) 作者:時鏡 出版社: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6-2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10 |
二手中文書 |
$ 252 |
華文羅曼史 |
$ 253 |
古代小說 |
$ 288 |
中文書 |
$ 288 |
大眾文學 |
$ 288 |
文學作品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博客來 評分:
圖書名稱:坤寧 五《寧安如夢》電視劇原著小說
內容簡介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時鏡
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代表作《坤寧》、《我不成仙》、《貧僧》、《劍閣聞鈴》、《我的印鈔機女友》等,擅長古代言情、仙俠幻想類題材,文字流暢,情節跌宕。
雖無八斗高才,但奉一管拙筆,且寫二三劣書。人無大志,混口飯吃足矣。
時鏡
晉江文學城簽約作者,代表作《坤寧》、《我不成仙》、《貧僧》、《劍閣聞鈴》、《我的印鈔機女友》等,擅長古代言情、仙俠幻想類題材,文字流暢,情節跌宕。
雖無八斗高才,但奉一管拙筆,且寫二三劣書。人無大志,混口飯吃足矣。
詳細資料
- ISBN:9786263526259
- 叢書系列:Kadokawa Fantastic Novels DX
- 規格:平裝 / 360頁 / 14.7 x 21 x 2.25 cm / 普通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