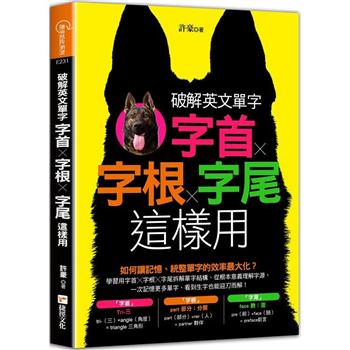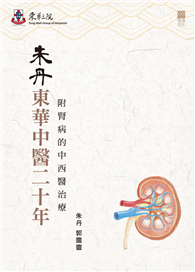第一章 塔裡的睡美人與她的王子
城市的一隅拉起了黃色警戒線。
馮艾保臉上戴著遮住半張臉的墨鏡,斜倚在車旁。紅色警戒燈光一閃一閃從他臉上掃過,帶起他嘴唇邊的一絲淺笑。
他伸手在車頂上用力拍了拍,接著彎下身從車窗往裡看,對還在車子裡與總部交談的搭檔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
「你看。」他指指被調高的警戒燈,頻率也被調低了,每隔約半分鐘才會在深色的天空上閃過一道紅光。
何思掛上電話,探頭順著馮艾保的手指看去,很捧場地笑笑。「第一次看到?」
「你說呢?」馮艾保哈哈一聲,反問回去,順手拉開了車門。「快下來,帶你參觀參觀我的少年時代。」
馮艾保與何思已經搭檔十年了,當然不會是第一次看到這種聊勝於無,往半空中投射的警戒燈。
還記得兩人第一次搭檔出任務的時候,同樣是夜裡的犯罪現場,黃色警戒線已經拉上了,地點在城市邊緣的小公園,周圍的居民在警戒線外探頭探腦,低低的交談聲嗡鳴著,聽在馮艾保耳中彷彿夏夜裡糾纏不休的蚊子。
你會很煩,卻又拿這些小渾蛋沒轍。
他們到達現場後,警戒燈便調整了高度跟頻率,像今天這樣,往高空上打去。馮艾保當年還是隻小菜雞,臉上乾乾淨淨隱約帶著點懵懂無知,何思比他早兩年入職,算是他的前輩,很貼心地安慰他。「別怕,有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
聞言,馮艾保立刻立正站好,用一種童子軍般澄澈天真的眼神看著何思,拘謹又好奇地確認。「真的什麼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嗎?」
這年馮艾保剛滿十八歲,才從學校畢業,在何思眼裡跟隻破殼三秒的小雞沒兩樣,表情和聲音都忍不住帶上慈愛。「可以,你問。我們這一行不怕問問題,怕的是明明有問題,卻裝作不知道。」
少年用力點點頭,在何思幾乎氾濫的體貼溫柔眼神中,用手指向天上的警戒燈。「那個,為什麼要朝天空打?」
豔麗的紅光恰好在夜空中一閃而逝。
「因為有你在啊。」何思溫聲解釋:「哨兵的五感比常人要敏銳許多,警戒燈的紅光對你們的視覺來說刺激太大了,所以才會往天空投射,避免對哨兵的視力造成暫時性的損傷。」
馮艾保靜靜聽何思說完才搖搖頭。「前輩,你誤會了,我知道為什麼要朝天空打燈。」
「那你想問的是……」何思困惑的瞇起眼。
「我只是覺得,這麼敷衍了事的警戒燈,恐怕召喚不出蝙蝠吧。」少年挽著手臂,瞇著純黑色的雙眼朝天上看,乍看之下像是失落,但熟人都知道,馮艾保只是試圖藏起眼中的頑皮而已。
「抱歉?」何思當時不知道少年本性,腦袋瞬間卡殼了,率先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什麼。
關蝙蝠什麼事情?話說回來,首都圈範圍內有蝙蝠族群嗎?
馮艾保把視線調回自己搭檔身上,眉彎彎眼彎彎唇角也彎彎。「沒什麼,這不重要,我身為哨兵總不會連一隻高科技蝙蝠都不如。」
姑且不論這句話會惹怒多少人,何思倒是察覺到眼前的小搭檔不是外表所見的單純天真。他自信、自傲可能還有些壞心眼,惡作劇得逞的歡快心情被何思的精神力觸手捕抓到,他才驚覺自己適才被人調侃了一番。
沒什麼壞心思,也不是惡意的,但就是……很欠揍。
這十年來,馮艾保沒少開警戒燈的玩笑,當然他嘴裡的高科技蝙蝠也沒少被拉出來溜幾圈,何思從一開始試圖理解,到現在他都心如止水了,隨便馮艾保想怎樣吧!
走下車,何思往左右看了看,感嘆道:「這是我待過最安靜的犯罪現場了。」
唯一在交談的,只有他和馮艾保兩人,周圍也沒有任何一個圍觀群眾,甚至連媒體都沒出現。
法醫和鑑識人員是第一批趕到的,早就在裡面忙碌一段時間了,像一群任勞任怨的工蟻,緊閉著嘴,表情嚴肅到近乎空洞,現場的大燈比普通犯罪現場的燈要暗了幾度,白熾光線陰森森的透出一種莫名的冷意。
警戒線內是一棟幾乎高聳入雲的白色巨塔,光滑的外觀看不出是何種材質建造而成,任何燈光打在塔壁上都會瞬間暗上幾度後很快散掉,整棟建築物除了底層的一扇大門外,從上到下不見一扇窗戶,明明通體雪白卻散發著壓抑的氛圍。
白塔位於一條長街的底端,遠離了城市最喧囂繁華的地區,坐落在城市邊緣。但並不是個陰暗危險的地方,相反的,這附近的治安絕對是整個首都圈最好的區域。
鄰近七個街區都是空曠的富人區,以長街為主幹道,可以從犯罪現場所在的白色巨塔一路望到盡頭的城市中心拱門。這是數世紀前留下的建築物,姿態典雅大方,雪白的石塊在裝飾燈的照耀下熠熠生輝,與白塔遙相輝映。
馮艾保聽了何思的感嘆,輕聲笑了出來。「這不算最安靜的時候,我聽到很多聲音。」
說著,馮艾保下意識伸手揉了揉太陽穴,這是他煩躁時的直覺動作,何思立刻用精神力觸手覆蓋在對方太陽穴上,用以安撫馮艾保的情緒。
馮艾保舒服了,歪著腦袋撒嬌般磨蹭了搭檔的精神力觸手。「走吧!」
兩人對看守的員警出示證件後,撩起警戒線走進了白塔。
說起白塔,算是馮艾保的二個家,從十歲開始到十八歲成年為止,他都在白塔生活。多數人離開後會時不時回來探望教官與老師,馮艾保倒是從沒回來過。
他總說自己是因為忙,只有何思知道,這貨就是討厭白塔的生活,毫無留戀罷了。馮艾保確實也不知道有什麼好留戀的,雖說白塔裡的日子不難過,卻也沒多好過,如果是個對人生大徹大悟的九十歲老人,也許會喜歡白塔裡的日子,可以很好地探索人生活這麼長到底為什麼?
可對花季少年來說,這就像把一株生意盎然的幼苗,從肥沃的土壤中、燦爛的陽光下挖出來,種進了溫室的保麗龍箱裡。
恆溫恆濕養分充足,但就是很無聊。
以前何思聽馮艾保以調笑的語氣抱怨白塔裡的生活時,沒什麼深刻的感受,畢竟馮艾保這人對無聊的閾值低到令人髮指的地步。想想,他都能從打在天空的警戒燈中感受到無聊了。
如今生平頭一遭走入白塔,何思才理解到馮艾保那些話的意思。
與其說無聊吧,不如說壓抑。
和外觀一致,白塔內部也是雪白的,牆面材質與外牆相同,並沒有刷任何油漆或貼壁紙,一丁點的裝飾都沒有,走廊與天花板的情況類似,差別在於走廊上有鋪地毯,只不過也是白色的。
也不知怎麼做到的,這種白並不刺眼,而是散發著淡淡的喑啞光暈,高度的柔和與安撫性,就是何思這種S級精神力的嚮導走進來,都有種立刻卸防的放鬆感。
然而,這種沒來由的放鬆感很快就會觸發人類天生的預警系統,精神會立刻緊繃起來,卻偏偏找不到任何具威脅性的事物,彷彿對著空氣揮刀一般,很快就會進入疲憊狀態。
反覆幾次後,五感跟精神都會受到嚴重的消耗,索性放空一切暫停思考與感知,任由白塔的寧靜包裹住自己。
難怪那些鑑識人員與警務人員的神態會那麼奇怪,看來是白塔內部環境造成的。
「如何?」馮艾保大概是所有人裡受到影響最小的,畢竟他在塔中住了八年,早就習慣了如何應付,現在還有閒情逸致回頭調笑何思。「是不是覺得這個世界好溫柔、好舒適、好無聊啊?」
何思懶得回話,他的精神力特別強,所以消耗也特別嚴重,只對馮艾保翻了個白眼。
兩人在外頭就已經聽員警說過屍體所在的位置了,馮艾保當時吹了聲口哨,沒多問什麼直接撩了警戒線就往裡面走,何思只得快步跟上。
白塔內的路線很單純,約略呈現一個井字型,他們的目的地在位於左上的那個大禮堂。
通向禮堂的大門是整座白塔中唯一的顏色,淺淺的暖黃色,令人精神一振,腦袋都清醒了許多。
大門左右敞開著,整個禮堂約莫有五十坪大小,牆面也是暖黃色的,地面則是象牙白地毯,從牆面上及空間中的布置來看,原本應該是一場宴會或派對。有飲料吧、取餐檯、適合聚餐的圓桌與舒適的椅子,不知道藏在哪裡的音響還在運作中,輕柔活潑的音樂流淌在整個空間。
看得出當初是精心布置的,彩帶的顏色選用、桌椅的色彩樣式、掛在天花板上亮晶晶的彩球,有一顆已經被拉開了,底下飄散著五彩繽紛的紙花。
這些紙花只剩寥寥幾朵,其餘的都被踩得破破爛爛,四散到各處去了。
現場到處是證物標示牌、攝影輔助錐體或照片尺度膠貼,桌椅多半都不在原本擺放好的位置了,應該是學生逃離時推撞的結果,地上還有被踩踏過的食物與飲料殘漬,可以想像當時現場有多混亂。
而這一片混亂的中心卻異常的整齊乾淨。
馮艾保沒有立刻上前,他搔搔鼻尖,用手摸了摸下嘴唇,接著伸舌輕舔了兩下。
何思立刻用精神力觸手安撫他。「忍忍,現場不能抽菸。」
「我知道。」馮艾保不再嘻皮笑臉,他又揉了揉人中部分,深深吸了口氣。「上前看看。」
他們走近整個大禮堂中,唯一沒有被腳印混亂的踩踏,甚至沒有紙花碎片的地方。
那裡乾淨、冷漠、沉寂。躺著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
兩人都穿著禮服,少年穿著燕尾服,黑色的布料合身立體,緊緊包裹著青年人柔軟充滿韌性的肢體,腳上的皮鞋擦得鋥亮,但似乎稍微有些不合腳;少女倒沒穿得那麼正式,而是件雞尾酒小禮服,緞面銀黑色,沒有過多的裝飾與剪裁,合身的包裹著女性凹凸有致的軀體,一雙修長的腿裸露著,並沒有穿上絲襪,蹬著一雙黑色簡約的高跟鞋。
馮艾保蹲下,戴上了手套,小心地撩開少女臉上的髮絲。
少女安安靜靜躺著,臉上的神情出人意料的恬靜安寧,彷彿只是睡過去了,就這麼一睡不起。
她身邊的少年也是相同的狀況,姿態放鬆,神情甚至說得上安詳,身上沒有可見的外傷,衣物都是整齊的,沒有絲毫破損。
馮艾保回頭看了眼何思,兩人交換了個眼神後,同時找尋起應該還在現場的鑑識法醫。
很快他們就在大禮堂裡音樂聲最大的角落找到鑑識法醫,他是個中年男人,端正的臉上架個粗黑框眼鏡,遮擋不住神情的疲憊,似乎本來是在閉目養神的。
「找我?」他對兩人揮揮手。
「想你了。」馮艾保眨眨眼笑回。
見到他依然充滿活力的模樣,法醫露出苦笑。他也是個哨兵,而且是不喜歡白塔的那種哨兵,進來之後用不了幾秒就成為一隻離水金魚,垂死掙扎著驗完基礎屍體狀況後,乾脆地癱著張著嘴等死。
「怎麼不先回去?」何思作為安撫哨兵的嚮導,自然而然用自己的精神力打算安撫法醫,但很快就受挫,被白塔的特殊性搞得自己難掩疲態。
「我猜你們會想問我問題,所以乾脆留下來等。」法醫通常驗完屍就走,他的主戰場畢竟不在犯罪現場,而是驗屍房。今天,或許是因為同情躺在那兒的兩個年輕男女,也或許是想到曾經的自己,所以就留下來了。
「怎麼了?想起當年的畢業舞會?」馮艾保自然猜到了法醫的想法。
白塔裡住的都是年輕哨兵,從特徵開始明確顯現之後,就會被送到白塔集中生活並接受教育。
平日的生活就是在白茫茫的塔裡,過著沉悶的日子,基於哨兵的生理特性,他們年幼時生理機能尚未發育成熟,並無法很好地控制自己,五感敏感又過度脆弱,在普通環境裡幾乎生存不下去。
在所謂的「外部世界」,他們不是因為高度敏銳的五感搞到精神耗弱瘋掉,就是因為刺激過度直接受到永久性的傷害,比如失聰失明失智啥的。
白塔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護哨兵,這也是為什麼裡頭的一切都是舒緩單調的,喑啞的白光、隱隱約約的柔緩白噪音、簡單的布局與陳設,以及那不知名卻能有效舒緩精神到直接讓人腦子空洞的特殊氣氛。
每年只有一天,這個用馮艾保的說法是「沉靜得跟墳墓一樣的地方」,才會出現一絲鮮活的氣息。
也就是無數年輕哨兵心心念念的成年禮暨畢業舞會。
顧名思義,這是只有即將畢業的新成年哨兵才有資格參加的盛會,年紀小的哨兵這一天反而是更受壓抑的日子,他們會被拘束在自己的小房間裡,避免過度感知到畢業舞會的音樂與歡鬧聲。
這也是為什麼,身為哨兵的法醫會與死去的兩個年輕哨兵有共鳴的原因。原本,成年禮或說畢業舞會都是讓人最歡樂、最期待的日子,代表著人生將步入新的篇章,充滿著希望與光明,更別說被鎖在白塔裡的這些孩子了。
他們忍受了八到十年不等的拘禁,其中一部分也許會留戀也認同這樣的拘束,大部分則是幽魂般逆來順受,而有極小的一部分痛恨這種監禁般的生活,恨不得立刻長翅膀飛走。
但無論哪一種,不可否認都對能離開白塔充滿了憧憬。
從整個大禮堂的布置就能看出,年輕哨兵們對這次的活動期盼有多深,像是終於找到了自己脖子上鎖鏈鑰匙的金絲雀,歡快得幾乎喪失理智,卻又小心翼翼地深怕走錯一步會導致全盤皆輸。
他們挑選溫柔的粉嫩色彩,謹慎地不刺激自己長年被雪白占據的視覺神經;挑選最柔和舒緩的音樂,也許加上一點小小的刺激,流行曲還不行,但古典樂似乎不錯,可以挑選一些活潑的曲調,也適合跳舞;食物也要調味溫和的,炸的東西還不適合,但烤跟煎的食物也許能嘗試看看,放些調味料的罐子在食物旁,大家可以斟酌著添加滋味,才不會一口氣傷害了長年吃著寡淡水煮菜餚的味蕾……諸如此類。
這種小心翼翼試探世界的心情,馮艾保跟中年法醫都經歷過,相信躺在地上失去生命的兩人也經歷過,再五天就能離開白塔了……再五天。
他們被永遠留下來了。
「所以對死因有大致的推測嗎?」馮艾保問,他不是個會過度陷於感傷裡的人,扣除哨兵這個特殊身分,他以前也不是沒經手過前景光明的年輕人橫死的案件,彼此之間並無不同。
「目前看起來是心搏停止導致的心因性猝死。」法醫回答:「暫時沒看到任何外傷,屍體還很柔軟,肢體末梢有輕微發紺現象,代表有缺氧症狀,但持續不久,很快就死亡了。」
「就沒人發現他們狀況有異常嗎?」何思忍不住問,哨兵的五感有時候比精密儀器還要敏銳,任何一丁點異狀都逃不過他們的感官。照理說,整個大禮堂裡都是哨兵,簡直跟布滿雷達沒兩樣。
試想,一個十平方公尺的屋子裡,窩著二十來隻貓,這時候有隻小老鼠想從牆洞鑽出來偷乳酪,這都不是寸步難行了,而是光一根鬍鬚探出牆洞,就會立刻被貓咪用爪子拎出來吞掉。
現在的大禮堂差不多就是這種狀態,理論上任何蛛絲馬跡都藏不住才對。
「不,今天狀況特殊。」馮艾保與法醫異口同聲道。兩人互看了一眼,法醫抬了下手,把說話機會讓給年輕人,他繼續當張著嘴等死的金魚。
馮艾保同情地拍了拍法醫的肩膀,這才接著對搭檔說:「對我和學長來說,這個大禮堂沒有什麼過度的刺激源,比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平緩許多,與白塔其他區域幾乎沒有差別。但你想想,今天聚集在這裡的孩子,都經歷了八到十年的極端無聊生活,他們眼裡除了白色、耳中除了白噪音外,什麼都沒有,這場舞會的色彩與音響,對他們來說已經超過刺激上限了。」
簡單來說,如果今天有個失明許久的人,突然恢復了視覺,當他看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就會有過多的色彩跟資訊一口氣湧入,導致他無法分辨哪些訊息是重要的,哪些訊息是次要的,哪些訊息是正常的,又有哪些訊息是異常的。
既然無法分辨,那所有的訊息與情報都是等重的,也就更沒有精力去發現那些隱藏在常態訊息下的細節。
「所以,即使有接近兩百人在場,但大概一個可用的目擊證人都沒有。」馮艾保語氣輕鬆地下結論,法醫與何思卻同時嘆了口氣。
沒有什麼比這個現實更令人沮喪了。普通犯罪現場還能找到些監視攝影器,尤其是學校這種地方,監視器的數量會更密集些,偏偏白塔環境特殊,是沒有監視器的,就算有外部人士,或者有人動了手腳,也無從得知了。
「好吧,我繼續留在這裡也沒用了……」法醫摘下眼鏡捏了捏鼻梁,戴上眼鏡後又深深嘆了一口氣。「其實,我更傾向這兩個孩子是承受過度刺激導致心因性猝死,就是一場意外。」
| FindBook |
有 6 項符合
貓與老鼠從來都是相愛相殺的關係(1)的圖書 |
 |
貓與老鼠從來都是相愛相殺的關係(1) 作者:黑蛋白 出版社: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07-28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型式 | 價格 | 供應商 | 所屬目錄 | 二手書 |
$ 206 |
二手中文書 |
電子書 |
$ 210 |
BL |
$ 221 |
華文 |
$ 221 |
文學作品 |
$ 221 |
華文BL/GL |
$ 260 |
中文書 |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貓與老鼠從來都是相愛相殺的關係(1)
在哨兵與嚮導的世界裡,精神體代表了一個人的本質。馮艾保是個特別的哨兵,他五感過度敏銳,體質也極度強壯,特別是神經更是強悍到連嚮導都嘆為觀止的地步。他的特別也展現在精神體上──據說他沒有精神體。身為中央警察署重案組的王牌刑警,當馮艾保聽到自己搭檔要退休的消息後陷入哀傷中,直到他看到了那個有著俄羅斯藍貓精神體的小嚮導,那隻貓高傲的肉墊下踩著自己的黃金鼠精神體──他的下體瞬間就不合時宜了起來。
在各種挑戰人性的案件中,貓咪與老鼠跳起愛與殺意的圓舞曲。
本書特色
★2022KadoKado百萬小說創作大賞BL小說組金賞!
★風騷精神力強悍哨兵攻X外冷內不算熱3S精神力嚮導受
★我需要你,你願不願意跟我去測試匹配度?
★詭譎獵奇的殺人案接二連三發生,人性深處的癲狂正逐漸顯露……
【首刷限定】
1.Q版印刷簽名明信片X1
2.精美票卡貼X1
3.特典漫畫1P
4.「KadoKado角角者」閱讀金50角點
(※首刷售完即無贈品)
作者簡介:
黑蛋白
曾經在《靈書妙探》這部美劇裡看到一段台詞「只有偵探小說家跟殺人犯才會每天思考怎麼殺人」。回頭看看自己最近的寫作資料夾,是完全不能被別人看到的啊!一堆毒藥跟病理解剖報告啥的,更重要的是一~~大堆的殺人計畫書……自己在電腦前瑟瑟發抖啊……
插畫
嵐星人
2D美術社畜兼鉛字中毒者,吸食VT切片熟肉打起精神。哨兵嚮導喜歡有動物精神體可以吸,如果自己有精神體希望是喜馬拉雅小熊貓,單純為了擼毛。
章節試閱
第一章 塔裡的睡美人與她的王子
城市的一隅拉起了黃色警戒線。
馮艾保臉上戴著遮住半張臉的墨鏡,斜倚在車旁。紅色警戒燈光一閃一閃從他臉上掃過,帶起他嘴唇邊的一絲淺笑。
他伸手在車頂上用力拍了拍,接著彎下身從車窗往裡看,對還在車子裡與總部交談的搭檔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
「你看。」他指指被調高的警戒燈,頻率也被調低了,每隔約半分鐘才會在深色的天空上閃過一道紅光。
何思掛上電話,探頭順著馮艾保的手指看去,很捧場地笑笑。「第一次看到?」
「你說呢?」馮艾保哈哈一聲,反問回去,順手拉開了車門。「快下來,帶你...
城市的一隅拉起了黃色警戒線。
馮艾保臉上戴著遮住半張臉的墨鏡,斜倚在車旁。紅色警戒燈光一閃一閃從他臉上掃過,帶起他嘴唇邊的一絲淺笑。
他伸手在車頂上用力拍了拍,接著彎下身從車窗往裡看,對還在車子裡與總部交談的搭檔露出一個大大的笑容。
「你看。」他指指被調高的警戒燈,頻率也被調低了,每隔約半分鐘才會在深色的天空上閃過一道紅光。
何思掛上電話,探頭順著馮艾保的手指看去,很捧場地笑笑。「第一次看到?」
「你說呢?」馮艾保哈哈一聲,反問回去,順手拉開了車門。「快下來,帶你...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