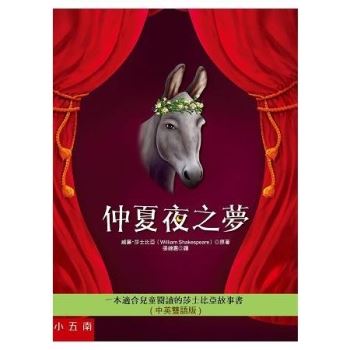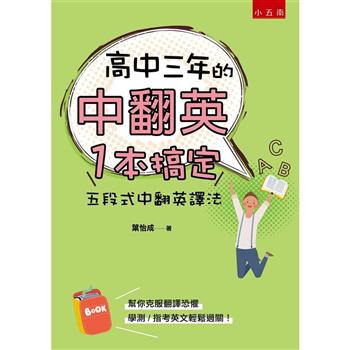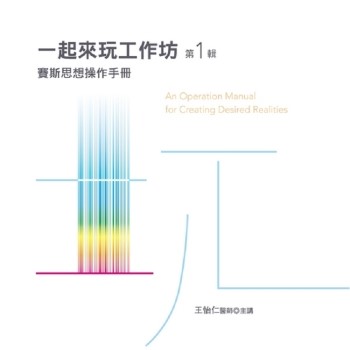序章 素未謀面的妻子捎來的一封信
蓋罕達帝國南部戰線的駐紮地,位於一片看似綿延不絕的平緩丘陵地帶。一望無際的平原拂來有些乾燥的風,讓矮短的草隨之搖擺。眼前翠綠茂盛的草,是地處遙遙北方的帝都鮮少看見的種類。然而,這已成了熟悉的日常風景。
──八年。
這既是與鄰國戰爭所經歷的歲月,也是這個男人離開帝都的時間。
更是與跨越國境而來的敵軍隔著平原對峙的年月。
這場漫長的戰爭,總算締結了停戰協定。消息轉眼間就傳遍了整個帝國。
此時,一封信送至還在處理後續工作的駐紮地。
不同於草原地帶特有的溫暖氣候,這封從帝都捎來的信件似乎散發出一縷冷風,讓人回想起環繞聳立在都城周圍、被白雪覆蓋的米特爾山群景色。
「真難得有家人寫信給你耶。」
在軍幕裡看信的安納爾德.斯瓦崗抬起頭來,看向隔著桌子坐在對面那位同為中校的友人。細長的祖母綠眼給人淡漠的印象,與那白瓷般的肌膚很相襯。儘管曾有情書送到這位出名俊美的中校手中,戰時也從來沒有血親寄信給他。大致瀏覽這封在一宣告戰爭結束就收到的信件後,安納爾德的嘴角微微揚起。
他就這麼將信件交到友人手中。
「怎麼,信中寫了多麼有趣的事情嗎?」
對於安納爾德默默遞過來信件產生興趣的友人,懷著看戲般的心情讀了下去,表情卻隨之大變。
「喂,這狀況容不得你這麼悠哉了吧……!」
看著友人驚慌失措的反應,安納爾德撫著下巴沉思。就像在擬定作戰時一樣,那雙機敏的眼中寄宿著殘忍的目光。
擅於將敵軍逼到絕境,並設下陷阱圍攻,再加上安納爾德的一頭灰髮,讓他被稱為「戰場上的灰狐」。然而,接下來應該是要望向政敵的那道眼神,不知為何卻注視著這封信的寄件人,也就是他的妻子。
戰爭結束了,這封信卻像是捎來一場新的紛爭一樣。
如果是個能讓自己極盡所能謀略的對手就更令人開心,可惜透過信件只能窺知一二。不過正因為未知,新的戰場才教人不禁雀躍。
「先不論她有何意圖,思考要如何將對手逼到絕境,多少還是能打發點時間。」
「喂喂喂,再怎麼說也是你自己的妻子吧。」
聽見友人傻眼的反應,他只是暗忖著「面對像在下戰帖一樣捎來這封信件的人,有必要寬容嗎?」這樣的疑問。
信件上以秀氣的字跡,慎重地寫下一字一句,而且還用刻有斯瓦崗伯爵家家徽的封蠟緊緊封上。信上也有父親的署名,這就代表父親也知道這件事吧?
更重要的是,藉此得知對方是認真的,讓他忍不住湧上笑意。
遙想著儘管未曾謀面,但多少耳聞了一些傳言的妻子,安納爾德反覆思量著信件內容。
那封信劈頭就寫著「致未曾謀面的丈夫」這般挑釁意味濃厚的句子。
致 未曾謀面的丈夫
耳聞與鄰國締結了停戰協定,實質上戰爭已迎來終結。然而與您成婚這八年來,別說連一封信都沒有,彼此甚至從未謀面,我這妻子可說是徒具虛名。
請務必趁著這次機會,同意我們離婚。
您未曾面識的妻子 敬上
第一章 賭注與時隔八年的初夜
時間回溯到八年前──
蓋罕達帝國的帝都位於大陸北方。名為米特爾山群的山脈環繞般聳立在都城周圍,作為天然要塞守護著帝都,也可說是守護著帝國。利用群山之間相對平緩的地形進行開拓的帝都,到了冬天總是十分寒冷,人們通常都是窩在家中,並在備有暖爐的溫暖房間裡生活。
坐落於帝都貴族區的霍洛特子爵家也一樣。一家四口在晚餐過後,會各自在事先讓人溫暖好的房間裡悠哉地度過夜晚──換作平常,皆是如此。
顧不著子爵家中的走廊既冰冷又昏暗,勢頭猛烈、一路快步走來的拜蕾塔,一打開與客廳相通的門就厲聲道:
「父親大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在裡面喝著餐後茶的雙親,對於女兒怒氣沖沖的態度並沒有感到任何動搖,只是回過頭並不約而同嘆了一口氣。
「妳講話總是這麼大聲。妙齡少女可不能擺出這種態度喔,拜蕾塔。」
「母親大人,要責罵請晚點再說!我聽兄長大人說了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那是真的嗎?」
「既然妳都聽說了,就是那樣。伯爵家來提親了。對方可是出自繼承舊帝國貴族血脈的家世喔,這是何等榮耀啊!妳看過對方的肖像畫了嗎,好一個俊美的男人對吧?」
所謂舊帝國貴族,是指早在蓋罕達帝國以前的時代就受命貴族爵位,有著悠久歷史的家世,而那對象正是繼承了這樣血脈之人──但這跟現在的自己一點關係也沒有。那種東西遑論榮光,根本毫無價值,說難聽點甚至還很棘手。
「那種東西早就在暖爐裡被燒得一點形體都不剩了。我之前不就說過不會嫁給任何人嗎!」
「看也沒看就扔掉了是吧……妳不嫁人這種事,我怎麼可能答應啊。霍洛特子爵家代代都是騎士,妳既然繼承了這樣的血脈,就不能愧對家族的功勳,好好嫁一個軍人吧!對方是陸軍少校,在這次的戰役中還會成為中校,是一位相當出色的人物。二十五歲這年紀是跟妳有些差距,但要管得住妳……還是要說懷柔呢……應該說是要能馴服妳?總之,以要跟妳結婚的對象來說,這年紀應該差不多。」
「請不要一再重提這話題。況且,我們家說是騎士,其實也只是鄉下地方的地痞靠著武力得到爵位而已──那還頂多是六代以前的事情,本來不過是平民罷了。既然是那麼出色的人物,應該沒必要娶我們這種家世的女兒吧?」
「妳動不動就這樣瞧不起我們家族,我們代代相傳的騎士血統是何等優異──」
「父親大人的自吹自擂一點也不重要,我現在想問的是,為什麼對象是我呢?」
「對方說了非妳不可啊。」
「地位、名聲都不缺的伯爵家,怎麼可能會直接找上我。是透過哪一位介紹的?」
「呃~……」
直到剛才還滔滔地說個不停的父親,一瞬間尷尬地搔了搔臉頰。這是父親在想謊言時會有的小動作,拜蕾塔的目光因此變得越來越銳利。
有著遺傳自母親猶如月之女神般的美貌,好勝的少女散發出強烈意志的紫晶色雙眼,寄宿了熊熊燃燒的火焰。
她撩起那頭莓果粉金的長髮,狠狠地瞪向父親。
「父親大人,這該不會是德雷斯蘭中將閣下的意思吧?」
身為帝國陸軍上校的父親在大約十五年前率兵前往北部戰線時,受到時任師團長的莫弗利.德雷斯蘭中將賞識,兩人更成了朋友。如果只是老朋友,家人也不會多麼擔心,然而莫弗利是個出名的花花公子,酗酒、賭博、玩女人樣樣都來,實在難以想像為什麼會跟個性認真又耿直的父親合得來。而且只要被帶去賭博,總是會花掉一大筆驚人的費用才回家。
這可謂我們家眼下最頭痛的問題,將德雷斯蘭中將形容為惡魔之子都不為過。
將父親的沉默視為肯定的拜蕾塔,雙手使勁地拍在桌子上。茶器跟著發出鏗鏘聲,但誰要在乎這種事啊!
「父親大人,你是認真的嗎!到底是因為怎樣的理由,才會讓你萌生要將自己剛滿十六歲的可愛女兒嫁出去的想法?」
「唉,有辦法堂而皇之地說自己是『可愛女兒』的妳,想必沒問題的。」
索性豁出去的父親將手中的茶杯放回桌上,以平靜的目光注視著她。
「確實一如妳的猜測,這樁婚事是德雷斯蘭中將閣下介紹的,好像是他疼愛的部下想討個老婆。這次,在南部戰線可能會打上一場長期戰爭對吧?所以就算只能先留下短暫的回憶也好,中將閣下說想替他添個可愛的新嫁娘。」
「就可愛這點我確實是全面同意。然而竟然受到閣下的疼愛,對方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危險人物?事情肯定不是只有幫他找個可愛的新嫁娘這麼簡單吧?」
「妳到底是哪來這樣的自信啊?為父都覺得有點擔心了……不過,其實對方開出來的條件是想找個有骨氣、有膽識,而且具備強悍實力,性別姑且算是女性的對象──然而,鮮少有這樣的女性,對吧?此時聽聞妳在學生時期的謠傳後,閣下就選中妳了。」
所謂的「學生時期」,應該是指在去年畢業的史塔西亞高等學院中所發生的事吧?自己確實度過了一段難以稱之平凡的校園生活,也曾引發動刀傷人的爭執事件……應該是因此被認為有膽識吧?
再次體認到莫弗利這個男人看待事情的觀點果然莫名其妙。
「完全沒有提及可愛的要素耶。」
「說真的,外貌並不在他的條件當中,他只求膽量跟實力。」
「這是要去踢館的條件吧!」
「哈哈哈,這可是妳這樁婚事的條件,真不愧是以武功揚名的霍洛特家女兒呢!」
拜蕾塔對著快活地笑了起來的父親展露一抹微笑。
「原來如此。看來父親大人希望當場讓身體與雙腳分家呢。」
「等等、等等、等等!妳的眼神也太認真了。」
「哎呀呀,我可是個性既耿直又認真的父親的女兒。最討厭說謊跟開玩笑了。」
發出「呵呵呵」的乾笑之後,父親頓時臉色蒼白。
「竟然能實現父親大人的願望,我實在高興到都快喜極而泣了。」
一拿起掛在牆上明晃晃的劍,就緩緩揮下。父親也敏捷地抓起裝飾在牆上另一把劍,並立刻應戰。
客廳頓時響起刀劍碰撞時,沉重的鏗鏘聲響。
「妳就是這樣才會都沒有人來提親,竟然從還在念書時就做起什麼生意!甚至在社交界傳出一堆不好的名聲,是要被人瞧不起到什麼程度啊?女人有女人的幸福。能這麼快就解決妳的婚事才好吧!」
「所以說,我要成為商人活下去啊。我已經都說過那麼多次了,就是不想嫁人。」
「我也說過,不容許妳這麼做吧!」
父女倆揮舞著長劍,在客廳一隅對打起來的時候,母親則是悠哉地喝完杯中的茶。
在那之後,無論拜蕾塔怎麼抗議也沒用,結婚的準備一步步進行下去。難以置信的是,兩個月後就迎來婚禮的日子。
無論怎麼反抗、威脅、脫逃都沒辦法撤回這項婚事,拜蕾塔也只能下定決心了。決定要直接跟對方當面談判的她,被半強迫地塞進伯爵家準備的豪華馬車裡。身穿新娘禮服,與一同搭乘的父親一起搖晃了一小段路程。
兩人抵達的宅邸坐落於帝都的中心。與子爵家蓋在郊區的小巧住家相比可說大相逕庭,讓他們感到驚訝不已。
眼前是一片深宅大院。竟然要嫁到這種地方來,真教人難以置信。感覺就像被誆騙了一樣。不愧是繼承舊帝國貴族血脈的悠久家世,自家門第實在難以望其項背。
在父親的帶領下,一進到宅邸內,傭人們全都出來迎接。順著他們的指引來到會客廳,只見斯瓦崗伯爵家宗主瓦納魯多.斯瓦崗就在裡頭等著他們到來。
伯爵年約五十幾歲吧,一頭褐髮之間開始長出斑駁的白髮,身軀卻依然魁梧。然而,那雙水藍色的眼睛卻顯得混濁,給人一種頹喪的感覺。儘管拜蕾塔對此感到有些奇怪,她的注意力卻很快就投向其他地方。
坐在宗主身旁的女性臉色相當不好,那是位將一頭豔麗金髮盤起來的年輕女性。大概才三十幾歲而已,卻一副疲憊不堪的模樣,怎麼看都不像有個二十五歲的兒子,應該是續弦。雖說她給人空靈的感覺,然而那副看了就令人心疼的樣子,讓拜蕾塔不知不覺間皺起眉頭。
拜蕾塔之所以會像這樣,觀察並非自己結婚對象的人,是因為現場不見這位最重要對象的身影。難道是為了換上新郎禮服而拖延、遲到了嗎?總之,現場只有自己穿著新娘禮服,感覺相當格格不入。
不過,這個疑問立刻就得到了解答。
「很可惜的,吾兒昨天就出發前往戰場了。戰況似乎不太理想,在名義上妳已經是伯爵家的媳婦了,婚禮就等到他回來之後再說吧。總之,那個可恨的兒子升遷之後,就這麼出征去了。」
「伯爵大人,請問這是怎麼回事?」
「你們沒聽說嗎?只要結婚就能升遷,所以他二話不說就答應了。他說妻子來了之後,只要讓她隨便在宅邸裡生活就好。」
父親應該是第一次聽說這件事吧。確實有耳聞對方的軍階會升到中校,但他肯定不曉得條件是要和拜蕾塔結婚。只見他頓時語塞,臉色沉了下來。
然而在這樣的父親身旁,拜蕾塔換了個想法,如果是當丈夫不在的期間,身處妻子的立場也不錯。既不會被丈夫這種沒用的東西束縛,也不會被家人逼著結婚,這樣的生活豈不是滿快活的?
如果丈夫從戰場上回來了,到時候只要趕緊逃走就好。幸好丈夫對自己似乎也不感興趣的樣子,肯定會很乾脆就答應離婚。而且除了丈夫之外,這個家也有讓拜蕾塔深感興趣的事情──那就是從剛才開始就一直低著頭,從未開口的婆婆。
瓦納魯多並沒有特別關心坐在身旁的她,並繼續說道:
「不過,老夫身為宗主,沒必要聽從那傢伙所說的話。既然現在最重要的丈夫也不在,妳想回去子爵家生活也沒關係,如何?」
以隨便的語氣拋來的問題,讓拜蕾塔緩緩眨了眨眼。
「拜蕾塔,這次真的是我不好,若想回來家裡也沒問題!」
「不,父親大人,我想就此在這裡生活。畢竟丈夫也都這麼說了。」
投以一道銳利的視線之後,父親也察覺到拜蕾塔的意志,而點了點頭。他應該是理解這個家有某些地方觸動了注重仁義與人情的女兒的心弦吧。
就這樣,拜蕾塔成為斯瓦崗伯爵家的一員。
結果,父親滿懷擔憂地回去了。既然沒有要舉辦婚禮,留在這裡也不是辦法,就這麼像被伯爵趕走一般離去。
雖然說了「還會再過來看看」,但父親這次預計也要上戰場,不過因為是後勤支援部隊,才比較晚被召集而已。拜蕾塔並沒有要上戰場,因此處境肯定遠比父親更加安全。畢竟再怎麼說,也不至於在夫家喪命。她不禁覺得,比起女兒,父親還是先顧好自己吧。
拜蕾塔說著希望父親能平安無事,卻得到父親回覆「身為帝國軍人,無論面對任何狀況都該勇猛果敢地踏上戰場」,這番一如往常認真到不行的話。儘管想頂上一句「不要一股腦衝上前去結果落敗就好」,拜蕾塔還是把話吞回了肚子裡。
雖然結婚對象跟瓦納魯多的態度都很不好,但姑且還是有為自己準備了房間。在傭人的帶路下,來到一個寬敞單間,從今以後就是拜蕾塔的房間。從家裡帶來的一點行囊,傭人都已整理妥當,拜蕾塔也只能待在安靜的房間裡發呆。眼前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做。就算想採取行動,資訊也遠遠不足。
結果,直到被叫去吃晚餐之前,拜蕾塔都在房間的躺椅上,反覆回想著白天時與父親的互動。
在幾乎教人喘不過氣的緊繃氣氛中吃著晚餐時,餐廳裡鏗鏘地響起碗盤破碎的刺耳聲響。
晚餐時,在伯爵家餐廳長桌就坐的有四個人,包括伯爵夫婦及一位小女孩。她是今年才剛滿六歲的米蕾娜。也就是拜蕾塔的小姑。
有著遺傳自母親的一頭金髮,以及傳承父親水藍色雙眼的女孩,感覺很害怕般、畏畏縮縮地做了自我介紹。這樣的舉動以她的年紀來說相當成熟,就算跟拜蕾塔相比,也顯得格外文靜;與其說她怕生,更像在害怕著什麼似的。這也讓拜蕾塔慶幸自己有留在這裡,不只是婆婆芯希雅,連小姑都深受其害,著實不可原諒。
拜蕾塔輕而易舉就推測出元凶正是將餐具摔在地上的那個男人。
「吵死了,少囉嗦!連妳都要對我頤指氣使嗎!」
瓦納魯多會這麼生氣,不過是因為芯希雅一句「老爺你酒喝太多了」的勸誡而已。然而,這似乎點燃了他的怒火。公公力道強勁地甩了婆婆一巴掌,從她腫起的臉頰看來,嘴巴裡應該也受傷了。白皙的肌膚泛起了紅印,看了就讓人心疼。
然而,無論待在餐廳裡的管家、服侍用餐的男傭及女僕,任誰都沒有要上前阻止宗主的暴行。
他們都盡可能不表現出任何反應,只是屏住氣息地在一旁看著。
「那個笨兒子都離開帝都了,我隨心所欲一下又怎麼樣?」
眼看男人又舉起手來要再次施暴的樣子,拜蕾塔連忙上前輕輕抓住他的手。
「竟然對自己應當守護的婦孺出手,儘管退役了,您這樣還能算是個帝國軍人嗎?」
伯爵是退役軍人,在戰爭中罹患肺病成了傷兵,聽聞從此就窩在宅邸裡專注於管理領地。但總覺得事有蹊蹺。斯瓦崗伯爵擁有領地,而且聽說管理得很順遂,似乎也沒有大筆欠債;然而從公公這副德性看來,實在難以想像。
不過,管理領地的事情可以往後再調查,現在還是以壓制住眼前這個男人為優先。
「妳這是在做什麼!」
「我才想這麼問呢,父親大人。看來您真的喝了不少。母親大人也都這麼說了,就請別再喝了吧。」
「吵死了,區區子爵家的小丫頭竟膽敢指使老夫!不過是個虛有其名、被丈夫拋棄的妻子,擺什麼大架子!」
「哎呀,父親大人,這話說起來可真是矛盾呢!我是個小丫頭,骨架子自然也小啊。」
拜蕾塔揚起「呵呵呵」的乾笑聲之後,氣得臉紅脖子粗的公公噴著口水怒吼道:
「少搬弄那種歪理了!還不快點放手!」
「堂堂的退役帝國軍人,竟說這種奇怪的話。難道您已經醉到連一個柔弱丫頭的力道都甩不開了嗎?真令人傻眼呢。」
「妳這混帳東西,給我過來,馬上就讓妳成為我劍下亡魂!」
「老、老爺……請別這樣!」
芯希雅連忙攀住怒氣沖沖的瓦納魯多,那溫柔的本性令人動容。
哪像拜蕾塔的母親,根本不會把吵起來的父女倆放在眼裡。由於早就司空見慣了,別說上前阻止,她甚至懶得開口勸阻。
「面對一個小丫頭也毫不留情啊……不過,或許這樣能讓您體認到自己喝到多醉了吧!」
「什麼!」
「我接受您的挑戰,到那邊的屋簷下就可以了嗎?」
除了公公以外,拜蕾塔的一番話讓在場所有人都不禁倒抽了一口氣。
移動腳步,在吊燈的燈光照耀下,先走到餐廳外屋簷下的公公瞇細了雙眼。
「妳就穿這樣嗎?」
新娘禮服當然已經換下來了,但拜蕾塔依然穿著略顯華美的禮服。那是一件裙襬寬鬆的洋裝。順帶一提,伯爵家完全沒有替她準備平時要穿的衣物,這是自己帶來的。
這是父母祝賀拜蕾塔結婚所贈送的禮服,總不能染上血汙。他們表示畢竟是要嫁到伯爵家,因此似乎挑選了十分昂貴的布料,因此也不能為了清掉血漬而用力搓洗。
父母說不定是事先預料到、為了避免發生這種事情,才會送上這件洋裝。但簡單來說只要別弄髒,俐落地擊倒對方就好了。
「當然,就算輸了我也不會拿穿著裙子當藉口。而且,我已經習慣了。」
「哼,囂張的小丫頭!我看妳應該是有兩把刷子才膽敢挑戰老夫,但終究橫豎只是小丫頭在耍耍劍而已!一個小女孩竟想做什麼反抗,乖乖聽話不就沒事了?老夫這就讓妳再也不敢強詞奪理!」
氣到抓狂的他,似乎不曉得拜蕾塔這樁婚事的條件。而且他跟兒子之間的關係好像很不好,應該也難以想像會有符合那種踢館般條件的新娘吧?如果他認為自己的程度不過是千金小姐的花拳繡腿,那正好,畢竟自負正是最大的破綻。
「父親大人才是,請別說出因為酩酊大醉而拿不穩長劍這種藉口喔!」
「哈哈哈!妳說話真有趣啊,小丫頭。竟然想贏過老夫嗎……哼,要是真的被妳打敗,不管妳有任何要求,老夫都能答應!」
打從一開始,拜蕾塔只是想懇請瓦納魯多不要喝到爛醉而已,但看樣子,事情好像鬧大了起來。既然他說任何要求都可以,那確實有一件希望他答應的事情。
當拜蕾塔這麼沉思時,公公無所畏懼地笑了。
「前提是妳要能打敗老夫再說。這就將妳送上黃泉,為自己侮辱退役軍人懊悔一番!」
他好像完全沒有要手下留情的意思。既然都說要送上黃泉了,公公應該將以會確實殺害自己的氣勢攻過來吧。
伴隨著這句話,他就架好真劍,迎面揮下。拜蕾塔也舉起自己的劍接下攻擊,並將重心側移,化解對方的力道。
即使喝醉了,以拜蕾塔的力量也敵不過男人。先接下攻擊,再化解力道——她不斷反覆這樣的動作;雖然看起來很不起眼,但其實需要相當精湛的技巧。為了學會這樣的招數,更需要經歷長年的修練才行,然而瓦納魯多應該是沒察覺到這一點吧?只見他忿忿地嘖了一聲。
「一味地接下攻擊,妳只會逃嗎?」
「小丫頭有小丫頭的做法呀。」
公公的劍比想像中還要快,但還是比不上身為現任上校的父親,實力甚至不及擔任文官的兄長吧。大概因為喝醉的關係,動作既單純又容易看穿。幾乎可說是憨直了。
拜蕾塔不禁回想起結婚的條件:要有骨氣又有膽識,而且具備強悍實力,性別姑且算是女性的對象。聽了讓人不禁拿踢館來比喻,沒想到還真是如此。
正當思及此而感到有趣時,瓦納魯多的眉頭微微皺起。她並沒有瞧不起公公,但說不定是心情表現出來,結果被誤會了。
交劍的鏗鏘聲響起幾次之後,變得有些粗劣。應該是因為遲遲沒有分出勝負,而讓瓦納魯多感到焦躁了吧。
「妳這混帳!」
「喝啊!」
| FindBook |
有 4 項符合
致未曾謀面的丈夫,我們離婚吧!(上)的圖書 |
 |
致未曾謀面的丈夫,我們離婚吧!(上) 作者:久川航璃 / 譯者:黛西 出版社:台灣角川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3-11-0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致未曾謀面的丈夫,我們離婚吧!(上)
蓋罕達帝國的子爵家千金拜蕾塔,貴為千金小姐的她才華過人,擁有著優秀商業才能及武術實力。除此之外,她還有個結婚八年以來都從未見過面的丈夫——伯爵家長男,傳聞中的美男子,無比冷酷的安納爾德中校。
在戰爭迎來終結之時,拜蕾塔的丈夫也從戰場歸來。面對拜蕾塔想離婚的期望,安納爾德提出了以一個月為限的荒唐「賭注」──
一直被不實謠言傳為「惡女」的拜蕾塔,以及從來沒有愛過人,個性孤高的安納爾德。不擅表達情感的兩人與深陷交錯誤會中的甜蜜戀愛物語,就此揭開序幕!
本書特色
★第六屆KAKUYOMU網路小說「戀愛部門」大賞得主,引爆日本網友絕佳好評!
★冷酷軍人與惡女千金,交織出一場深陷交錯誤會中的甜美溺愛羅曼史。
作者簡介:
久川航璃Kouri Hisakawa
以Markov(マルコフ)的名義發表〈致素未謀面的丈夫,我們離婚吧〉,並在第六屆KAKUYOMU(カクヨム)網路小說競賽的「戀愛部門」榮獲大賞殊榮。並在Media Works文庫以久川航璃的名義正式出道。
譯者簡介:
黛西
從書店員到編輯,現在是自由譯者。經手圖文書、實用書、漫畫輕小說及手遊,希望能伴隨文字去看遍更多不同的世界。
聯絡方式:seventhfancy@gmail.com
章節試閱
序章 素未謀面的妻子捎來的一封信
蓋罕達帝國南部戰線的駐紮地,位於一片看似綿延不絕的平緩丘陵地帶。一望無際的平原拂來有些乾燥的風,讓矮短的草隨之搖擺。眼前翠綠茂盛的草,是地處遙遙北方的帝都鮮少看見的種類。然而,這已成了熟悉的日常風景。
──八年。
這既是與鄰國戰爭所經歷的歲月,也是這個男人離開帝都的時間。
更是與跨越國境而來的敵軍隔著平原對峙的年月。
這場漫長的戰爭,總算締結了停戰協定。消息轉眼間就傳遍了整個帝國。
此時,一封信送至還在處理後續工作的駐紮地。
不同於草原地帶特有的溫暖氣候,這封從...
蓋罕達帝國南部戰線的駐紮地,位於一片看似綿延不絕的平緩丘陵地帶。一望無際的平原拂來有些乾燥的風,讓矮短的草隨之搖擺。眼前翠綠茂盛的草,是地處遙遙北方的帝都鮮少看見的種類。然而,這已成了熟悉的日常風景。
──八年。
這既是與鄰國戰爭所經歷的歲月,也是這個男人離開帝都的時間。
更是與跨越國境而來的敵軍隔著平原對峙的年月。
這場漫長的戰爭,總算締結了停戰協定。消息轉眼間就傳遍了整個帝國。
此時,一封信送至還在處理後續工作的駐紮地。
不同於草原地帶特有的溫暖氣候,這封從...
顯示全部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