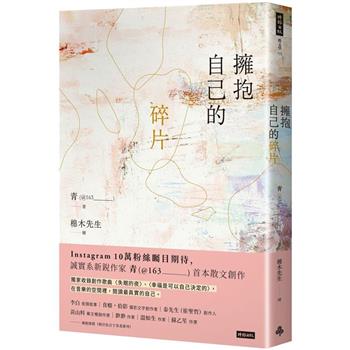智慧始於覺察,對自我和自我以外的世界之覺察;智慧隨著我們對內在的「我」與外部世界的固有張力的覺察增強而加深。
《紐約時報雜誌》邀請我寫一篇關於智慧相關研究的文章時,我開始意識到這一點;那篇文章在那期雜誌封面上的標題是:「科學能告訴我們誰會變得更有智慧嗎?」一如我很快發現,我們不缺智慧的定義,也不缺對這些定義的爭論;在一九九○年出版、書名為《智慧:其本質、起源和發展》(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的學術文集中,十三章分別由多位知名心理學家撰寫,每位提出他們對智慧的不同定義。正如羅伯.史登堡(Robert J. Sternberg)簡要地指出:「充分和正確理解智慧所需要的智慧,可能超出我們任何一個人所擁有的。」
但思考智慧使我們更接近智慧本身。每次我遇到智慧的新定義,或心理學文獻中的相關論點,我都發現我會思考自己的人生:我的各種決定、我的價值觀、我的缺點,以及我面對實務和道德難題時所作的抉擇。如果有心理學家認為情感上不偏不倚是智慧的一個構成要素,我會停下來思考自己的情感行為,例如什麼東西使我情緒激動?當我不得不處理與專業同事之間令人沮喪的情況或我的孩子在不方便的時候提出情感索求時,我作了怎樣的決定──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語氣和肢體語言如何?如果有人認為憐憫是智慧的核心要素,我會被迫思考自身行為的局限和不一致。我閱讀巴爾特斯的著作時,發現他認為處理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是現代智慧的一個核心面向,此時我意識到,面對模糊和不確定的情況往往是我們生活中最大壓力和最困難的事。(這種自我覺察使我想起我以前寫健康醫療相關文章時對疾病的著迷,但這比較像一種哲學形式的疑病症,沒那麼可怕,而且啟發性大得多。)我意識到,每一個新問題都使我不知不覺地展開即興的心理鍛鍊,投入一種非正式的自我覺察健身操。
隨著我比較深入探索關於智慧的文獻,我發現自己每次遇到問題或困境時,都會一再對自己默念這問題:現在最有智慧的做法是什麼?我不會說我行事有智慧──正如巴爾特斯和許多人指出,智慧主要是一種理想的願望,而不是我們常有的一種精神狀態或行為模式。但是,光是以這種方式形塑決策,就足以在知性上和情感上令人振奮。為《紐約時報雜誌》撰稿的那次經驗使我發現,一旦你面對智慧的定義,無論那定義是多麼初步、試驗性、有爭議或不恰當,你都不得不透過你自己的歷史和經驗的稜鏡來看這個定義。這也就是說,我們所有人頭腦裡都有個智慧的操作性定義(working definition),但我們很少被迫考慮它、諮詢它、質疑它或修正它,遑論在日常生活中應用某種智慧標準來衡量我們自己的行為和決定。
簡而言之,思考智慧迫使你思考你的生活方式,一如(我認為)閱讀有關智慧的文獻迫使你深思智慧的意思和涵義。你可能會像我一樣,將這種鍛鍊視為一種開明的自我覺察,近乎空想的正念或冥想,必然為我們的行動提供參考。另一關鍵是:將智慧與行動分開,是生活中的一種不當做法。希臘哲學家普魯塔克寫道:「我們尋求美德,不應該只是為了思考它,而是還要從實踐中得益。」
很快,每次我面臨挑戰──處理兄弟姊妹間的爭執,面對與親人或朋友的人際摩擦,被要求處理引發巨大阻力的事,甚至是權衡有關憐憫的瑣碎問題,例如是否要給某個窮人一些零錢──我都察覺到自己放慢了腳步,有足夠時間問自己這個問題:現在最有智慧的做法是什麼?我知道,相對於在加爾各答貧民窟工作的德蕾莎修女或在塞爾瑪遊行的馬丁.路德.金恩面對的問題,我的那些事真的微不足道,而且我不會說我持續不斷地如此思考──有良知有智慧的人可能很容易經歷一種思索存在意義而陷入的「屍僵」狀態(rigor mortis),因為連續的深思而癱瘓。
但我發現這種鍛鍊令人振奮。它迫使我看清楚選擇。它使迫切性時鐘慢了下來;我們難以作出決定時,似乎都在與迫切性時鐘賽跑。它使我得以走到自我之外,暫時抑制自己固有的自私衝動(我認為我的自私衝動不比任何人弱,但也很可能與其他人差不多),得到更多時間夠讓我看到較大的局面。它有一種古老但熟悉的自我監督特質。因為找不到一個更恰當的詞,我會說它使我覺得負責──不是別人要求我們負責任那個意思,而是指我們提高了對自己的期望。
***
但我所說的智慧確切是什麼意思?
智慧的許多定義集中在一些一再出現的共同要素上,例如謙遜、耐心、對人性和人類的困境有清醒和冷靜的看法、情緒韌性、應對逆境的能力,以及對模糊性和知識的局限近乎哲學性的認知。一如許多大觀念,它也受許多矛盾困擾。智慧以知識為基礎,但智慧的部分物理卻是不確定性塑造的。行動很重要,但明智的無為也很重要。情感對智慧至為重要,但情感上的超脫又是不可或缺的。某種情況下的明智行為,在另一種情況下可能非常愚蠢。
這些內在矛盾並沒有帶給智慧的潛在定義致命的困擾,它們反而嵌入其中。事實上,思考智慧的最好方式之一,就是試著找出能夠調和這些矛盾並仍然體現智慧的罕見人物。這些活生生(或曾經活生生)的人向我們展現智慧的定義,而因為他們是人,這些定義並不完美,但它們也比較不抽象,比較像是有血有肉的智慧。關於智慧,我們可以從它過去和現在的模範身上學到很多東西。
幾年前,加拿大一些心理學家做了一項研究,要求受訪者提出他們認為特別有智慧的歷史或現代人物。這種所謂的問卷調查研究有很多問題,首先是受訪者往往是大學本科生,樣本可能有代表性不足和智慧不夠成熟的問題。儘管如此,我們還是來看調查結果:受訪者提出的智者依序為聖雄甘地、孔子、耶穌基督、馬丁.路德.金恩、蘇格拉底、德蕾莎修女、所羅門、佛陀、教宗、歐普拉.溫弗瑞、邱吉爾、達賴喇嘛、安.蘭德斯、曼德拉,以及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絕大多數是歷史人物(現代智慧的少數在世模範之一是一名脫口秀主持人,這針對當代文化說明了什麼?),主要是男性,社運人士意外多,但以一張公認多孔的文化網而言,捕獲這些人也算是相當有智慧的表現。一如智慧本身,我們似乎都能在看到智者時認出他們。
智者名單上有那麼多歷史人物,說明了人類文化持續關注這話題──智慧這個題目永不過時,智者帶給我們的啟示超越他們所處的時代、地方和環境。另一方面,曼德拉和歐普拉這樣的當代人物入選,則令人欣慰,證明智慧對現代世界仍有強大的文化影響力,並提醒我們,智慧的一個核心要素是對促進社會正義和公共利益的承擔。許多人可能會對這個智者名單上的一些名字有異議(事實上,如果你在晚宴上討論這些人的相對優點,可能會引起非常有趣的談話),但我們多數人會同意,他們代表一群相當崇高的有思想的人,有明智行事的能力,至少在部分時間裡是這樣。
但是,這個名單也暴露了一些驚人的事實。其一是堅持有智慧的行為可能非常危險:在一個深刻的意義上,我們現在認為智慧出眾的人往往與他們所處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嚴重對立。事實上,古希臘智者畢達哥拉斯當年住在克羅頓,與當地民眾的關係惡劣到當地人燒毀他的房子,屠殺了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許多追隨者,迫使「創造」哲學一詞(philosophy,字面意思為「熱愛智慧」)的畢達哥拉斯為了保住性命逃離當地(畢達哥拉斯指出三種不同的「生活方式」──貪得型、競爭型和沉思型,並認為沉思型──東方的習慣說法是「覺醒型」──是最好的,遠勝其他生活方式)。畢達哥拉斯的遭遇預告了蘇格拉底的悲劇,而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在許多文化中,智者也是容易成為攻擊目標的人。上述名單上的許多智者必須放棄傳統的生活和思想模式,才培養出他們現在受讚揚的思維習慣(這些習慣往往導致他們堅持宣講社會大眾不想聽到的東西);當中許多人在世時被排斥或遭放逐,還有一些直接遭處決或暗殺。曼德拉和甘地遭囚禁;孔子求仕無門;蘇格拉底遭處死;而根據哲學家卡爾.雅斯培(Karl Jaspers)的說法,甚至耶穌基督最親近的朋友也視他為瘋子。在特定的時與地,智慧不但使人不安,還往往在社會上顯得危險。
令人驚訝、同時令人不安的另一點,是智者名單上女性相當少。名單上這麼多男性並非只是性別上的異常現象,還揭露了我們關於智慧的操作性定義有重大問題。智慧顯然不是男性Y染色體上某個基因賦予的特質。世上有所羅門(Solomon),也有撒拉(Sarah)和以斯帖(Esther);有伯里克利(Pericles),也有阿斯帕西亞(Aspasia)──後者是前者鮮為人知的情婦,而根據普魯塔克的說法,她是希臘文明最有智慧的時代裡最有智慧的人之一。世上有耶穌,也有抹大拉的馬利亞;有曼德拉,也有翁山蘇姬。在《希伯來聖經》中,智慧是個陰性詞。
那麼,為什麼智者名單上女性那麼少?我不認為世上有女性智慧不足的問題,問題僅在於有關智慧的文化觀念演變速度慢得令人苦惱,而且在許多個世紀裡,女性被剝奪了在公共領域展現智慧的權利,這種現象同樣漫長和令人苦惱。在古希臘文化中,雅典娜是智慧女神,但與此同時,雅典的女性不是公民,不能在議會裡發言或投票,不能加入陪審團,不能選擇自己的結婚對象或結婚年齡。她們是否因此就喪失智慧?當然不會。一如題為「女性崇拜:古典雅典的儀式與現實」的藝術展覽清楚顯示,雅典的女神──雅典娜、阿提米斯、狄蜜特、愛芙羅黛蒂──都是私人、家庭、近乎神祕的智慧領域的模範。藝評家霍蘭.科特(Holland Cotter)完全正確地指出:「出生和死亡──以存在而言僅有的民主經歷──都掌握在女性手上。」利西翠妲(Lysistrata)為了終止戰爭而率領女性同胞「性罷工」,作為雅典智慧的模範媲美蘇格拉底;莎孚(Sappho)視情感為思想的一部分,進而解放情感,比柏拉圖更接近現代神經科學。
因此,智者名單上女性較少並非天意如此,而是人類有問題:我們必須願意放眼更多地方尋找智慧。我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捨棄所有常見經典著作中所有常見的男性老白人;他們是很好的夥伴。我們可以在柏拉圖的對話、《聖經》的箴言和聖奧古斯丁的悲歎中找到關於智慧意義的有益啟發;蒙田睿智但常帶焦躁的洞見更是如此,他曾經宣稱:「智慧最明顯的標誌是持續的愉悅。」如果他是指對未來保持樂觀,神經科學家會認為他是有道理的,因為他們已經開始找到支持該觀點的證據。
但是,正如最有名的其中一名老白人觀察到(以窮漢理查謙卑的老生常談語氣說出):「有些人默默無聞,但靈魂與最有名的傑出人物一樣偉大。」事實是,智慧並非只能在巴特農神殿的臺階上找到,也可以在家庭餐桌上找到;並非只能在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的經典著作中找到,也可以在好笑的東西中找到(在漫畫家查爾斯.舒茲的傳記中,作家大衛.麥可里斯捕捉到《花生》漫畫的極簡智慧:他說《花生》漫畫是「關於人們如何有效應對日常生活的內部問題但從未真正解決它們」)。事實是,歷史上女性一直在公眾視線之外發揮她們豐富的智慧,「默默無聞」,但力量和影響力並不遜色。
事實上,我將論證,正是在這個私人、家庭、家族的領域,智慧對人的終身影響最大。母親的聖潔塑造了甘地的人格,父親的務實睿智成就了班傑明.富蘭克林;孔子的勤奮植根於他的單親童年,蘇格拉底頑強的哲學可能與他父親當石匠、母親當助產士有關。此外,這些人全都有老師和導師。在重大歷史關頭的偉大領袖宣言中,智慧顯而易見,但在父母與孩子日常分享的安慰和建議中,智慧也並不罕見(我可以補充一點:這種智慧是雙向暢通的)。我們可以在家裡,在工作中,在獨處或置身於人群時,在禮拜場所,有時甚至在更衣室裡找到智慧(體育記者早就認識到,落敗者比勝出者更有智慧並不稀奇)。
因此,智慧可能藏在許多不同的所在,取決於歷史時期、文化環境以及所面臨的個人或社會困境的性質,而且受正與這些困境搏鬥的人的氣質影響。在理性的時代,思想似乎是智慧最受尊崇的夥伴。在感性的時代,情感似乎才是最有智慧的嚮導。極端一點,在基本生存至為重要的時期,一如我們眼下的日子,非常務實的智慧比較可能造就美好的生活(事實上,在史前時代,粗糙的社會實用性可能被視為原始智慧)。而在科學時代,人類大腦的內部運作似乎能使我們得以窺見智慧的生物學原理。
| FindBook |
有 9 項符合
智慧之源:從哲學到神經科學的探索的圖書 |
 |
智慧之源:從哲學到神經科學的探索 作者:史蒂芬.霍爾 / 譯者:許瑞宋 出版社: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2-12-06 語言:繁體書 |
| 圖書選購 |
| 圖書館借閱 |
| 國家圖書館 | 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 | 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 電子書服務平台 | MetaCat 跨館整合查詢 |
| 臺北市立圖書館 | 新北市立圖書館 | 基隆市公共圖書館 | 桃園市立圖書館 | 新竹縣公共圖書館 |
| 苗栗縣立圖書館 | 臺中市立圖書館 | 彰化縣公共圖書館 | 南投縣文化局 | 雲林縣公共圖書館 |
| 嘉義縣圖書館 | 臺南市立圖書館 | 高雄市立圖書館 | 屏東縣公共圖書館 | 宜蘭縣公共圖書館 |
| 花蓮縣文化局 | 臺東縣文化處 |
|
|
圖書介紹 - 資料來源:TAAZE 讀冊生活 評分:
圖書名稱:智慧之源:從哲學到神經科學的探索
用現代科學顯現智慧的奧妙
橫跨人文與科學領域,探討智慧的關鍵課題
我們這時代是否可望變得更有智慧?
黃俊儒(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特聘教授)
謝伯讓(認知神經科學/腦科學家)
愛智推薦
史蒂芬.霍爾利用他的廣博學識和文學技巧,
帶給我們一部敏銳有力的綜合著作,
說明了在人類歷史悠久的智慧源泉探索中,
哲學家、神學家和二十一世紀的科學家作出了什麼貢獻。
這是一部結合洞察力與藝術的作品,
是一本充滿智慧的書。
──許爾文.努蘭(Sherwin Nuland),《死亡的臉》(How We Die)作者
人類文明歷史發展到現代,累積了許多智慧的成果,終於在二十世紀開始有科學家試著透過實證方法和科學儀器分析「智慧」。智慧可以被測量嗎?它有什麼特徵?智慧的運用如何反映在神經結構中?我們是否可以由此尋找智慧在大腦裡的源頭?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智慧和科學的對話又能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
作者史蒂芬.霍爾悉心拆解並重組了智慧最關鍵的科學命題。他立基於深厚的人文傳統,查覽重要的智慧文獻,包含荷馬史詩、哲學、《聖經》及古典文學,並援引蘇格拉底、佛陀、耶穌、孔子、甘地等人類史上公認的智慧典範。在他嚴謹的梳理下,智慧的種種概念跟心理學、生物學及神經科學的關注點一一連通起來。
霍爾將智慧概念分成八個神經支柱,分別是情緒調節、判斷力、道德推理、憐憫、謙遜、利他、耐心、處理不確定性,他援引相關主題的重要科學研究,詳實地加以論述。透過這樣的分析策略,霍爾引導讀者探勘了人文與科學互通的新領域,讓智慧在實證科學的檢驗下顯現其微妙之處。在這段知性旅程的最後,霍爾為智慧的時代意義作了發人深省的陳述。
各界好評
本書是全面認識人類心智的一趟黃金旅程,由歷來最有洞察力和最值得信賴的其中一位科學記者擔當領隊。本書是一場盛宴,而不是一些零食。請作好準備消化超出你想像的大量腦科學知識。
──大衛.申克(David Shenk),《別拿基因當藉口》作者
本書展現了驚人的才智、令人難以置信的寫作技巧,以及非常傑出的綜合能力。你可以不同意部分內容,但很難否定整本書。智慧仍與我們同在。
──麥可.葛詹尼加(Michael Gazzaniga),《大腦、演化、人》作者
史蒂芬.霍爾並非只是傑出的科學作家,他根本就是一位傑出的作家。
──麥可.波倫(Michael Pollan),《雜食者的兩難》作者
史蒂芬.霍爾再次做到了。他巧妙地解釋了「智慧」如何從大腦中產生,而且沒有過度簡化這個極其複雜的課題。
──約瑟夫.李竇(Joseph LeDoux),美國神經科學家
智慧是我們最珍視但最不理解的理想之一,本書是嘗試理解它的迷人著作。
──《種子雜誌》(Seed Magazine)
霍爾運用資深科學記者的才能,帶領我們完成一趟歡樂的跨學科跨時代旅程,結合了現代科學、歷史與哲學……非常可讀的著作。
──《自然神經科學》(Nature Neuroscience)
本書內容全面、發人深省,以一種合理──甚至睿智──的方式探討智慧這個棘手課題。
──《科學通訊》(Science News)
引人入勝的著作……霍爾充當人文學科與神經科學之間的翻譯和中介,這工作本身就需要非凡的心理平衡和理解能力。
──《信使郵報》(The Post and Courier)
作者簡介:
史蒂芬.霍爾(Stephen S. Hall)
資深記者與科普作家。三十多年來,史蒂芬.霍爾就科學與社會的交集寫了大量文章,主要發表在《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在本書之前出版了五本廣受好評的著作,包括《看不見的邊境》(Invisible Frontiers,關於生技產業之誕生)和《長生不老專賣店》(Merchants of Immortality,關於幹細胞科學與再生醫學之誕生)。他多次獲獎,包括2004年全美科學作家協會「社會中的科學新聞獎」的書籍獎,以及1998年癌症研究所(Cancer Research Institute)的威廉.柯立獎(William B. Coley Award)。除了科學,霍爾還大量撰寫關於旅行、棒球和義大利的文章。他與妻子和兩個孩子住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
譯者簡介:
許瑞宋
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任路透中文新聞部編譯、培訓編輯和責任編輯,亦曾從事審計與證券研究工作。2011年獲第一屆林語堂文學翻譯獎。譯有《反資本主義編年紀事》、《絕望死與資本主義的未來》和《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等數十本書。(http://victranslates.blogspot.tw/)
章節試閱
智慧始於覺察,對自我和自我以外的世界之覺察;智慧隨著我們對內在的「我」與外部世界的固有張力的覺察增強而加深。
《紐約時報雜誌》邀請我寫一篇關於智慧相關研究的文章時,我開始意識到這一點;那篇文章在那期雜誌封面上的標題是:「科學能告訴我們誰會變得更有智慧嗎?」一如我很快發現,我們不缺智慧的定義,也不缺對這些定義的爭論;在一九九○年出版、書名為《智慧:其本質、起源和發展》(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的學術文集中,十三章分別由多位知名心理學家撰寫,每位提出他們對智慧的不同定義。正如羅...
《紐約時報雜誌》邀請我寫一篇關於智慧相關研究的文章時,我開始意識到這一點;那篇文章在那期雜誌封面上的標題是:「科學能告訴我們誰會變得更有智慧嗎?」一如我很快發現,我們不缺智慧的定義,也不缺對這些定義的爭論;在一九九○年出版、書名為《智慧:其本質、起源和發展》(Wisdom: Its Natur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的學術文集中,十三章分別由多位知名心理學家撰寫,每位提出他們對智慧的不同定義。正如羅...
顯示全部內容
目錄
第一部 智慧的定義(某種意義上)
第1章 什麼是智慧?
第2章 世上最有智慧的人:智慧的哲學根源
第3章 心與腦:智慧的心理根源
第二部 智慧的八個神經支柱
第4章 情緒調節:應對的技藝
第5章 知道什麼重要:確立價值和作出判斷的神經機制
第6章 道德推理:判斷是非的生物學
第7章 憐憫:慈愛與同理心的生物學
第8章 謙遜:洞察的天賦
第9章 利他:社會正義、公平以及懲罰的智慧
第10章 耐心:誘惑、延遲滿足和學習等待更大報酬的生物學
第11章 處理不確定性:變化、「元智慧」以及人腦的硫化
第三部 獲得智慧
第12章...
第1章 什麼是智慧?
第2章 世上最有智慧的人:智慧的哲學根源
第3章 心與腦:智慧的心理根源
第二部 智慧的八個神經支柱
第4章 情緒調節:應對的技藝
第5章 知道什麼重要:確立價值和作出判斷的神經機制
第6章 道德推理:判斷是非的生物學
第7章 憐憫:慈愛與同理心的生物學
第8章 謙遜:洞察的天賦
第9章 利他:社會正義、公平以及懲罰的智慧
第10章 耐心:誘惑、延遲滿足和學習等待更大報酬的生物學
第11章 處理不確定性:變化、「元智慧」以及人腦的硫化
第三部 獲得智慧
第12章...
顯示全部內容
|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2023全新增修版]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2023全新增修版]](https://cdn.kingstone.com.tw/book/images/product/20156/2015630770320/2015630770320m.jpg?Q=2631a)